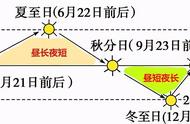阳光一天天地温暖起来,笑微微地照耀着大地。
风儿一天天地柔和起来,轻微微地吹拂着大地。
大地上,皑皑的积雪萎缩着身躯,不甘心地融化成雪水荡然无存。黑黑的土地在阳光下舒展着身躯,冰雪下沉寂漫长一冬的野草,急不可耐地破土而出,星星点点、若隐若现的绿色,昭示着一个充满希望季节的开始。
婆婆丁蘸酱、荠菜疙瘩汤、榆树钱面饼。吃了一冬天白菜、萝卜、土豆的我们,餐桌上越来越丰盛起来。在那个物质贫乏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着实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母亲是这个村庄最早走进春天的人。她在野地里仔细寻觅野菜的背影,也深深刻在了我童年的记忆中。
在这个百十户人家的小村庄里,母亲始终是最早在菜园子劳动的那个人。翻地、起垄、点种、栽秧,每年这个季节母亲都在菜园子不厌其烦地重复着,在我们看来十分枯燥无味的劳动。我们偶尔会去帮着翻地,获得足够的蚯蚓后,便扔下铁锹,拿起鱼竿扬长而去。
我们家的菜园子是最早长出绿色的,绿油油的韭菜、翠油油的生菜,惹得路人驻足而望,笑盈盈地同母亲搭着话,走时手里多了一捆鲜嫩嫩的蔬菜。
村里农具场旁有一块荒地,长满一人多高的杂草。母亲说这地方开出来一定是块好菜园子。清除了杂草,下面是一堆碎砖烂瓦、碎玻璃。母亲这才明白这块地为什么荒了这么久。
母亲一点点地捡砖瓦,我用土篮子将垃圾搬到一旁的土坑里。突然,我听到母亲痛苦的尖叫声,我看到鲜红的血从母亲的手指滴落,玻璃碎片划伤了她的手指。母亲用手帕将伤口包好,埋下头继续着劳动,我劝她别干了,但是被她倔强地拒绝了。
不久,一块平整的菜园子出现在人们的眼前,看着母亲在菜园子点种子、栽苗,人们不仅投来羡慕的目光。许多人也开始懊悔起来,这么好的菜园子为什么自己不去开垦哪?
母亲接连在村里、村外开垦出四五块菜园子。春天里,母亲在各个菜园子里奔波、忙碌着。
母亲不仅在菜园子忙碌,她也在翠绿的山林里采摘春色。
我始终无法忘记1986年的春天,那年农场向日本出口蕨菜,从山里采回的新鲜蕨菜每斤可以卖到3角钱,一天采个十斤八斤的就相当于一天工资。于是,小村子的人们争先恐后地走进山林。
母亲从山林归来时,身上的柳条筐是满满的蕨菜,母亲满脸微笑地看着眼前小山一样的蕨菜。收蕨菜的人惋惜地说,你这蕨菜没有及时蘸上一些泥土,根部老了很大一截,不能要了。看到蕨菜几乎被拦腰斩去,母亲的眼眶中盈满了泪水。
第二天,我们醒来时母亲已经进山了,锅里为我们热好饭。天黑下来的时候,仍然不见母亲的踪影。父亲焦急万分,找到了村干部,很快山林里手电筒四处闪亮,呼喊声此起彼伏。晚上九点多的时候,人们找到了母亲,她为了采到更多的蕨菜,走进了大山深处,返回时,由于林深树密,迷失了方向。她本可以丢下满筐的蕨菜,但她始终没有舍得放下。村干部叫来负责收蕨菜的人,破例收下了那筐蕨菜。
母亲是村里采蕨菜最多的人,领到了106元钱,她为我们兄弟三人每人买回来一双回力鞋,一件背心,还有一些饼干。她没有舍得为自己花一分钱。
2014年,母亲搬到了城里居住,每年春节刚过她就去市场买回了菜籽,然后张罗着要回村里。我劝她别回去了,她笑着说,我舍不得那几块菜园子。
我担心母亲,怕她累倒,多次给在村里生活的弟弟,让他劝劝母亲不要太累了。弟弟无可奈何地说,她能听谁的啊,她就知道种菜园子。其实,母亲种的菜我们家根本吃不了,大多数菜都被她送给了左邻右舍,看着村里人欢喜地拎着新鲜的蔬菜离开,母亲的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2019年5月19日,母亲突然因病离世。办完母亲的葬礼,我回到了母亲居住的老屋。在外屋的水缸旁,整齐地摆放着十几棵茄子苗。那是母亲去世前一天购买的,还没来得及栽在菜园,就永远地离开了。
我心情沉重地将茄子苗栽在笔直的田垄上,那是母亲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最后一垄没有播种的菜地。我看见,满菜园嫩苗在阳光下、微风中摇曳着身姿,它们在为这个季节而歌唱。
蓦然间,我真正明白了,母亲放不下的不是这几块菜园,她舍不下与春天的约定。
春天里的母亲,永远地印刻在了我心灵深处。
作者简介:
贺俊立,1969年出生,原籍山东省沂南县。1986年参加工作,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1990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先后在《北大荒文学》《农垦日报》《东北电力报》《黑龙江电力报》等报刊发表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100余篇。出版小说集《畸形之猎》、文集《谁可相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