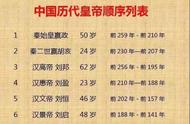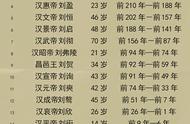1944年某一天的史屯,有一群女人为了救“老八”,她们在日本士兵的枪口下,用自己丈夫的性命换回了“老八”的安全,从而成为了八位“英雄寡妇”——后来他们有的不清不白地死去,有的投身革命,在建国后跌宕的政治风云中沉浮。王葡萄是“英雄寡妇”之外的第九个寡妇,她认领了自己的丈夫,但最后她的丈夫铁脑被“打孽”(百度了一下,是报仇,械斗和暗*的意思)打死了,那一年,王葡萄才14岁。
王葡萄是孙家领养的童养媳,丈夫死后,她依然生活在孙家。孙怀清是她的公公也是养父,为人正直善良,勤劳有智慧,因此积累了一定的家产。土改时,孙怀清被错划成恶霸地主,家产被史屯人分了,人也被抓了起来判了死刑。孙怀清的大儿子是投降解放军的国军团长,闻知父亲受辱后大闹了一通又投靠了国民党,从此没有了音讯。二儿子是解放军的军医,有着较高的“觉悟”,为了自己的前途和父亲划清界限,竟然要求尽早枪决自己的父亲。只有王葡萄在尽力营救,但也无济于事。
所幸的是,执行枪决时,孙怀清并没有死。王葡萄将孙怀清背回了家,藏在红薯窖里,这一藏就是二十多年,从最开始的土改到最后的解放,不管外面怎么风云变幻,葡萄始终以自己的秉性承载着这片土地最原始的热情和状态去生活,并且努力让孙怀清活下去。她说,只有活着,才有希望。(后来孙怀清总算被平反了,尽管对当时的孙怀清来说平反与否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
在别人眼中,王葡萄是“混不吝”、“生胚子”,她没有觉悟,不顺应时代,不管别人怎么在台上斗来都去,她始终坚守自己的认知不和别人同流合污。
在孙怀清的眼中,葡萄浑然不分的仁爱与包容一切的宽厚,使其超越了人世间的一切利害之争。(葡萄帮助过很多和她不相*人,即便别人会对她恩将仇报,她也不记恨,她一直在坚守自己做人的准则,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别人。好在一直以来也有人在帮助她。)
在和葡萄有过情感过往的男人眼中,她是“尤物”。葡萄经历了琴师朱梅、二哥孙少勇、史冬喜、史春喜和朴同志这五个男人。可以说,在每一份感情中,葡萄都很勇敢地去爱和享受。她可以抛弃一切和患了肺病的琴师朱梅私奔,也可以为了救公爹孙怀清,放弃她深爱的二哥孙少勇。她爱上了虽然长得丑但心地善良的冬喜,并且导致了后面与春喜的结合。和朴同志大概就是我们向往的灵魂伴侣了。她能在那个饿死人也斗死人的年代,瞒住所有的人顽强的生下了自己和少勇的孩子。她也为了能让孩子活下去,把自己的亲骨肉送给了“侏儒”,即便孩子从来没有叫过她一声“妈妈”。做为一个寡妇,在当时那个年代,她并没有被传统观念所束缚,也没有被现代女性意识所谓的“坚贞”所捆绑。她想爱,就去爱。她觉得这样很好,就去做,去享受。不为别人活,只为自己活。这也是我很欣赏的一点,我认为,别人眼里我们的幸福不一定是真的幸福,只有自己感受到的才是真正的幸福。
小说最后,孙怀清讲的这个故事,我也没太看懂,借用书友百度的内容,和大家共享,这也是我认同的观点。度娘说,通过这个神话故事,严歌苓想要表达的是一种神圣的母性!雌性在轮回,不管是任何力量,任何改革,军阀混战,各种观念在相互的替换,各种人物在轮番登场,这都不影响她回到人间,做她自己的事情。而且正如严歌苓的挚友、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女性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红旗所说,这个民间神话的化用,不仅有点儿化腐朽为神奇,同时仿佛注入了一种性别隐喻。一位老男人讲述着一位“祖奶奶的故事”,一代一代的托生转世,这世界倒底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而讲述者的性命得救,是因为一个女人的力量?严歌苓实际上以自己的创作演绎了这样的观点:女性应该以一种本能力量与男性平等生存,女性和男性都是第一性,这种本能力量是指一种不自知、不自炫、不媚男的自然力量,理想的女人不是作为取悦于男性的一种人,她本身也是一个被取悦的人,就是相互之间都在取悦,都在共同分享一种乐趣,这就是严歌苓独特的女性观。

第九个寡妇
我认为,这世间,也有那么一种女人,她们不在乎年龄,不受外界约束,从容笃定地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她们活得逍遥肆意,又让人念念不忘。
很喜欢亦舒说过的一句话,人生短短数十载,最要紧的是满足自己,不是讨好他人。
我们这一生会遇到很多人,我们走走停停,都是在寻找一种能让自己感到舒服的状态。
不为他人而活,不辜负自己,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才是一个女人最好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