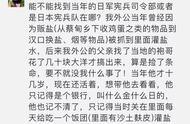前言
在上世纪物质匮乏的五六十年代,归化城里家家都有汆壶。汆壶,五十岁以上的人都应该记得,而再年轻些的人就未必知道了。那么,这汆壶究竟为何物呢?

汆壶是一种直径七八公分、高一尺左右,下有底、上有把的铁制桶形烧水工具。简陋点的汆壶上边无盖,精致考究的上边有盖,盖与桶把以铁链相连。
早期的汆壶是铜制的,配以可翻的盖。因为铜比铁传热快,所以烧水速度更快。解放前,归化城大户人家聘闺女时,父母都会买铜盆和铜汆子做陪嫁。铜质家用具不但质量好,档次高,而且经久耐用,寓意着夫妻和美,同心同德,所以铜汆子被人们列为上等品。
铜制品虽然讲究,但长期不用会生锈,需要时常擦抹;铜汆壶里面还需要镀一层锡,否则铜锈中的硫酸铜,会使人致病。锡的熔点才230度,如果涂层掉了汆壶就不能再用了,使用时必须精心;再则铜价太高,普通人家用不起。
自从马口铁在中国广泛使用,汆壶才不再珍贵,进入了寻常百姓家。马口铁又叫镀锡铁,铁皮的表面镀有一层锡,不易生锈。因为当时这种制造罐头用的镀锡铁皮是从澳门(英文名Macao可读作马口)进口的,所以这种材料在中国很长时间被称为“马口铁”。

加工汆壶的手艺人即“焊洋铁壶的”,此前不成行。齐如山先生曾说:“专做铁壶、铁盆、铁罐等器。从前此行甚微,只焊铁锁皮、铜器等而已,因无论中外铁匠,绝对不管焊活也。自马口铁、倭铅铁输入中国后,用以做成各种器皿,这种手艺始行发达,近来满街都是焊洋铁壶人矣。”
依稀记得,洋铁汆壶使用一年半载,底就漏了,这时可以到焊洋铁壶的摊上去换底。不过一换底就得裁去一段筒边,汆壶就短了一截,再漏了就只能换新的了。业此者以洋铁皮焊接水壶、水勺、喷壶、漏斗等器皿。货担一头放一小火炉、焊锡及一小瓶镪水;另一头为木箱,内装铁剪、丁字砧、木锤、烙铁等工具。其串街游走,吆喝“焊洋铁——壶来”。
五十年代,归化城里有暖瓶的人家很少。想及时喝上一口热水,只有靠汆壶。如遇贵客登门,用大壶烧水很费时;沏好的茶水旋即变凉,以冷茶待客,又礼数不周。所以用汆壶烧水,即烧即喝。因其方便、快捷,成为家家必备之物。
尤其冬季,家家都有洋铁炉子,把炉盘中间的圆盖用炉钩子挑起,将装满水的汆壶插入。因盛水少,离火源近,只需几分钟,里面的水就会沸腾。归化城的居民一般不用锅熬水,锅熬水有味,沏茶不宜。

笔者至今仍可回忆起儿时家里的老人们守着暖暖的炕火,捏一撮砖茶、小叶茶,或者圪枝儿茶放在小小茶壶里,等着汆子里咕嘟咕嘟的水开了以后,马上沏一壶香气四溢的热茶。可以想象一个人劳作一天以后,捧一把茶壶,一杯一杯地抿茶,那种物质和精神的享受是无法替代的。
记得我的一个小学同学,父亲解放前是掌柜子,五十年代公私合营后,以吃定息为生。那时,他家有大小不等的几个水汆儿。最小水汆儿烧开的水刚好泡一杯茶,中号的水汆儿烧开的水,可泡一壶茶。而那个大号的水汆儿,烧开水后一次可泡两壶茶,那是为来客多时准备的。当时家里来了客人,急于沏茶招待客人,他妈就会吩咐他:“去,拿水汆儿汆水去。”
汪曾祺先生在《寻常茶话》里曾说:“老北京早起都要喝茶,得把茶喝‘通’了,这一天才舒服。无论贫富,皆如此。1948年我在午门历史博物馆工作。馆里有几位看守员,岁数都很大了。他们上班后,都是先把带来的窝头片在炉盘上烤上,然后轮流用水汆坐水沏茶。茶喝足了,才到午门城楼的展览室里去坐着。”
汆壶在全家仅有一口大锅的年代,其不仅仅是烧水,还兼有小锅的作用。记忆里,汆壶里的水沸腾了,母亲抓几根粉条放在壶里,然后在里边揪上十几块面片。煮熟倒在碗里,拌点油盐葱花,就算一碗特殊的片汤。偶或还可以在壶里给我煮颗鸡蛋……

汆壶不仅城里人用,在乡间也很普及。浩然在《艳阳天》中曾写道:“锅里的水不是等着熬粥吗?等等汆子里的水热了再使不行吗?”但农村使用的汆壶更长一些,有的甚至达六七十厘米,又称“水吊子”。
雁北农家都是连炕灶,灶台与土炕相接。在灶台上面坐锅做饭,灶口开在下面,用来添柴。在灶台上靠近灶口的地方另有一个垂直的圆孔,这便是插汆壶的地方。做饭时可顺便将汆壶伸入那个圆孔中,利用灶膛的火就能同时给汆壶加热,做饭烧水两不误。用汆壶烧水,无需专意,即便用饭后的柴火余热,也能烧开几壶热水。
雁北不适宜种茶,乡间也沒喝茶习惯。我常想,倘若农家有喝茶习俗,这汆壶就是最方便的烧水工具了:生火做饭之余,顺便将汆壶伸入灶镬内,须臾间便可烧滚一壶泡茶的沸水,多及时、多方便!
试想,用滚烫的沸水沏一壶上好老茶,坐在纸窗下的土炕上慢呷细品,那该有多悠闲、多惬意!几杯香茗入唇润喉、满口生香。舌根沁津、浑身通泰,两腋习习风生,所有烦热与躁动顿时消遁尽净。如此农人生活不失为享受,倘再能有一碟野蔬或几颗山果佐茶,那就更是真正的田园生活了!
“小小子儿,倒拿锤儿,开开怯屋子两扇门儿,八仙桌子漆椅子儿,足蹬着脚搭子儿。水满壶,洗汆子儿,四样儿菜有名景,嫩根儿嫩韭菜,八大碗烩虾仁儿,烧猪烧鸭子儿,天上大娘是个道人儿,扯下荤席摆素席儿,叫声大娘吃饱了,上南台,听大戏,芭蕉扇儿,打蚊子儿。”这首老北京儿歌,经美国传教士何德兰整理,收入中英文的《孺子歌图》中,1900年正式出版。其中“水满壶,洗汆子儿”,恐怕今天知道它的北京人也不多了。
自从进入新世纪,随着集中供暖,洋铁炉子的消失及电热壶的普及,汆壶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即使在乡间也难见它的踪影,遗弃了的汆壶也多被当作废铜烂铁卖到废品收购站了。

内蒙古诗人柳苏有诗《汆壶》云:
我们在饥饿中坐定听着汆壶里烀嘟嘟的响声那时候,远离贪婪满足,把一撮黄豆、一颗鸡蛋煮熟无惧的铜锡随时纵身于水火感激之情就变作不断擦拭日子流水般过去了,主人的笑容日渐增多汆壶开始流泪,修补匠失去踪影也许,几辈子的沸水沸汤堵不上某一天针眼大小的渗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