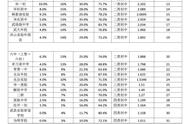作者/金先生

泛彼柏舟,亦泛其流。
耿耿不寐,如有隐忧。
微我无酒,以敖以游。
我心匪鉴,不可以茹。
亦有兄弟,不可以据。
薄言往愬(su),逢彼之怒。
我心匪石,不可转也。
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威仪棣棣(di),不可选也。
忧心悄悄,愠于群小。
觏(gou)闵既多,受侮不少。
静言思之,寤(wu)辟有。
居月诸,胡迭而微。
心之忧矣,如匪漧衣。
静言思之,不能奋飞。
1
看那划行的柏木船,随着河水自由地行驶。我却独自难眠,耿耿于怀,有难言之隐。我也难以借酒消愁,因为我心想遨游,却不能遨游。
我的心哪不是铜镜,不能谁都看得清楚。我也有兄弟,可是他们是靠不住的。我真诚地把心里话向他们诉说,他们还向我大发脾气。
我的心哪不是石头,不能随意地改变。我的心也不是竹席,不能随便地卷曲。我堂堂正正,满腹才华,怎能在这狭小黑暗之地憋屈!
我的心哪忧愁压抑,因为身边的小人都在嫉妒我,打击我。我遭到多次的陷害,受到不少的欺侮。我已经深思熟虑,下定决心,非离开这里不可!
太阳啊月亮啊,你们为什么不放出光芒?我的心忧愁而憋屈啊,好像一件脏衣服洗不清。我已经深思熟虑,想展翅飞翔,可是我飞不起来……

2
《柏舟》写的是什么?关键要看其抒情的主人公是谁。读其诗,深知全诗写的是一个“耿耿不寐”、“心之忧矣”的人。这样忧愁的是什么人呢?诗中有一句“威仪棣棣”值得注意。这一句是承接“我心匪石”、“我心匪席”之后的第三个排比句,并与“不可选(退让)也”与“不可转也”、“不可卷也”并列,可见是自指。
恰好《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写北宫文子向卫侯谈到《诗经》“威仪棣棣,不可选也”。他说什么是“威仪”呢?“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爱,进退可度,周旋可则,容止可观,作事可法,德行可象,声气可乐,动作有文,言语有章,以临其下,谓之有威仪也”[1]——这不很清楚了吗?《柏舟》的这个主人公是个堂堂正正、为人楷模而又满腹才华的人。于是,这个人只能是当时的“士”,而且是贤士。贤士“心之忧矣”,肯定是不能发挥其雄才大略。诗中接着又写到了,这样的人还“忧心悄悄”,因为有“群小”的嫉妒和欺侮啊!
贤士受了打击,使他“耿耿不寐”。他当然不甘心过着憋屈的生活。于是,他经过“静言思之”,决定“以敖以游”。当他把这一决定告诉他的亲兄弟的时候,谁知得到的是大发脾气。自己的兄弟都不能理解,他就只能非离开这里不可了。可是,他生存的环境藩篱重重,黑暗无边,连太阳月亮都照不到,他仍然“不能奋飞”。这样,他怎能不愈益忧愁和焦虑!
精神分析认为,“焦虑作为一种情感状态,是一种旧的危险威胁事件的回忆”,由此便在精神上产生“压抑”。弗洛伊德还进一步深挖这种焦虑和压抑的根源,乃是由于“本我”与“超我”的冲突,“本我”受到了压迫和挫折。弗洛伊德认为的“本我”又称“伊底”,即性本能;“超我”即社会规范,社会规范压抑性本能乃是永恒的冲突[2]。只是我们可以把“本我”从狭隘的“性本能”扩展为人的本性——人性来认识,也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他也为太强烈的本能需要所促迫:他渴望荣誉,权势,财富,名誉,和妇人的爱;但他缺乏求得这些满足的手段……”[3]。弗洛伊德这里指的是艺术家的人性“本能”。对照《柏舟》里的那个“耿耿不寐”的贤士,他的忧愁,他的焦虑与压抑,不也正是这样的人性本能所造成的心理反应吗?他的本能需求完全是正当的,可是他生存的环境太黑暗,他“缺乏求得这些满足的手段”,以致他想“奋飞”也不能够。《柏舟》就是抒写这个贤士的苦闷不能避免。
3
传统的《诗经》解读多是误读,唯对《柏舟》的解读还差强人意。据《诗经原始》载,《小序》说《柏舟》是“言仁而不遇也”;而《诗经原始》则说是“贤臣忧谗悯乱,而莫能自远也”。并分析说,“邶既为卫所并,其未亡也,国势必孱。君昏臣聩,佥壬满朝,忠贤受祸,然后日沦于亡而不可救。当此之时,必有贤人君子,目击时事之非,心存危亡之虑,日进忠言而不见用,反遭谗谵。欲居危地而清浊无分,欲适他邦……”,这些见解都是说得很好的,完全与本诗的内容相吻合。只是分析这位“贤臣”为什么“不能奋飞”的缘故时,竟然说是由于“宗国难舍”,这就有点想当然了。以至更说到“一腔忠愤,不忍弃君”,而“古圣编《诗》”,并编之于“一国之首(邶风之首),以存忠良于灰烬”[4],可见也是从忠君的正统思想来看待的。殊不知《柏舟》诗里却写“我心匪石”、“我心匪席”,他哪有“宗国难舍”、“不忍弃君”之心呢?“日居月诸”,可比之于君吧,但如此黑暗,他又哪里还有一点留意?
其实,在春秋时代,随着分封制的建立,财富和知识的垄断也相继瓦解,士人的独立人格也得到了尊重,士人的自由流动渐成风气,“养士”、“楚才晋用”等便是普遍的现象。《战国策》写有“天下之士合从相聚于赵”的事,秦王很担忧,秦相就派人载着美女和乐队,到赵国大摆宴席,并分尝千金。结果3000金没有尝完,“天下之士,大相与斗矣(大家便为钱争斗起来)”[5]。由此可以看出士人在当时并无所谓“宗国难舍”、“不忍弃君”的情怀。
钱钟书先生在解释“我心匪鉴”等句时认为,“我心匪鉴”与“我心匪石”、“我心匪席”“三句并列同旨”,都是“人不能测度与我,人无能明其志”之意[5]。钱先生解说深得《柏舟》之意,抒情主人公的心啊,已无人能够理解,他怎能不太孤独,太痛苦!

4
现在,都把《柏舟》的抒情主人公解读为一个“可怜的妇人”,而且是“一个性格刚烈的女子”。于是,这首诗就成为“自伤不得于夫,见侮于众妾,表现出一种委屈忧伤而又愤愤不平的情绪”[7]了。
《柏舟》写的是一个女子吗?首先,诗中写“微我无酒”,女子饮酒吗?其次,即使女子失宠,投诉于兄弟,哪有兄弟发怒的事?再说,把“群小”释为“众妾”也不当,“群小”一般是指朝廷的谗臣小人;况且即使是小妾,也不至于成“群”。第四,说这是个刚烈的女人,但也不能用“威仪棣棣”来自况。“威仪”一般用在男子身上。第五,最重要的是,诗中写到主人公“以敖以游”和“奋飞”的打算,这更不是古代女子决绝的行为,而是大丈夫远走高飞的举动。至于诗的开头“泛彼柏舟,亦泛其流”,显然只是起兴,将其解为比喻女子的处境漂流无依也是望文生义,而应该是反衬诗人内心的隐忧,是移情。
把此篇《邶风·柏舟》解为女子失宠,也许是受到了另一篇《鄘风·柏舟》的影响。按《鄘风·柏舟》的抒情主人公确实是个姑娘家,“髧彼两髦,实维我仪,之死矢靡它”,明显写着她选定了那个还留着两只丫角的少年郎,誓死也不变心。接着写“母也天只,不谅人只”,则是对母亲干涉她的婚姻的强烈反抗。这首诗涉及的人物和事件都很明白,如果她想私奔,也说得过去,但她没有。而《邶风·柏舟》里写的,“以敖以游”和“奋飞”却绝不是私奔之意,岂能是个女子?
两篇同题《柏舟》,一复杂,一单纯。那个贤士的心理苦闷,是不可解的。
金先生叹曰:
泛彼柏舟我断流,
小人在上我碰头。
心非铜镜人不知,
插翅难飞欲何求。
【注释】
[1][春秋]左丘明:《左传》。华龄出版社2002年版,第377页。
[2][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新编》。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61-65页。
[3][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01页。
[4][清]方玉润:《诗经原始》(上)。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21页。
[5][西汉]刘向:《战国策》。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86页。
[6]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7页。
[7]朱杰人:《<柏舟>赏析》,见周啸天主编《诗经楚辞鉴赏辞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90年版,第66页。
更多文章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道风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