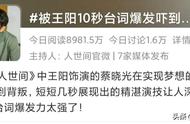注意到痕迹,就注意到了人,注意到了人的本性。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痕迹。鞋印、痰迹、用过的卫生纸、嚼过的口香糖、玻璃板上的手痕、墙角高高的尿痕;气味,各种各样的气味,屁臭、口臭、狐臭、汗臭、脚臭,还有醉酒后鼻息喷出的酒臭,居民楼的门缝下钻出的每个家庭独一无二的气味。这些东西让人无法忍受,正如人本身。
痕迹比别的东西更能暴露人的本质。人追求超越性,而痕迹毁灭超越性。后来我再也不直接拍摄人,而是拍摄暴露痕迹的空间。我力图使照片有一种不动声色的震惊,这些空间往往存在三个层面的场景:
- 这里没有人,也未曾有人来过
- 人在这儿时的样子
- 人在这儿之后的样子
这样无人注意的角落有很多,只不过无人发现。实际上,城市并不属于人。我刻意去观察散落着啤酒瓶和废报纸的天台、一堵墙和另一堵墙之间无人光顾的夹道、三十楼外无人触及的半空。只要注意到这些你就会明白,人只是在想象中占据了城市罢了。无人占用的空间总让人觉得放松,有一种万人如海一身藏的惬意和自由。
我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我讨厌人。确切地说,是讨厌包括我在内的任何人。我厌恶手上的皮肤,厌恶呼呼作响的肺,厌恶脂肪和血红蛋白,厌恶早晨毛孔里钻出的胡茬。生物肮脏,就像捏死蜘蛛后流出来的荧绿色汁液。如果没有生物,世界上将不会有丑恶。从小我就从动画片里得出一个规律,肉体是精神性的,丑恶天生具备生命而不是相反。
连医院走廊里带有婴儿笑脸的张贴画都会让我厌恶。
无论外表还是内心,罪恶从毛孔里一点一滴地渗透出来。那些婴儿是谁?说不定已经长大,犯下无数丑恶的勾当。也说不定早已成为平庸的普通人。一点一滴都是罪恶。谁能觉察呢?面对自己,人人都会大吃一惊。人们会想,这个人是谁?自己什么时候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少年时代开始,我就能感到自己的生长,精神性的那种,如同罪恶本身在蜕变——像褪掉一层又一层的躯壳。我恐怖地感觉到一件事情:原来的那个我再也回不来了。我再也不是他了。现在的这个我是以前无论如何也无法料想的。一直到几年之前我仍然对未来抱有期望,会等待下一次蜕皮。
下一次往往会重复这一次的经历:对失去的格外惋惜,对现有的格外困惑,对未来的格外希望。人总在变,或许也可以这么看:虽然人在变,但这个认识本身从未改变。这个从未改变的,不停的反思的存在就是我。我思故我在。但没过多久我厌倦这一切胡思乱想了。变不变都一样。
我试图尽量的守住自己,像一株大树那样。安分,不动声色,对外界的一切默默接受。我总是把自己想象成一棵大树。不,准确地说,是树干里面那柔软,白色,渗透着水分的树肉。我把自己想象成那部分东西,或许每天都在生长,可生长出来的东西完全一样,亦即完全没有质的改变。
我尽量少和别人接触,正如一棵树不会知道旁边的树。它连自己都不知道。它什么都不知道。它生长,白色地,柔软地,而且毫不质变,如此而已。
在这个城市中,我能说的话越来越少了。我跟小卖部的老板有不多的几句交谈,我需要烟。这几乎就是全部了。这个城市已经自动化到不需要任何交谈就能生活的地步。只要有手机,完全畅通无阻。我从自动提款机里提出钞票,在超市里购物,接过零钱。耳朵里永远塞着耳机,连拉屎时都这样,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圆号和小号音浪滚滚。从没有人打扰到我。
刚开始,我的确遇到了一点困难,因为不得不讨回照片稿费。有了微信后,渐渐好了起来。我试图减少自己给别人留下的印象,像擦玻璃一样把自己擦掉。我从来不在作品上属我的真名。比方说,如果拍摄了一条马路,那么,这张照片的署名就是“窗户”。因为从窗户可以正好看到这条马路。这样就是窗户在拍摄,而不是我在拍摄了。如果我拍摄了一扇窗户,署名很可能是“路灯”。
除此之外,只听音乐,看本世纪以前的电影。我看大量的新闻。新闻给我灵感,别人的庸俗照片经常被我抓到足以成为天才之作的素材。我是一个二手的再加工艺术家。
这种情况不可能持久。我明白生活如此脆弱、不堪一击,全靠过时的摄影技术维持。我的工具是一整套的佳能相机:支架,相机,大三元镜头。我的相机和科特兹的一样扎实。我用这台相机拍摄各种各样的图片。我不想跟对象本身有什么关系。拍摄是为了隔断而不是建立联系。
我清楚地明白,照片是照片,事物是事物。两者之间根本没有任何关联。我把这些照片寄到全国各地,靠电子邮件和编辑来往。每张照片的收入足够一个星期的伙食。
有一次,我在路边发现了一具麻雀的尸体。我突然想到了什么。每天早晨,都会有一群麻雀在窗前叽叽喳喳。从我的窗子往外看,只能看到一堵红砖砌成的围墙。墙的另一面是一个菜园,丝瓜还是什么藤蔓类植物从墙头翻越了过来,垂下许多弯弯曲曲的绿丝。麻雀每天蹲在墙头叫嚷,我有时候觉得很吵,有时候觉得很安静。
实际上,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麻雀的尸体。小小的宛如破损标本的尸体已经干枯,骨头发白,感觉像是饼干。皱巴巴的眼睛黑乎乎的,羽毛完全没有任何水分,爪子被压扁成了片状。我用脚踢了踢,它很轻,像一片枯叶。它散发出淡淡的腐臭味,很咸。
我站起来,俯身用镜头对准麻雀的尸体。花了五分钟才找到令人满意的角度,快门。一张,又是一张。我再次换了个角度。拍摄完毕后,我把它轻轻地放到了路边的草丛里。
晚上,我在电脑中再次观察了这只麻雀。我怎么从来没见过麻雀的尸体,除了早上见到的这一只。只有这一只而已。许多人如同这麻雀一样,在眼皮底下正在改变,正在失去,正在成为过去。麻雀成了骨头和羽毛,它们再也不是麻雀了。我觉得这妙极了。
上网之前,我看了手机,有两条短信。其中一个是我的朋友。我们正商量着相约自*的事情。我将短信删除。另一条短信是缴费提醒。关机。查看早上浇过水的一大盆吊兰。拉上窗帘。撕开一包咖啡。泡好。重新坐在电脑前面。
和以往一样,网上找到的资料有很多重复,内容颇不一致。鸟纲,雀形目,文鸟科,麻雀属。寿命的记载不完全相同,大致十年左右(真久,比我想象的久多了)。活动范围二点五至三千米。每年至少繁殖两窝。平均八只雏鸟可以成活一只,十五天即可自行寻食。体型,产地等等。
我注意到一条消息。2000 年,麻雀成为国家二类保护动物。天知道,2000 年那天(资料上是八月一号),我正巧在看新闻联播,那时候我还很兴奋、好动,喜欢把泡泡糖吹成一个气球然后炸开。有一点让我印象深刻:麻雀是一种群居动物。它们只有在快死的时候才会离开群落,找个不易发现的地方等死。大概是由于这个缘故,麻雀的尸体并不常见。也就是说,麻雀是群居的孤独者。
没错,动物似乎都有感知自己死亡的本能。在死之前它们就预知了自己的死期,不声不响地找到一处僻静之所安身,就像人给自己找一个坟墓。换句话说,我就是一只在寻找坟墓的麻雀。在众人眼中我已经死亡。我希望的正是如此。
对于长眠不醒的人而言,床很重要。我想起了一处无人涉足的海滩。海滩是我发现的,位于福建省的某个角落。之所以选择它,是因为它还没有被谷歌地图拍摄下来。一处没有被现代化的场所,用来赴死最好不过。
上床之前,我给朋友回复了短信。短信中告诉了他海滩的地址。自*的时间约定在明晚。入睡前,我注意到了窗外的雨。雨滴装作有生命的样子在玻璃上爬来爬去。那样子让我感到非常恶心。
醒来,早晨。我准备好行李,一样都不少。相机和钱包都在。背包里装着几件衣服。出门前自己手绘的地图。笔记本、手电筒、防风火机和半包香烟。下了车。地图早就在心中背熟,所有的乘车线路也早已熟知。
城市全都一样。第七个小时,我到了。这是一座小小的海滨城市,几乎所有的商店都关了门,安静得像电影片场。道路上一个人都没有,偶尔有车辆急匆匆驶过。路灯的影子让人想起排列整齐的巨大廊柱。
我猜测这和天气有关。还在火车上的时候,我已经注意到逐渐阴沉下来的天空。乌云浓重而黑,像垃圾场里的垃圾一样堆积得越来越多。风把棕榈树往一个方向使劲儿拽,像男人的手拽住了女人的头发,然后有点疯狂地扯动着。没有公交车,我沿着街道顶着风往前走。
在路上,我看到了海。它是黑色的,夹在民居之间,像一片坟场。我的四周,风莽撞地穿行,看不到任何行人,所有的人都好像消失了。开始下雨了,伴随着轰隆的雷声。道路在风雨中变得模糊起来。我听到了远处的玻璃碎裂了,一些广告牌摇摇欲坠起来。
竟遇到了这种天气。我走到海边时,风已经非常大了。海浪一浪高过一浪,不停地往岸上推,伴随着轰鸣无尽地砸出大团的泡沫。夜光表显示的时间是晚上七点,天就要黑了。天气让我有些意外。我本以为大海是平静的,硕大的月亮挂在深蓝色的天空里。然后我就可以一点点往海的中间走去,越走越深,越走越平静。
计划中我并没有安排住宿。这天晚上,我将住在海滩无疑。别的地方无处可去。我待的地方不属于任何浴场或者小区,整个沙滩都空空荡荡。左侧的山坡上有一个杂木丛生的树林,右侧的山坡迎着风浪,岩石黑而坚硬。沙滩不过三四百米长而已,后面的沙地上生长着灌木丛。海面上吹来的风寒冷刺骨,但这里并非只有我一个人。
大路已经到了。他正对着大海抽烟。海风把烟头都快吹灭了。他低头看了看表,说还有时间,我们再等一会儿吧。我一年没见过他了,他看起来还是很瘦。他根本没有看我。
“台风要来了。”他说。
“我早该想到的。”我对他说。我洞彻了我们的任务:台风和我们无关,我们要不留下任何痕迹地死去。
我和大路的相遇完全来自于我们的天才。
几年之前,我在一所大学拍摄照片。有什么异样的东西出现在了镜头中,让我的心脏震颤起来。我抬起眼睛,没有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校门外人来人往。三三两两的学生正在合影留念,有些路人驻足欣赏古朴的校门。我拍摄的对象是大门两侧两棵硕大无比的石楠。时值花季,盛开的的石楠散发出饱满的精液的气息,漂浮在慵懒的暮色里。很多人对这种气味一无所知,甚至凑上去嗅这种腐败的味道。他们的脸上浮现出了不可思议的笑容。
让我震颤的肯定不是精液的气味。
一个正在上出租车的男人朝我走了过来。隔着五米,我知道我为什么震撼了。他的额头和耳朵和我一模一样。他的脸上带着略微的震惊和困惑。他的眉毛、鼻子、眼睛和嘴巴和我一模一样。他站在我面前,有那么一会儿,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因为从他胸腔下面的心跳传递到了我的胸腔。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他对我说。
我们面面相觑,忍受着这种异样的古怪感。我仿佛看到了另一个自己从相片里走了出来。我们身旁路过的一个女孩也似乎注意到了什么,惊讶地叫了一声双胞胎啊。为了避免引起混乱,我们离开了,留下了联系方式。我是在回到家之后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的。
他瘦得要命,像一具骷髅,穿一件松垮垮的大衣。那样的大衣是我梦寐以求的,因为我是个胖子,而且腿短,穿这样的衣服只会引人发笑。在他身上,大衣很合适。他瘦削的面庞很像我的灵魂。我太胖了。他仿佛是从脂肪堆里打捞出来的另一个我。
大路是一个房东。这也是我梦寐以求的职业。他生活在一个县城。如果从高空俯视,县城的造型看上去很像是一枚硕大的铜钱。方方的城池,四面围着一条圆形的护城河。在这座有着近千年历史的小城,他靠父亲名下的几套房子过日子。房租不多,但在小城足够了。可笑的是,我的生活是大路的梦想。他一直想摆脱县城,去大城市生活。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点,都想过自*。
大路自*过两次,都没有成功。我能理解他,对于过分敏感的人而言,死也会变得格外漫长。因为在死之前,必须先感受死的含义,就像品味一种味道很苦的东西一样。自*是对于死的思考而不是仅仅死掉。经历了几次自*之后,我们还是没有体会到死亡的味道。
海浪越来越大,砸出大团的泡沫。风用肉眼可见的速度冲刺。大路还是那件大衣,紧紧地裹在身上。他瘦高的身材很适合风衣,这种衣服穿在我身上只会变得好笑,就像猪脖子上绑了一件披风。
他偶尔会说起他父亲的事情,那是个疾病缠身的酒鬼。大路的瘦弱就是因为遗传了父亲的疾病。有一次大路说打算卖掉父亲的房子,搬到我所在的城市生活。后来这件事又逐渐没了下文。每次见他,他都是老样子,好像从来不会蜕皮。认识两年之后,我们的话慢慢变少了。语言成了多余的东西。过了好一会儿,我又问他父亲的事情。
“走之前跟他喝酒了。”他说。
我没有继续往下问。
就在这时,风里传来了不一样的声音。发动机的声音。我转过头,海滩上漆黑一片。远处,两束光芒一下子跳了出来,隐约看到一台越野车的轮廓。那情形就像从黑暗之中窜出了一头野兽,怒吼着往前跑。它很快跑到了我们不远的地方,吭哧吭哧地喘气。
车上下来了四五个人。在远光灯的照射下,我隐约看到有三男两女。他们在狂风中发出了兴奋的呼喊,随后开始脱衣服。在单薄的外套下面露出来早就穿好的泳衣。泳衣都是连身的,鱼皮一样从脖子包裹到脚踝。随后,他们从车顶卸下了几块长长的东西。从形状上看,是冲浪板。
没有人发现我们。我和大路在离他们几步远的黑暗里。
他们开始在沙滩上跑步,那模样像是在热身。风太大了,他们说话时不得不扯着嗓子。偶尔有残破的话被风送到我们这里。我听到他们说,“今天这浪可以。”大路一动不动,只是看着他们。我觉得他们的出现扰乱了我们的计划,本来,我们打算在空无一人的情况下去死。我对大路说,“怎么办?”。他回答说不知道。
我看着他们跑向了黑色的大海。
他们的冲浪板好像会发光,变成了远处不停闪灭的几个光点。除此之外,我们只能听到风声和海声。这就是台风吧。风太大了。我们很快支撑不住,在沙地上缩成一团。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风,风声像许多匹马在狂奔。雨水在空中被风击打得粉碎,变得坚硬,敲打在身上一次比一次沉重。四下一片漆黑,唯有越野车的两束大灯射入黑暗尽头,那模样像蹲在门前的狮子,目光炯炯地守着岗位。大路在大衣里面蜷缩着,我听到了他牙齿打颤的声音。
他说:“等会儿,等他们结束。”
他们根本没有结束的样子。风越来越大。海浪发出潮涌的巨大声音。渐渐地,人的声音被彻底冲散了。只有海浪一次又一次不知疲倦地冲击着海岸。我浑身都湿透了,雨水顺着领口淌进了身体。除了嘴里残存的口水,我几乎感觉不到自己的体温了。他们该不会死了吧。我脑子里突然想。
“我最近买了一套相机。”大路突然说,“我也想搞摄影了。”
“那么,你还来这干什么?”我问他。
“你知道麻雀吗?”他问我。
“麻雀?”
“对。我在老家的时候,听别人讲过这样的事情。我们那里到处都是麻雀,以前,人们都打麻雀来吃。在路边随处可见油炸麻雀的小摊。我小时候就打过麻雀,用自己做的弹弓。后来,我想你已经知道了,麻雀成了国家保护动物,数量多了起来。除此之外,麻雀是一种群居动物,它们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死。在临死之前,它们会自己找一个地方,静悄悄地死去……你以为你为什么会想死?”
“看来你都知道。”
“对。我知道,你也知道我知道。我们虽然人是两个,但几乎一模一样。那天,从出租车上下来,我就明白你是另一个我。所以,如果我要自*,你也不能活着。我就拉上了你。我知道你也一样。”
我没有说话。
“后来,我们都发现,我们可以感受到对方的感觉。你看,你厌恶你的精神,而我厌恶我的身体。父亲瘦弱的身体也让我软弱。如果我们换换位置,将会变得完美……你能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
大路看着我。在黑暗中,他的眼睛像铁钉一样冷而坚硬。我的呼吸急促起来。渐渐地我觉得这不是我的呼吸了。我的眼睛像磁铁,紧紧地被他的眼睛吸住了。我感觉很冷。寒冷裹挟了我,朝我的胸口伸出十根长而冰凉的手指,穿过前胸一直插到后背,拽住了我的肋骨,占据了我的全部身体。血以双倍的速度在血管里流动。肺用两倍的力量呼吸。我看到面前的身体站立起来,朝那片黑暗的地方走去。那是我的身体。他正在缓慢地往前走。
我感受到大海已经在我的脚下了。不,那已经是他了。冲浪的年轻人在他的旁边。他们的冲浪板周装饰着一圈儿闪烁的射灯。光线可以照亮冲浪板周围的一小块海域,海水像滚开了似的。他们光溜溜的身体在海浪上打着盘旋,忽上忽下。我听了一会儿,听到了断断续续的呼喊声。我知道他不会回头了。他怔怔地走向了大海,仿佛梦游一般。海浪汹涌而至,不会给他思考的时间,一切都在计划之内。苦涩的海水嘴对嘴呕吐一般灌入了他的口腔和肺部,仿佛灌入了我的口腔和我的肺部。我目送那具身体被大海卷入黑暗的深处,那个令我作呕的瘦弱的身体。我第一次然而绝不会是最后一次体味到死亡的味道。
我知道他已经去了。没有人发现这一切,包括冲浪的年轻人。现在他们在黑暗中差不多耗尽了精力,没了劲头。这些人技术不错,海水把他们冲洗得很干净。当他们把冲浪板夹在身体一侧往海滩上走的时候,已经离我非常近了。发光的冲浪板像许多大睁的眼睛,在黑暗里缓缓移动着。
这家伙是谁?我听到他们发出了充满惊奇的声音。我看清了他们的面孔。他们的脸被冻得发青。冰凉的海水让他们浑身上下每寸皮肤都紧绷着。头发缩得很细小。这些被冻僵的脸看上去全都一样,分不出谁是谁,甚至分不出男女。他们的手触及在我肩膀上时,我确确实实感觉到那手触碰到了自己身上。对我而言,这是一个崭新的身体。
“我是个摄影师。”我听到自己说,“我叫大路。”
我从沙滩上站起来,感受到自己肥胖的身体像酒桶一样有着轻微的晃动。脂肪让我感到温暖,我非常满意。现在我已经知道什么是死亡了。死亡是苦涩的,充满了生命的咸味儿。我向他们借了一块冲浪板,朝大海走去。他们问我风快停了,你去干什么?我告诉他们,我刚学会了蜕皮,现在是时候洗个澡了。
关于作者甄明哲
甄明哲,90 后,河南人,在《青年文学》《大家》《西湖》《山西文学》《作品》《牡丹》《大观》等刊发表短篇小说二十余万字,短篇小说《京城大蛾》转载于《小说选刊》2017 年第 6 期,入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青春文选》,短篇小说《池中金龙》入选“《作品》90 后文学大系•小说卷”《近似无止境的徒步》。
一些解读
这篇小说的特色所在并不是它的故事——两个人互换身体,这类故事多少有些老套,而在于对主人公所作的心理刻画。他对自我、他人和死亡的思考方式,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困扰,会让我们想到《地下室手记《厌恶》《局外人》《人间失格》这一系的小说。其中不乏奇诡的比喻,比如将自己想象为“树肉”。
小说中使用了许多有力的短句,情节推进、景物描写都表现得干净利落。麻雀的尸体作为一个慑住主人公心灵的意象,在故事中有点突兀,如果是更纯粹的心理小说,也许能获得更充分的挖掘。但是,我们也可以设想,两人互换身体这件事也是一个心理事件,死掉的是主人公的另一个自我,一个抽象的人格。而那些被压抑、被抹*,或者通过升华消解掉的“自我”,就像是他人看不到的“麻雀的尸体”。(特约编辑:朱岳)
题图原图来自:Evgeny Karasevon iSto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