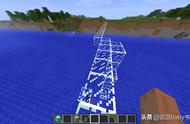*雨果的额妮柳霞
11月,大兴安岭森林腹地的土还是冻着的,不能立刻下葬。雨果计划等到来年春天,将柳霞的骨灰送回山上,和姥姥的墓葬在一起。墓就在驯鹿点不远处。母亲离开后,驯鹿们总喜欢来回瞅,“不知道是在瞅我妈,还是听到什么动静了。”
和母亲一起走的还有常年陪伴柳霞的两只草原笨,这是一种蒙古獒犬,以忠诚著称。雨果是在上山收拾东西时,发现草原笨没了。他在35万公顷的阿龙山上喊了两三个小时也没回应。期间有朋友上山暂住,三天之后,雨果上去接他们,他们也说没看见狗。一直到现在,草原笨也还没回来。
他最近总梦到母亲,梦到自己在山上参加聚会,大家互相聊天。柳霞从远处走来,边笑边和顾桃聊天,一个人从雨果眼前走过,倏忽间,柳霞消失了,顾桃还在。
一周后,顾桃写了一篇告别信,标题是《再见,兴安岭上的好姑娘,柳霞》,雨果在朋友圈转发了这篇文章:“或许你已不在,或许你一直都在。”

葬礼后的一周,雨果不想一个人呆在林子里。他先飞去了北京,又到南京、南宁、香港和曼谷,一路去往更温暖的南方。临近农历新年,他又折返北京,再到哈尔滨落脚。一路都是一个人。
山上的驯鹿,老孙会帮他看着,冬天林场没什么活,只需要白天把驯鹿吃的饲料撒在雪上。
在北京的一间酒吧里,雨果见到了刚从美国回来不久的摄影师猫,两人因为《雨果的假期》结缘。
2003年,政府启动了鄂温克人的整体生态移民,猎民们失去猎枪,从满归迁到根河,整日借酒消愁,导演顾桃就是在那之后开始影像记录的。猫则作为片子的摄影师之一一直陪着顾桃。
在山上,顾桃暂住在柳霞的帐篷里,他当时觉得柳霞是森林里最诗意的母亲。柳霞说,“太阳是我的母亲,月亮是我的父亲,星星是我的儿子,天上的都是我的。”
柳霞想念星星。雨果出生两年后,柳霞的丈夫骑摩托去敖乡不慎掉到山沟里摔死。她一直酗酒,无力抚养雨果。恰好海拉尔妇联有指标送孩童去外地上学,生态移民的前一年,姥姥做主,把九岁的雨果送去了无锡。

在无锡的一所私立国际学校,雨果上的班叫「希望班」。班里有九十多人,由全国各地的孤儿和特殊家庭的孩子组成。而这所国际学校的其他学生,大都来自殷实人家,他们都有属于自己的假期。只有「希望班」的孩子没有,他们连过年也在学校。
顾桃想着把雨果带回森林,让他和柳霞度过一个假期。
2007年暑假,雨果第一次见到顾桃,正在上五年级的他打完篮球回到教室,一个同学跑过来说,雨果,你爸爸来接你了。雨果有些惊讶地说:“我哪有爸。你别吓我,我爸前几年就死了。”
长头发、留着茂密胡须的顾桃出现了。雨果想,如果自己不是常年坐在最后一排的“学渣”,就该被吓哭了,“我都害怕他是拐卖小孩的。”

顾桃签了担保责任书,把雨果带出来。从无锡到北京要二三十个小时,从北京到海拉尔也有38个小时,雨果困得不行,直接睡在两节列车之间。
他原本没想拍雨果,因为觉得沉重——狩猎文化在下一代中消逝的沉重。但在火车上,越接近森林,顾桃感觉雨果“骨血里有一种血液在苏醒”。在加格达奇,顾桃带他吃呷哺呷哺,雨果问生牛肉能吃吗,顾桃说想吃就能吃,他直接把肉放在嘴里。
顾桃临时决定借个机器,拍下雨果回家后第一次和妈妈见面,这才有了后来的《雨果的假期》。此后连续几年假期,顾桃给雨果买车票,也有朋友出钱支持,接力似地把他送回森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