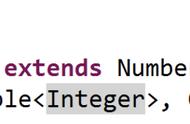一座桥凌驾于故乡的上空,如一根线,缝合了两座山的距离,也把故乡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连接起来。
我的故乡,位于豫西山区。她以前如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躺在群山的怀抱里,憨憨而睡。自从有了桥以后,她忽然睁开了眼睛,翻身而起,不分昼夜地欢腾起来。
我站在桥上望故乡,故乡在桥下望我。我是故乡的的儿子,故乡就是渐行渐远的父母。我从远方匆匆归来,父母站在桥下举目遥望。
桥下有小河在低声流淌,就如我那日益年迈的父母,在喁喁私语。河水清澈潺缓,在冬日暖阳里不急不躁。它如一条蛇在枯*河草和乱石间穿行。窄窄的水面,把故乡的桥缩了又缩。宏伟的大桥,落在水里,只剩下一小段晃动的影子。
我归来的时候,故乡正在为一位老人举行故去三周年纪念。喇叭里传来唢呐的婉转、锣鼓的激烈。悠扬的胡琴声在山沟里回荡,一个甜美的女声,带着水音,把古老的故事,小河流水般,向故乡的山水树木、男女老少心里渗透。那思念的曲音,如一拨又一拨鸟儿,沿着桥的高度,向空中飞去。
站在桥上看故乡,故乡隐身在竹林树木之中。古老的泥土瓦屋,摇身一变,成为一座座钢筋混凝土楼房,沿着山坡前的水泥乡路铺排。雪白的墙壁,蓝色的太阳能板,闪着白光的水泥路,在青山绿水间,与故乡的桥融合,组成一幅巨大的山水画,在我眼前徐徐展开。
回到家中,父母如故乡深处那座老石拱桥一样老迈。他们围坐在火盆前,父亲吸着他的旱烟袋,母亲在打盹,一缕花白的头发,露在深红色的圆帽外边,在火光中来回晃动。看见我归来,父亲连忙从椅子上站起来,母亲也不再打盹,惊呼着:“我的儿,你回来了!恐怕还没吃饭吧。”不顾我的阻拦,立刻去为我张罗饭菜。
老石桥默默地躲在新桥的阴影里,成为新桥的陪衬。走下新桥,一条水泥路从老桥上穿过,送我抵达故乡家的地方,回到父母的身旁。望着八十多岁的父母双亲,我仿佛又回到童年,回到与他们甘相厮守的岁月。我的父母,如老桥,虽然岁月剥落了他们的明艳敏捷,但也打磨着他们的坚强,他们把身躯弓成桥梁,载着他的儿女们走向远方。
站在老家门前看桥,新桥彩虹出岫,老桥亦精神焕发。老桥的西桥头处,已成为故乡经济新的发展点,那里店铺林立,人声喧哗,涌动着叫卖的浪潮。
老桥所在的地方,是盛仓公路的一部分,随着盛仓公路新干道的修成,已沦为走进故乡深处的便道,她退而不休,毅然承担起接纳返乡儿女回家新的使命。
来来往往的车辆,在新桥上穿梭。望着新桥,总能勾起一些往事。
老桥修在横穿袁坪川的小河上,位于新桥上游大约三百米处。小河在老桥下拐了一个大弯,宋仓公路也在这里拐了一个大弯,形成了一个大大的“几”字。宋仓公路从西面五百米处的山嘴上猛拐了个九十度急弯,沿着山坡俯冲而下,在老桥处扭了一个“几”字后,又沿着东面山坡奋力而上,在东面的山嘴处也拐了个急弯,继续攀爬。
老宋仓公路从七十年代中叶修成,到现在已经快五十年了。老桥承担着东来西往车辆的运行,在车辆的千万次碾轧里,桥面已凹凸不平。西面山嘴处,由于弯拐得太急,车祸频繁发生,驾车的人因此而不幸丧命。因此,就有许多怪异故事破土而出。人们说,山嘴处的那个大石头,很像一个老虎的头,下面的石洞就是老虎张着的嘴。这是一条饿虎,每年都要吃几个人。
独拱的老石桥在几十年风雨剥蚀中,已失去当年风姿卓越,二十几米长,不到六米宽的桥身,越来越不堪重负。拱顶上由袁坪学校老校长题写的“胜利大桥”几个大字,已漫漶不清。桥面损毁严重,我每一次从老桥上经过,都要颠簸一阵子。
2019年,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政府要重修宋仓公路,故乡要重修一座大桥,把宋仓公路行经老桥处的那个“几”拉成一条直线。岁末回乡,新公路已开始动工。那个老虎头在挖掘机的反复挖掘里已灰飞烟灭,变成了新桥的西桥头预定位置。
新桥由于疫情干扰,历经三年时间终于架了起来,并于2021年冬开始通车。站在家门前老看新桥,灰色的水泥桥身悬在几十米高的空中,如一条二百多泥长的直线,系在东西两个山嘴之间。车辆在新桥上通行,似一朵朵七彩祥云从故乡上空飘过。新桥如天上的街市,夜晚雪亮的车灯,不时从故乡的天空划过,如仙人夜游,似星光飞驰。
现在,老桥已新铺水泥路面,如枯树逢春,焕发着勃勃生机。
故乡的桥,点燃了家乡人生活的热情。他们把乡间小路打造成旅游景观路,普通民居摇身一变为农家乐,淳朴的家乡人酝酿着乡村振兴的梦。回到故乡,就回到梦里。我在梦里看见,故乡的桥化作一条龙,驮着故乡向梦深处飞去。
【作者简介】程金顺:微信名“空空”,河南邓州赵集人,闲爱读书,舞文弄墨。现为南阳市作协会员,创作有《月季情》《紫藤故人》《幸福的样子》《穰原的冬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