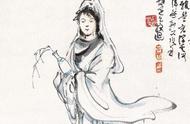现实中巴黎圣母院的一把大火,燃起了不少人对小说《巴黎圣母院》的热情。在微博和微信朋友圈里,极品丑男卡西莫多和绝代佳人埃斯梅拉达的图片又随着火灾后圣母院的残垣断壁刷了屏。
此情此景,很难让人察觉到这样一个事实:《巴黎圣母院》其实在中国是一部非常小众的名著。大多数人压根没读过或读完它,更毋宁说读懂了。我第一次读这本书是在烟台图书馆借来的,当时就发现上下两册《巴黎圣母院》外观差距明显。上册破得不成样子,显然被很多人翻阅过;下册却光洁如初。

《巴黎圣母院》的作者雨果虽然声名在外,但其小说的写作风格对今天大多数人来说却十分“劝退”。在十九世纪法国群星璀璨的小说大师群中,如果说大仲马是“小说家中的小说家”,那么雨果则是“小说家中的散文家”。同样是以历史为题材写作小说,大仲马能将他想涉及的历史巧妙地融入故事的发展中,描述得十分自然;而雨果则“放飞自我”,经常写着写着就以跑题的笔法,硬生生塞给你一段他想说的历史——在《悲惨世界》中,他能抛开冉·阿让的逃亡之旅,硬写了整整一章滑铁卢战役;在《巴黎圣母院》中,他能撇下埃斯梅拉达的命运,兴致勃勃地论述起圣母院的哥特式风格。这种硬加进去的论述,宛如电视剧里插播的广告,很不符合现代读者追求高效的阅读习惯。若不是雨果洞见深刻、笔调犀利,硬塞进去的这些小散文也值得一读,相信他的作品是很难在这个年代保住名著地位的。
抛开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接近一半的这种“剧情掺水”不谈,该书其实讲述了一个现代小说中常见的四角恋故事:巴黎圣母院的副主教克洛德爱上了吉普赛绝色美女埃斯梅拉达,但后者却倾心于外表帅气的渣男菲比斯,克洛德在求之不得后因爱生恨,构陷害死了埃斯梅拉达,自己却被同样爱上这位美女并受其感化的丑陋敲钟人卡西莫多推下塔楼摔死,最终卡西莫多也为其心上人殉了葬。
如果光看简介,这个剧情常见到几乎烂俗,问题就在于怎样解读它。以往受政治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中国人对《巴黎圣母院》的解读牵强到几乎可笑:副主教克洛德和皇家卫队队长菲比斯分别代表了反动腐朽的封建阶级中的教士阶层和贵族阶层,他们伪善、道貌岸然却又贪得无厌;而卡西莫多和埃斯梅拉达则代表了淳朴善良的劳动人民,他们勤劳、勇敢……
即便近些年来书评家们抛开了阶级分析法,对该书中人物的认识依然是脸谱化的:克洛德就是道貌岸然、贪得无厌,而卡西莫多就是面丑心善、品格高尚。到豆瓣等一众书评网站上去搜,仍能看到这种声音占主流。由此可以看出,很多读者的阅读习惯仍跟小孩子看电影是一样的——剧幕一拉开,就要先问清楚:“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然而,一部名著与一本烂俗小说最大的区别,就是主人公在故事情节的推进中,必须有成长、有变化。人物性格的嬗变与张力正是人性小说的最大魅力。而雨果正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在《悲惨世界》中,我们见识了他笔下的冉·阿让是怎样从囚徒、匪徒变为圣徒的,而《巴黎圣母院》更令人拍案叫绝之处,就是他竟然成功同时描写了两个灵魂的“互化”——克洛德的堕落与卡西莫多的升华。
重读一遍《巴黎圣母院》,你会发现雨果笔下的克洛德并非天生是个伪君子,相反,他曾经道德高尚、几近圣人,若非如此,他也不会先后收养失去双亲的弟弟与被遗弃的卡西莫多,更不可能从一个无背景的小教士做起,赢得公众的承认,最终爬上副主教的高位。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接近圣徒的人,在邂逅埃斯梅拉达后却堕落了。他对埃斯梅拉达的最初感情也许的确是爱,却因得不到而变质,最终欲除之而后快。看到心上人被绞死,他所发出的笑声已经是“魔鬼的狞笑”。
而卡西莫多则刚好是克洛德的反面,与很多衍生影视作品热衷于将卡西莫多一出场就刻画的人丑心善不同,原著小说中刚刚出场的卡西莫多实在没啥“心灵美”。作为饱受世人白眼和嘲讽且幼年就失聪的“丑八怪”,卡西莫多的性格刚开始与他的容貌一样乖戾。当克洛德要他绑架埃斯梅拉达时,他立刻就照做了。可见那时的卡西莫多处在一种道德不自觉的状态,只不过是克洛德的奴仆、命运的奴仆。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因为对埃斯梅拉达的感情而赢得人性的解放,完成了灵魂的升华,最终做出了惩恶扬善的壮举。
两个灵魂,一个堕落、一个升华,而他们的催化剂居然是对同一个美丽女郎求之不得的爱慕。这种情节的安排难道不是巧夺天工而又寓意深刻吗?这就是命运。
雨果在序章中说,他写作《巴黎圣母院》一书的动机,就是因为在巴黎圣母院游览时,看到了不知谁刻下的“ANAΓKH”,这个希腊语的“命运”一词其实寓意深刻。自古希腊时代起,西方戏剧、小说的最大特点就是承认并刻画人性在命运的洪流中会身不由己地发生嬗变,也正是因为承认了这种人性的多重和易变,而不是只做脸谱化的分类,西方文明才能领先其他文明率先结出近代启蒙思想的硕果。而雨果用他高超的笔法,就描绘了这样一场人性与命运的激斗:同样是对美的爱,能让一些高尚的灵魂堕落,又让一些卑微的灵魂伟大。人性之复杂、复杂如斯;命运之多变,多变如此。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王昱
壹点号 昱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