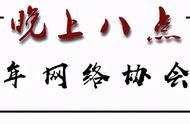扮作“迦陵频伽”跳舞的日本女孩

中国版本的变异
然而在有着自身深厚文化根基的中国,寒号鸟的故事却有着与佛经乍看相似、实则大异其趣的版本,而且这种差异甚至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初就开始了。
提到“雪山鸟”的《长阿含经》早在姚氏后秦(384-417)时便已译成汉文传入,因而中国人并非不知这一典故,但却偏重将之作为因果报应中受惩罚的形象,如中国佛经《佛说善恶因果经》中说:“今身喜露形坐者,死作寒鸮虫。”此经是汉地广为流传的佛经,起始年代不详,在敦煌汉文遗书中唯一有纪年的经卷中记载于唐玄宗先天二年(713年),可见早已流布。
在五代吴越国景霄《四分律行事钞简正记》卷十五则认为,破戒衣(僧尼犯戒条不穿法衣),将受地狱正报,转世为无毛鸟,“无毛鸟即寒号鸟是也。身既无毛,日中不出,夜里方出,作忍寒声等,广如俗书中说之。”
这里说的“寒号鸟”或“寒号虫”,其实并不是印度佛教中所说的“寒苦鸟”,而是源自中国自身传统的另一种鸟。西汉扬雄《方言》卷八:“鳱旦,周魏齐宋楚之间谓之定甲,或谓之独舂,自关而东谓之城旦,或谓之倒悬,或谓之鳱旦,自关而西、秦陇之内谓之鳱旦。”郭璞注:“鸟似鸡,五色,冬无毛,赤裸,昼夜鸣。好自低仰。言其辛苦有似于罪谪者。好自悬于树也。”
这种鸟在先秦文献中就有记载,据说夜鸣不已,到寒冷季节提前预感到阳气将生,即止声不啼。《礼记·坊记》:“《诗》云:‘相彼盍旦,尚犹患之。’”郑玄注:“盍旦,夜鸣求旦之鸟也。”
又《礼记·月令》:“仲冬之月,日在斗昏……冰益壮,地始坼,鹖旦不鸣,虎始交。”郑玄注:“曷旦,求旦鸟也。”所谓“虎始交”,也是因为虎本属阴,预感到一阳将生而交。鸟类夜鸣本不多见,猫头鹰、雄鸡夜鸣在中国古人看来都寓意不祥,《诗经》逸诗之所以说“相彼盍旦,尚犹患之”,可能也是因为以夜为昼,预兆上下失序。由于其鸣叫声如舂谷,故又被称为“独舂”,三国吴沈莹《临海异物志》:“独舂鸟声似舂声,声多者五谷伤,声少者五谷熟。”叫声多就五谷歉收,足见这种鸟在中国人看来很不吉利。
在隋唐五代提到“寒号虫”或“独舂鸟”时,人们的理解都是根据中国原有文献的,与印度佛典无关。中晚唐精通印度与中国典籍的疏勒国僧人释慧琳著《一切经音义》,这是一本引证字书来解释佛经中疑难字词的书,其卷九十九《广弘明集音下卷》引《礼记》郑玄注、扬雄《方言》及郭璞注来解释“独舂”。当代民俗学者张子开认为其注解“并无佛典背景,全是源于中土说法也”。
不过这一典故既然引入中国佛教,就与佛教原有的“众生寒苦”、“八寒地狱”之类的说法联系到了一起。可能又由于“夜鸣求旦”与“寒冷季节”这两点,加上“鳱旦鸟”与“寒苦鸟”读音也有几分近似,于是原本与所谓“地狱正报”无关的这种夜鸣之鸟就变成了中国佛教徒理解的受罚形象。
但这也不能责怪古人,连张子开这样的现代学者虽然旁征博引诸多典籍来讨论中国文献中的“鳱旦”与佛经中的“寒苦鸟”,可他的结论却也认为:它们“当为同一种鸟”。
然而,除了有限的一点相似之处外,两者其实根本不是一回事。
佛经中的雪山鸟鸣声美妙、寓言中且有雌雄对话;而中国文献中却说“鳱旦”是“无毛赤裸”、形象近于罪罚(城旦即城旦舂,秦汉时的重徒刑犯,劳役时身穿红衣,施加刑械,因为筑城挖沟是第一等苦役)、多与阴寒不祥相关[8],甚至预兆五谷丰歉,更不曾提到它是否筑巢,也从来没有雌雄双鸟对话的说法。
从存世文献来看,在很长时间里,中国人所说的“寒号鸟”或“寒号虫”其实是国产的“鳱旦”而非印度佛经中的“寒苦鸟”。不仅中国人自造的佛经中偏重以此警诫僧尼犯戒将受罚为“无毛鸟”,而且通常只说它“寒号”而不像印度传说里那样解释是因它不肯筑巢所致,如清赵翼《途遇大雪》诗:“如曷旦鸟寒自号,比纥干雀冻不语。”这明显是把“曷旦鸟”与“寒号鸟”划了等号。
不过,如果说隋唐时的中国人还能区分这两种不同的鸟,到了元代陶宗仪笔下,它们就有点被搞混了。现在许多人便是根据他所著《南村辍耕录》卷十五的记载,以为寒号鸟“其实是虫”,原文如下:“五台山有鸟,名寒号虫,四足、有肉翅,不能飞,其粪即五灵脂。当盛夏时,文采绚烂,乃自鸣曰:‘凤凰不如我’。比至深冬严寒之际,毛羽脱落,索然如鷇雏,遂自鸣曰‘得过且过’。嗟夫,世之人中无所守者。率不甘湛涪乡里,必振拔自豪,求尺寸名,诧九族侪类,则便志满意得,出肆入扬,以为天下无复我加矣。及乎稍遇贬抑,遽若丧家之狗,垂首贴耳,摇尾乞怜,惟恐人不我恤。视寒号虫何异哉?是可哀已。”
显然,这里说到它“盛夏时,文采绚烂……深冬严寒之际,毛羽脱落”是本自东晋郭璞所说的“五色,冬无毛,赤裸”,但说“得过且过”,却又像是佛经里寒苦鸟的口吻。陶宗仪的版本去除了原先偏重破戒受罚的宗教告诫意味,却转而强调了寒号鸟在一盛一衰时的前倨后恭,以抨击世上无操守的势利小人,不能在顺境逆境时皆宠辱不惊。
由此,寒号鸟的形象完全世俗化、道德化了,而且变成了一个人对不同境遇起落时的态度问题,而不是修行觉悟的宗教议题。陶宗仪讲这个故事的用意并不在于强调未雨绸缪和勤劳,他没谈到筑巢,寒号鸟的“得过且过”在他笔下只是失势时的隐忍蛰伏,是外部境遇的变化,其实和“懒惰”也无关——是季节更替导致它“毛羽脱落”了,勤劳也不能让它长出一身羽毛来。
不仅如此,陶氏的故事版本还进一步强化了寒号鸟的中国色彩,明确说此鸟出自“五台山”,并说“其粪即五灵脂”——据李时珍《本草纲目·禽二》“寒号虫”条解释,是“谓状如凝脂而受五行之灵气也”,中医相信可以治疗心腹冷气、女子血闭等诸症。
这可能是因其名为“寒号”而来的巫术思想,就像中医认为蝙蝠能在夜间飞行是因视力好,因而蝙蝠粪便称作“夜明砂”,据信能有“清肝明目”的功效。
照此说来,既然其粪便是中药,似乎世上真有此鸟,然而自然界却无法找到符合上述特征的鸟类。鸟类中夜鸣的本已不多见,仅夜莺、杜鹃、猫头鹰等,再加上五色、冬无毛(冬季换羽又极其罕见)、自悬于树(只有绿毛幺凤等鸟类喜欢倒挂于枝干上)等特质,实无其类;陶宗仪甚至还说它“四足、有肉翅,不能飞”,那就更近乎不可能了——全世界9000多种鸟类中,不会飞的鸟仅有企鹅、鸵鸟等40多种,至少没有原产于五台山的。
当然,它也并不像有些人所揣测的是鼯鼠,因为历代记载都明确说它是鸟(“得势时自比超过鸟中之王凤凰”的情节可以证明),何况陶宗仪还说它“不能飞”——鼯鼠至少是会飞的。只能说,它与其说是一种自然生物,不如说是一种中国文化中生成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