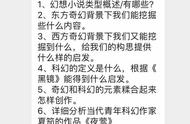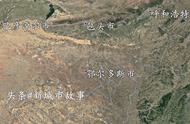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张向阳
刘兴诗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科幻作家,被誉为“中国科幻小说鼻祖之一”。他笔耕75年,出版400余本书,可谓著作等身;他是研究四川盆地第四纪地层的权威专家,在史前考古学、果树古生态环境学和青铜铸造史等方面也有深入研究。
近日记者对刘兴诗进行了专访,年届九旬,他还给自己制定了三个写作方向,他要不断创新,从零开始。


从2019年电影《流浪地球》热映开始,很多人认为开启了中国科幻小说新纪元,成为一段时间里火爆的话题。此外,近年来玄幻小说、影视也成为年轻人关注的热点。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科幻作家,刘兴诗认为,科幻小说说到底,只不过是浪漫文学的一种,通过折射的方式反映现实生活。以前讲科幻小说有两个流派,一个是凡尔纳流派,又叫重科学流派;另一个是威尔斯流派,即重社会学流派。根据现在的情况,远远不能这么划分,刘兴诗对科幻小说做了三个划分:
第一个是重科学流派,以凡尔纳为代表。这个流派最重要的是必须有一个切实可靠的科学主题,有扎实的科学根据。第二个是重社会学流派。以威尔斯的《隐身人》为代表,这部作品看似荒唐,却讲到一个非常严肃的社会问题,一个人企图离开社会必然灭亡。第三个流派就是现在流行的一类,以玄幻小说居多,刘兴诗给它取名叫娱乐流派。娱乐并不是贬义词,哈哈一笑并非不可,只不过在科幻小说中,最好不要成为主流,不管科学主题,还是社会学主题,还得言之有物才好。
“玄幻不等于科幻,这个界限要分清楚。我们有些忧虑,有些人把玄幻和科幻搅在一起,现在有些年轻人、学生喜欢这一类题材,作者也没有脱离这个阶层。故弄玄虚,成为一种玄学,对青年人误导很大。如果忘记了立足现实这一点,只是幻想,没有联系现实,那岂不就是断线风筝、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了?”刘兴诗说,他不赞成将各种无聊的传闻冒充科学普及,科幻不是未来学,也可以审视过去,创作历史科幻。“现在有些科幻作品离不开外星人、机器人、外国人,动辄地球要毁灭,人类一走了之,这些作品对少年儿童影响很大,这个观念要纠正。科幻不能靠胡思乱想、离奇的编造吸引眼球,非科学思维对孩子来说会有误导。”
有人说中国人太现实,天生对科幻小说就不敏感。刘兴诗不认同这种说法。
他认为,有人认为中国缺乏想象,需要国外作品来引导,这种说法其实是对我们文化史的一种忽视,我们先秦时代就有科幻小说《山海经》等,这些作品的想象力非常丰富,在中国古代不少笔记小说和文献里,都充满了神奇的想象和瑰丽的幻想……晚清时期,出现了很大一批想象力丰富的科幻小说,比如吴趼人的《新石头记》等。
谈起新中国成立以来科幻小说发展,刘兴诗可谓全程参与。20世纪50年代,伴随着“向科学进军”的号角,刘兴诗与一批科学家“下海”从事少儿科普和科幻创作事业。郑文光《从地球到火星》(1954年)被视为新中国第一篇科幻小说,标志着新中国科幻小说第一次高潮的到来。“一大批国内文学出版界名家,像叶圣陶的儿子叶至善先生、陈伯吹先生、王国忠、赵世洲等都赤膊上阵,亲自写作。”刘兴诗说。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郑文光、童恩正、刘兴诗、叶永烈等非常有影响力的科幻作家推出了一系列优秀作品。中国的科幻小说曾经繁荣一时。1980年童恩正《珊瑚岛上的死光》成为当时风靡全国的科幻电影,刘兴诗自己编剧的《我的朋友小海豚》(1982年)是新中国第一部科幻美术片,获得意大利第12届吉福尼国际儿童电影节最佳荣誉奖以及意大利总统奖章,让中国科幻作品第一次在国际上升起了五星红旗。
科幻小说的细节必须真实上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是刘兴诗的创作井喷期,他写下了《美洲来的哥伦布》《死城的传说》《陨落的生命微尘》等诸多科幻小说。
因为经常进行野外地质测量,他钻过上百个溶洞。看到溶洞里的地下河,他突发奇想:要是在溶洞里建设水电站该多好!1961年,在上海《少年文艺》编辑的邀请下,刘兴诗发表了科幻文学处女作《地下水电站》。

刘兴诗那些严肃主题的科幻小说是有预见性的。他在1962年发表的《北方的云》,是最早的气象科幻作品。他在文章中认为,内蒙古克什克腾旗沙漠可能起沙对北京产生威胁,就设想运用渤海湾人工蒸发制造雨云,进行空中调水,治理这个近在咫尺的沙漠。
“后来不幸言中,现在影响北京的沙尘暴的确主要来自这个沙漠。”他说。
多年前,他在《蓝色列车》里聚焦铁路运输压力,设想“能否在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之间开凿海底隧道通车”把东北工业区与华东工业区连接起来,减少中间的中转,缩短运输距离。这个设想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会变为现实。
1963年,刘兴诗读英国科学家莱伊尔的《地质学原理》时,其中一句话引起了他的注意。书中说,在英格兰西北部一个湖底的泥炭层中挖出8只独木舟,“它们的式样和大小,和现在在美洲使用的没有什么不同”。据刘兴诗对考古学的了解,加上他对地质研究的认识,可以推断出埋藏独木舟的泥炭生成于四五千年前。那么,有没有可能一些出海捕鱼的印第安独木舟,被横越北大西洋的墨西哥湾流冲入大西洋,一路来到英格兰呢?写作中,为了核实几千年前欧洲大陆到底有没有某一种美洲形式的独木舟,他花了十多年时间来考证。

“细节必须是真实的。”他强调。他总是告诫年轻的作者们:科幻小说在荒诞的外衣里面,有一颗严肃的心。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刘兴诗已经著作等身了,他还注重科幻新人的培养和发现,说,“年轻人比老年人重要”,他曾经向山西希望出版社推荐刘慈欣:“有个写得不错的年轻人,在你们娘子关电站当技术员……”
美好的童话与凡人的幻想刘兴诗笔下的童话充满爱与温情,比如《偷梦的妖精》,前不久刘兴诗和一个加拿大华裔作家共同完成了歌剧剧本改编,正在加拿大制作中;同时也不乏天马行空的幻想,比如《辛巴达太空浪游记》。他说:我的童话“言在天外,意在人间”。
“美的童话”是刘兴诗提出的童话观,他认为长期以来,科普作品中少了“美育”这个重要维度——所以,将“真善美”的创作原则灌注其中,将真的情感和知识,美的意境和语言,善的性灵和追求统一于作品之中,才可能为中国儿童提供优质的阅读作品。
此外,还有《星孩子》《阿雪的世界》《谢谢您,施耐尔太太》等脍炙人口的作品。这些作品充满爱与温情,深受孩子们喜爱。刘兴诗认为,儿童文学要坚持真善美原则,美的意境和语言、真的情感和知识、善的性灵和追求,对当代儿童成长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应尽量减少玩弄噱头的纯娱乐性创作,要给孩子们健康向上的引导。
刘兴诗写的微型小说与现实生活联系也比较密切。《流星雨之夜的梦》,写的是在一个小餐厅工作的姑娘梦想自己的白马王子。一口气跑上天桥,果然就出来一个白马王子。第二天早上,他来了,原来是给这个小店送煤球的小伙子。凡人之间的爱情故事为什么不能写啊?难道爱情只能是王子和公主吗?平凡人的爱情可能更加纯洁和质朴。
还有《中国足球狂想曲》《三六九梦幻曲》也是针对现实生活,关于中国足球和房改等问题,有感而写的。刘兴诗提倡写现在进行时的作品,切中当下的现实问题,平凡人在生活中的幻想也是非常美好的题材。

“过去的成绩我已经忘记了,女排有一句话值得我们学习: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开始。我在科普和科幻方面获过不少奖,国际大奖也获过,可以说曾经上过领奖台,现在一切都归零,我要从新开始,我现在每写一部新的作品都要改变形式和内容,不断创新。”
刘兴诗要从全新的领域试一下,他给自己制定了三个新方向。
一是动物小说,现在国内的动物小说作家,想象的比较多。写这类小说,要懂动物,有研究的基础。而我们地质工作者常常遭遇野生动物,工作中不可避免进入它们的生活领域,有许多真实的体会。“在北冰洋地区科考时,我钻过北极熊的窝,考察过它的习性,连故事里面写到的爱斯基摩人用的都是真名;在南方科考时,几乎每天都跟眼镜蛇打交道,还有狼等野兽,不但熟悉它们还研究它们的习性和生存环境。”刘兴诗说,在这一点上,地质工作者有天然的优势。
几十年都在户外跟地质、野生动植物打交道,刘兴诗写的大部分动物小说都是有切身经历的,比如《蛇宝石》是当时在热带地区野外考察时碰到眼镜蛇的启发,《最后的北极熊》则是在北冰洋考察期间与北极熊打交道而写下的作品。在动物小说中,他最喜欢像杰克·伦敦的《荒野的呼唤》、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反映人与动物关系的作品。
他还想写探险小说,“地质工作者跟驴友相比,也有优势。”刘兴诗说,他认为,现在有些探险小说是野外俱乐部的驴友写的,他们选择最危险的地方去穿行,走过去就是胜利,是一条线的体育活动,他们的勇气固然可嘉,但他们深入宝山却空手而归。地质工作不一样,我们在地质图上把一个地区分成很多小方格,科考中每个地区都要走到,都要采样、取岩石标本、进行测量、搜集地质信息,是面的工作而不是一条线。刘兴诗注意到前不久15名驴友擅自进入黔西县素朴镇水西洞险些被困的消息,他自己在广西野外地质工作时也曾遇险,被困在一个迷宫一样的溶洞里,依靠自己的经验逃生。他说:“在地质工作中一定要注意安全,现在有些探险小说只讲冒险,有些年轻人冲动之下就去冒险,非常危险,要避免这种观念,一定要有专业人士来写。”
“民俗与童话的写作,文学童话表现真善美,我也想试一下。我给青岛出版社写了《少年徐霞客游记》,孩子们非常喜欢。”除此之外,他对古籍研究、古代神话、古诗词也很感兴趣,他还想从古代文化中挖掘出适合青少年读的作品,像《山海经》《水经注》等也是很合适的题目,这些他都做过研究,“长江、黄河除了青海省那一段,都徒步沿江河进行过考察,不只是走,每一段都有研究成果。”
找记者、求报道、求帮助,各大应用市场下载“齐鲁壹点”APP或搜索微信小程序“壹点情报站”,全省600多位主流媒体记者在线等你来报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