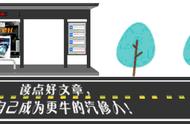我们以医者仁心的名誉,守护着每一位患者的生命线。这不仅是坚守的神圣使命,职业情操,更是我们的医生医德的道德水准。
——题记
他很忙。从早晨踏进办公室,或者说更早在家的时候,去单位的路上,都有可能接到不可意料的电话,但绝不是朋友邀约喝早茶,吃午饭,晚上喝酒等一类话题,那是来自科室、病员、病员家属关乎病人身体状况、病情恶化、生命垂危等人命关天大事的电话。就是在没有准确时间下班回家的路上,同样会接到类似的电话。细心观察的人会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噫——这个人的手机总是“挂”在耳朵上吗?怎么来来回回都在接电话,走路那样匆忙,与熟人打招呼,回应的也就是挥挥手。因此,每天到岗上班的他,换好工作服第一件事便是开简短的晨会,听取昨晚的工作汇报,安排部署今日新的工作。随后就是与医生、护士们一道查房,掌握病人身体状况的第一手资料。回到办公室,要不就是写病员身体状况分析,就是写工作总结、检查汇报材料、发言稿,还要随时听从医生、护士的“呼唤、调遣”,有时还得作好随时出差、开会、学习的准备。因此,他一天的工作用忙得不亦乐乎、一塌糊涂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本次采访尤为“艰辛”,历时时间最长,跨度最久。不是他不配合而显“清高”,不是因工作忙碌而“推谢”,更不是因工作的“特殊性”而拒我于门之外,让我坐冷板凳。那确实是一个特殊而特别的“战场”,他就是一名冲锋的战士。就他所在的科室,经与医生、护士短暂接触的所见所闻,方知他们真的是一群与时间赛跑的人。医生巡视病房后,回到办公室,立马坐在电脑前,作病历记载、分析、判断、查资料,或是新建病历档案;护士们都忙着给病人打点滴、测体温、量血压、送药、做各种必要或特殊的护理。一个医生稍有一点空暇时间,不等端起茶杯,就有护士在“呼叫”,或是病人、家属敲门探头或直接进门相对而坐。医生如去病房,病人或家属咨询病况,就没有个时间的概念了。在办公室如遇问诊的病人、家属,一个,二个也就罢了,要是三、四个这种情形,就是一个上午,一个下午,一天就这样忙忙碌碌而过。因此,说他们没有时间按时吃饭,按时下班,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说他们忙得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既不夸张,也不过分,这就成了一种现象。从医职业的付出与艰辛可见一斑。
他们最为感叹的是:一天的时间怎么就过得这么快啊!
架着一副黑色眼镜,寸长的小平头,微胖的脸庞略显人到中年的发福,一身洁白的白大褂,衬托出他的干练精神,更显医生职业那神秘而崇高使命与责任感。他,就是我要采访的人,攀枝花市中心医院,肿瘤科主任——杨胜利。就是这样一个团队的领头人,医生、护士、病员都尊称一声“杨主任”。胆大、调皮的年轻人当面叫“杨主任”,背地却喊“头”或称一声“老大”,但无论怎样称呼,都带有一种尊敬的口吻。
基于杨主任工作的“特殊”性,每每预约上、下午采访时间不是被推迟就是被取消。即便抽点空闲刚好坐下,未等你张口或提问,不是有医生探讨工作,就是被病人或家属上门咨询,要不就是接一个同为咨询电话,于是起身,手一摊,一个对不起的手势,一个歉意的笑脸,不无幽默地对我说:我就是一个整天被他们“安排、调遣”的人,随即转身离去,至于何时回来,就没有准信。从未畅快地交谈过,唉,预约下一次,又该是什么时候与时间,心无数,好生无奈。因此,我只能以马拉松或者叫“挤牙膏”式地进行采访。其实,我也是挺有耐心的,那就等吧,为的是让读者认知在医院有这么一群天天与病魔、死神打交道,争时间,创生命奇迹的人,记录医生、护士是怎样忙碌每一天的。
我以为,与一名“肿瘤科”的主任交谈,要么是直入主题,要么就是话题特别深沉、沉重。不料杨主任开口便对我说道:你知道在医院大家最忌讳,不愿意,不能说出口的是那两个字吗?我心一愣。想,他怎么会这样提问?随即摇头,表示无从猜测。他笑着向我伸出食指和中指,我以为他要说:胜利!然快人快语的他却摇头说道:不,——再见!我好生茫然。他接着说道:是的,无论是什么地方,任何时候,我们与亲人、朋友分别时,都会礼节性地脱口而出——再见!下次再见!因为“再见”有再一次见面的含义,所以,在特定的地方,特定的环境,特定的人,譬如说殡仪馆,譬如说劳教所,又譬如我们医院。面对出院的病人,就不易用这两个字。有人就委婉地对我们说过:大夫啊,感谢您们的救命之恩,您们辛苦了哟。出院了,我是既想见到您们,又怕见到您们,有两个字我就不说了,也怕说。我们点头表示理解。但为表达心情,他还是说道:但不说点什么,心里实在过不去,那就感谢您们的大恩大德,祝愿您们一起都好。有的甚至是下跪磕头,也不说“再见”两字。这样,每当面对康复出院的病人,出于“忌讳与尊重”的缘故,为营造欢乐、开心、难忘的气氛,我们的医生、护士们就手持鲜花,再三祝福:恭喜出院,快乐回家,身体健康,幸福生活!大伙热情握手,挥手道别,互道:珍重!保重!
放松一下,是为了不让我们交谈的话题不显得那么的沉重、凄切。他看我一下,笑着继续说道,生活就是要笑着过。坦诚地讲,对于本次采访,于我的心而言,确实的略感有那么点的“沉重”,甚至是还有那么点的恐惧害怕。从人们正常的心理来讲,对于一个健康者来说,最怕,最忌讳,也是最不愿意议论、听到的就是谈及一个人生病,尤其是谈及“癌”这样敏感的字眼,更不愿谈及死亡这样的事。但作为一家医院,一个科室,一名医生,却也是一个绕不开且必须面对、直视的话题。
用你们文人的话讲:只有了解历史,方能珍惜和爱在当下。那我也从我们医院的院史讲起吧。呵呵,豪爽,直奔话题,真是爽快。旋即,就像影视演员很快地进入了角色的他,在我耳旁响起讲述的声音,脑中却像是放映机放出的一部由黑白到彩色胶片画卷式的历史电影……
1965年初,为了响应*主席提出“好人好马上三线,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和那句:“攀枝花建设不好,我睡不着觉。”的话。中国大地从南到北,五湖四海汇集了那么多热血沸腾、朝气蓬勃的优秀青壮年们,为实现建设祖国美好蓝图,心向一个地方,人朝一个方向,肩负历史重任,勇挑历史重担,迈着矫健的步伐,个个精神抖擞、意气风发地向不知地名的地方挺进!来到这个沟沟坎坎、荒山野岭的不毛之地,扎根于无水、无电、无路、无车、无住房的攀西大裂谷——攀枝花,
奔赴三线,奔赴攀枝花。那是时代吹响的进军号角,那同样是青春芳华的绽放!
不毛之地闪动着生龙活虎的青春倩影,乱石山岗有着精力充沛的时代弄潮儿。开发建设攀枝花,尤为重要的是除要保持青年人一颗火热的心,奋力拼搏精神的同时,还要有一个强壮的肌体,健康的体魄。要确保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医疗必须先行。于是,在荒野的山地,条件还未完善,基础相当简陋的情况条件下,一支支由上海、天津、四川、川医、重庆组建的医疗队先后到达渡口市(攀枝花市前市名),在仁和区的大田镇,于2月组建并宣布了一个临时医院,医院无名。要叫也叫“临时医院”、“战地医院”吧。同年4月,渡口市医疗机构的第一所医院——“渡口医院”正式成立,并迁建至东华山,也就是现“攀枝花市中心医院”的前生。

创业初期渡口市的医务工作者们,同商业战线的营业员一样,虽不像奋战在厂区、建筑、高炉、矿山、铁道旁的创业者们那样,置身于火热的工地,但是,他们同样的不畏烈日炎炎,不畏凹凸山路、风沙弥漫,那样豪情壮志、朝气蓬勃迎地着朝阳,顶着烈日,哪怕是鼻血横流,哪怕坡陡路滑;哪怕滑跌摔跤,哪怕划伤腿脚手臂,背着红十字药箱,走工地,进帐篷,将创业者们急需医药用品送到手中,好生感人,好生温暖。
开发、开拓、创业时期的渡口市,正因有了这些创业者们那种艰苦卓绝的奋斗,忘我奉献的精神,有了商业、医疗、运输等群体坚实的后勤保障,才得以确保一九七零年七月一日的高炉出铁,成昆铁路全线竣工开通运营。就是这些前辈,在共和国三线建设史上写下了气吞山河、撼天动地悲壮而又辉煌的一页。凝练出让后人永生难忘,永远铭记,永远传承、发扬光大的三线攀枝花精神。
一九七一年,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研究所专科医师朱学清、钱景文医师来“渡口医院”开展工作,并成立了内科血液专业组;一九八七年八月,毛光菊主任创建的肿瘤专业正式开诊,与血液专业共同组建内三科(即现在的肿瘤血液科);一九九七年八月八日,四川卫生厅发文,同意成立“攀枝花市肿瘤防治中心”,挂靠攀枝花市中心医院。
我是一九八六年七月从重庆医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渡口医院工作的。
22岁,正值一个人青春年华的黄金时间,也是一个人多梦时期。那时,有人给我提及过“渡口市”,说那里的地理地貌有点像重庆,是一个正在轰轰烈烈搞生产建设年轻的工业城市,除了工厂、工棚、工地,就是席棚子、油毛毡、干打垒、红砖平房和高不出四层楼的楼房,没有像样的商场、影院、医院,条件极其艰苦,就是所谓的商店、书店都是用芦席子、油毛毡搭建成的。正因这样,我也热血了一回,豪情了一把,怀揣志向,大学毕业后义无反顾地奔赴渡口市,来到了这个叫“渡口医院”的单位工作。眼中的渡口医院已由1965年组建的“帐篷临时医院”到4月搭建的油毛毡、平房的“渡口医院”发展到已有红砖平房,四五层红砖楼房,已有办公室、门诊部、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住院部这样“高大气派”的“渡口医院”。我先被分配到消化内科,1996年从北京进修回来后,根据组织安排,去了由毛光菊主任创建的内三科(肿瘤血液科),并于1997年担任科主任至今。到渡口市次年的1987年,“渡口市”被国家正式命名为“攀枝花市”。“渡口医院”更名为“攀枝花市中心医院”。
是啊,同其他各条战线的青年人一样,那个时候的我们也正在青春昂扬、豪情壮志时期,对自己的工作投入了极大的热情,虽说条件、环境都还简陋,但丝毫影响不到我们对工作的积极性,那种刻苦学习技能劲不比攀钢高炉温度的热度低。工人师傅们在高炉炉台前战高温,我们的专家、老师在手术台前战酷暑,每每看到他们从手术台上下,那汗湿的一身衣,精疲力竭得连饭都不想吃的样子,除了心痛的同时,也曾暗想,我什么时候才能顶上去?在得到他们的指教,学到精湛的医术,治愈解除病人深受病痛带来那份痛苦,健康快乐出院,回到自己的家中,那该多好啊。这样一想,学习、专研业务的积极更高、更主动了。幸运的是我得到了老专家、老医生及有经验同事的传帮带的指导、指教下,开始慢慢地进入到自己的工作状态,进入医生的角色中。再就是争取到外学习的机会,不断地请教、充实、提高自己,将学得的医术技能应用于临床。
杨主任,三十几年过去了,你已步入中年。你治愈了多少病人,肯定是无法记住的,你看你现在都当主任了,验证了那么一句话:付出终有回报。
惭愧,惭愧!就像你们作家一样,不一定是为了出名、成名,但一定是喜欢文字写作。每当面病人的病情,总想医治得更加的“完美、优雅”或叫风情浪漫,诗情画意些,从而彻底根治,留下的遗憾疑难杂症,就成了下次攻克的课题。
哟,你挺会联想的啊。其实,你每天都在“书写”优美的文字,只是表达的方式不同罢了。当你有时间集册成书,就是一本厚厚的学术著作了。是有西学研究价值的。
呵呵,你是拿我开心吧?这样,你教我怎样写作,等我退休后来完成。
堂堂的“重医”毕业生,还在乎笔上功夫,那不是小儿科的事吗,只等你有时间就可动笔。
那意思是我退休后有事可做了,不怕寂寞了哦,哈哈哈……
嗯,杨主任,关于你们这个肿瘤科,让人听到总有点毛骨悚然的感觉。你的朋友会不会在意你的职业,对你敬而远之呢?
怎么可能?上班时间穿“白大褂”,我是医生,下班时间脱下“白大褂”,我就是我了。照样与朋友逛商场超市,吃烧烤喝啤酒,喝到尽兴时还不是要拼酒,那就是豪放,没有与人不同之处啊。只因职业不同,我接触的都是癌症病人。不过,癌——这确实是一个令多少人生畏,惊骇、恐惧、害怕的字。这个病,使多少病人身心受损,摧毁了多少人精神意志,同样的让病人家属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而伤感而悲切。谈“癌”色变是不可回避的共识,这里就不作过多的注解。记得在我工作的时候还未曾听说过这字,听到最多的就是肺结核、肝炎晚期,就是白血病都叫“学友病”,而不称“血癌”。
出于情感与人性化的考虑,我们走进任何一家医院,是看不到“癌症科”字样的,取而代之的是“肿瘤科”三字;同样是出于人性化考虑的缘故吧,每一家医院肿瘤科的“住院部”都设不为显眼偏僻的僻静处。有人就调侃说,同为医院的医务工作者,病人的“守护神”,你们肿瘤科的医生、护士们与院里同仁们一道忙碌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但你们更像是秘密工作的“地下者”。哈哈哈……
那,那我今天就当着你的面,“恭维”你们一翻。你们是不张扬,不显山露水,一群高调做事,低调做人的医务工作者。是你们——崇高而圣神的医生,当今的华佗,用自己精湛的医术,满腔的热忱,精心的护理解除病人的痛苦,拯救病人的生命,使他们获得新生。当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敬礼!
没想到,杨主任竟也“严肃”起来,很快幽默地回敬道:谢谢首长夸奖,为人民服务!一阵轻松气氛调节后,杨主任继续说道:说实话,每一个医生的技术和医德不是靠“恭维”能活出来的。作为医生,你知道,我们最害怕的是什么?
我怎么能知道,只能无助地摇头,听他讲述。
告诉你,不是病人患的什么病,不是病情有多么的严重,也不是我们医生付出了多少的心血。我们最怕的是病人不能正视自己的病因及现状。在还没有确诊医治的病因,就猜忌、判断,自己给自己下结论,自己放弃自己。不是有那么一种说法吗,好多的病,不是医生医死的,是自己给自己吓死的。放弃治疗,就意味着放弃生命;还有一“怕”,就是病人家属,在得知病人病情后,不是很好地与医生沟通,积极配合治疗,而是一次又一次地追问:医生,这病还能有救吗?还能活多久?我们该怎么办啊?等等。于是五花八门的提问,无理地取闹,与医生争吵、辱骂,更有甚者对医生、护士动手。我们只能不厌其烦地解释,忍受委屈,忍辱负重地工作。对于医学、医术那是要讲科学的,病因很多且复杂,还有病人身体的个体差异不同,而出现不同的症状。因此,我们医生没有一个人敢确切而肯定地回答你:三年、一年、三个月或是下周、明天、后天,更不能说出上午、下午、晚上。
所有的病,都得先找清、找准病因,再对症下药,慢慢医治。盲目的下结论,那是对科学规律的不尊,同样也是对人格的不敬。
攀枝花市中心医院肿瘤科,同样的住院大楼,同样的科室、病房、医生、护士。如你没有看见,注意到楼外墙体上那“肿瘤楼”三个字,不知这里是“肿瘤科”大楼的病房,你绝不会有什么样的心里压力与“恐惧”。除了治病,就是救命。常言道:人命关天!工作中的状况是不可以放下或耽搁的,这是一群与时间赛跑与死神争夺的人。即便是下班,他们也不可能准时准点地离岗,还要接受病人或家属的咨询,做心理疏导,整理或新建病人的病历档案,录入电脑系统等。做完这些,稍微的舒缓、平抚一天紧绷的神经,调整一下回家的心绪,带着倦意离开办公室,至于人在走,心在想些什么就不得而知了。
攀枝花市中心医院肿瘤科,环顾四周,上白下绿宽敞的内走廊,墙两旁挂着有关癌症基本常识与预防以及医生与病员交谈的照片。同别的科室一样,因病员较多,有点“人满为患”的感觉。像是猜着了我的心思,杨主任对我说道:来我们这里就诊、住院的病人,除了本市的,还有来自西昌、木里、会理、会东,云南丽江、永仁、大姚、华坪的病人,甚至还有昆明的病人。我“哦”了一声说:怪不得你说上班屁股就沾在“板凳”上,什么时候下班回家没有定数,看来是真的。他处理了电脑屏幕上要处理的相关工作事宜后,对我说:走,我先带你去看看我们的科室。
说实在的,眼前的病房,远不像医院外科病房的病人,有头缠绷带的,手臂腿打石膏的,头、脚被“吊起”的,看着都令人不寒而栗。眼前一间间明亮透光的病房都很安静,病员与病员,家属与家属们在轻言细语地交流。走道上那些增加病床上的病人,在家属的陪护下,有的在睡觉或闭目养神外,有的安静地玩手机,看视频,刷抖音,只见医生、护士脚底下像是安装了一台“滑轮车”,一会儿从这个病房“滑”出来,一会儿又“滑”向另一间病房,无暇接听响铃的电话,没有时间看或回复短信。彼此交流都是急促的工作“交代”。忙碌的身影与平躺的静养,尽显病房一动一静的画面,看不出一点的惊恐、惧怕感。

短暂的感观,我以为,医生和护士们既是病人眼中不背“枪”的战士,又是与病魔、死神打交道的勇士;是解除病人疼痛、疾苦、病患的在世“华佗”,更是将微笑、温暖、自信送给病人的白衣天使。同其他科室一样,这是一个有着集体荣耀感,敢于担当,勇于奉献,将微笑与自信带给所有向战胜“死神”病人的团队。他们站在了危重病人人生的最终点,却也是危重病人人生再生的新起点。每一个康复出院的病人,除了好好地活着,如不那样,都有愧与医生护士们的辛苦付出。
杨胜利是接过第几任主任们交出的接力棒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所肩负起肿瘤科主任的重担既艰巨,却也倍感荣誉的神圣且自豪。
如果说,一家医院,只是为了收治病人,医治患者,那恐怕是每一个医生、护士职责操守与使命的体现。让每一个前来就诊的患者,享受到最佳、最优的医疗服务,不仅仅是为了一个治病,能得到医生给予最大的关爱、关怀,健康快乐地出院,以得到生命延续的最佳值,最大值,活出自己最为精彩的人生,我想,这才是每一个医务工作者共同的心声与愿望。所以,我们才以崇敬的心情和眼光尊重与尊敬医生这个高尚而又圣神的职业。
只见杨主任的手指在桌上轻轻地敲击,发出微小的敲击声音,我知道,那是一种酝酿,是故事的开始。果然,他挠挠头发说,哎呀,嘿嘿,想告诉你的故事太多,该从哪个人讲起呢?
我提议说道,就从你们医生办公室墙上的锦旗说起吧。他哈哈一笑,你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要是把收藏的锦旗都展示出来,那就像唱山歌一样,三天两夜也唱不完。我还是选典型的实例讲吧。这个,这个凡是来到我们科室的病人,不用问,不用说,仅凭那张“入院通知书”,病人及其家人都“绝望”二字写在了脸上,你就能看出“癌”所带给人们心灵及精神负担与恐惧。先给你讲个例外的,其实不然,这样的实例很多,这是较典型的病例。
那上世纪的80年代后期,我们科室收治了一个病人。不用问,仅看他那一张脸,不说是医生,就是稍有点常识的人都能看得出,这不是一般严重的“肝炎”患者,那一张蜡黄毫无血色的脸就能反映出他的病情——肝硬化、原发性肝癌。病情有多严重,不仅是病人痛苦,生存时间也有限,中位生存期半年左右,所以说人们谈“肝癌”色变,一点也不夸张。为了确诊,我们请了各科室的专家来进行会诊,确信无疑的结论就是:原发性肝癌。也就是说,我在他的病历上写下“肝癌”的字样。换作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开出了一张“死亡通知书”。
针对他的病情,我们制定了一套严密而详细的医治方案。再看他,知道自己的病情后,好似患伤风感冒一般的毫不在意。当我对他提出各种注意事项的时候,他却满不在乎地对我说:有那么严重和吓人吗?我才不行,咱们活着瞧。我嘴上夸他乐观、坚强,心里确实为他捏把汗。这应是我收治病人中少有的乐观者之一。除了嘱托他特别的腌制辛辣、粗糙食物和烟酒茶不碰不沾以外,他是该吃的就吃,该喝的都喝,该睡的就睡,就这样“没心没肺”快乐地活着。有时间就与我们医生、护士天马行空的聊天,打嘴仗。其间还下过两次“病危通知书”,通知其家属料理后事。不知是老天不收,还是他的“命大”,还是天生的乐观,他居然都闯过死神关。“病危”几天,他就像是缺瞌睡一样,睡上几天,精神稍好转,他就又活蹦乱跳地与病友说笑吹牛皮,还得意地说:老天爷想收我的命,不是那么容易滴,门都没有。他有常鼓动病友,向他学习,与死神抗争,看谁斗得过谁。每天都乐呵呵的,这种病人的精神真的难得,也值得称赞。病友们给他取的绰号就叫“乐呵呵”。
一个人难得有这样乐观的精神。要是病人都能这样,那该有多好啊。我也情不自禁地称赞说。
说的是。有一段时间不见“乐呵呵”的影子,问护士不知道,问病友都摇头。可有人传言说,“乐呵呵”是怀疑我们的医术,偷偷上省城看病确诊去了。一听这样的消息,不知真假,但我的心确实给气“炸”了。这家伙,不假外出也道罢了,还跑到省城去,这不仅是对我们的不信,也是给我们打脸啊。要去也是我给你开转院证啊。想当初,为挽救他的性命,我们研究了多少次医治方案,医生护士们费力多少的心血。哦,病情好点了,就可以随意的乱跑?真是乱弹琴。
当“乐呵呵”再次出现在我们科室的时候,仍是笑嘻嘻,嘻哈哈的样子,却真的是遭到我的一顿很批。一头雾水的他直叫“冤枉”。原来,是他们单位的共青团组织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要到云南昆明的石林、滇池搞活动。听到这个消息的他,死皮赖脸地缠磨,非要去不可。这是一个判了“死期”的重病人,出来了事,谁敢承担责任?他跑到团支部*办公室声称:“坚决去,必须去。就是死了由自己全权负责,与组织无关。”经不住他的死缠烂打,又磨不开同学情面,在通盘考虑后,他参加了这次的五四青年活动。来回没有出一点病情状况,又活蹦乱跳地回到病房。还大言不惭的告诉病友,我是宣布“死期”的人,活一天,赚一天,就是死了,有同学背我回来,我怕谁啊。呵呵,嘿嘿……
嘿嘿,这样的病人,你说是该批评呢?还是该表扬?要是他胆小,听到“肝癌”,怕是早就吓死了。但由于他的乐观,通过医治,体检、照片,他肝上的病灶居然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