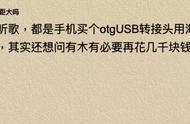读到海子《九月》这首诗纯属偶然,甚至现在我也说不清究竟是怎么撞上它的。
对于当代的大多数诗歌,我都敬而远之,因为我觉得有些诗太过朦胧、晦涩或者荒诞,我无法理解;而有些则太过浅陋、庸俗或者牵强而丧失了诗歌应有的意味。
作为受过一点教育的普通人,我希望读到的诗歌必须有一点内涵,但不能陈义过高;有一点格式,又不能匠气十足、内容空洞。
由于“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句话在学生嘴上和一些文人的笔下太流行,海子又有着巨大的生前身后名,我才有意去查阅了一些有关海子与他的诗歌的信息,但我一直没有喜欢上他。
说句得罪海迷的话吧,在我印象中,与不少诗人和艺术家一样,海子是一个有着精神疾患的人,虽然他的诗歌充满了各种哲学式的思考,我却无法接受他对于自己生命的态度。
作为诗人的海子的自*在中外历史上当然并非个案,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甚至可以算是诗人的一个传统,中国古有屈原,今有海子以及稍晚的顾城,外国有前苏联的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美国的西尔维亚·普拉斯等一大批人,其中有一些人的死亡还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或者社会的悲剧。
但总的说来,他们的自*尽管使当时和后世的很多人感到哀伤和惋惜,却也暴露了他们各自内心的脆弱和思想的极端。
《九月》我也不懂,在网上搜索别人对它的解读文章时,我又意外得到了周云蓬吟唱这首诗的音频。
诗人、盲人歌者周云蓬苍凉、幽远、伤感的歌声对我很有吸引力,我把它作为QQ空间的“说说”来转发,也把它暂时设为背景音乐了。
广东湛江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张德明教授有一篇论文---《海子<九月>的存在主义读解》,这个解读应该是相当专业、权威的,很多其他人提到或者评说海子的《九月》时也多引用这篇文章作注脚。
张教授的解读之高度与深度,我当然根本无法企及,不过,我也从中得到了一些启发,虽然未必能自圆其说,我仍然愿意与大家一起来再探讨一下,以下就是我个人的理解。
我们先来看看原诗:《九月》
目击众神死亡的草原上野花一片
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
我的琴声呜咽泪水全无
我把这远方的远归还草原
一个叫木头一个叫马尾
我的琴声呜咽泪水全无
远方只有在死亡中凝聚野花一片
明月如镜高悬
草原映照千年岁月
我的琴声呜咽泪水全无
只身打马过草原
读完这首诗,我觉得应该把它叙事的顺序颠倒一下,也就是说,它叙事的起点应该是(我---叙事者本人)“只身骑马过草原”,接着才是“我”在“草原上”的所见、所思,其间,内在与外在形成尖锐冲突,由于外在不断向内在侵袭,内在又不断形之于外,以致“我的琴声呜咽泪水全无”,思维分层次推进,诗人则通过对这一句的反复吟唱来逐步强化自我的感受,最后是“我”的思绪导致了行为的宿命式回归,诗行则形成一个往复的圆圈。
不然,则诗篇开头的“目击”莫名其妙,“我”何以在场?缺乏必要交代。而诗人之所以并不在开头交代这一点,正是在有意制造一种突兀与神秘的效果,同时,它还使人产生强烈的、想探究的*,就像大街上的路人偶然目睹一场交通事故。
现按这个思路,我把全诗重新排列、分节如下:
(我)只身骑马过草原
目击众神死亡的草原上野花一片
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
我的琴声呜咽泪水全无
我把这远方的远归还草原
一个叫木头一个叫马尾
我的琴声呜咽泪水全无
远方只有在死亡中凝聚野花一片
明月如镜高悬
草原映照千年岁月
我的琴声呜咽泪水全无
只身打马过草原
从意象来说,“草原”可以看作人世或者说现实社会;信则有,不信则无,“众神”代表信仰;“风”是一种个人理想或者说是“我”崇信的某种价值,比如说,自由;而“马”则是飞逝的时间。
如《红楼梦》中所说,人生死于世间无非“赤条条来去”,“我”就是这样孤独地来到“草原”的,但“我”却意外地“目击众神死亡的草原上野花一片”---这句话有歧义,到底是目击了“众神死亡”呢还是“野花一片”呢?我的理解是先看到“众神死亡”,然后野花盛开。就像上世纪八十年代(这首诗作于1986年),中国原来的社会信仰轰然坍塌,新的价值观体系根本没有建立,而社会经济却因为自由的扩张迅速繁荣了起来。
“众神”是形而上的,而野花却是物质的、具体可见的,“野花”的生长较少受到人为的干预和约束,它们是自由的,然而这种自由还不是“我”期待的,我期待的是“远方的风”---在一个理想国度里,精神上彻底的自由。
可是,在现实的“草原上”,“我”全然感受不到“风”的存在,也绝看不出它有任何实现的可能,它离“我”遥远得不可想象。空间上的距离可以通过行走来缩短,而“我”的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却无法消除,因而可以说它“比远方更远”。
意识到这一点,我为自己感到悲哀,然而,“我”没有这种精神上的自由,只好强行按捺住这种悲哀,使自己不至于落泪,却还是不免要“呜咽”。“我”的“呜咽”甚至也不能通过嗓音发出,而只好通过“琴声”,也就是我的诗行,这种隐晦的方式发出。
理想是对现状的否定,但它也只有在现实中实现才有意义,而更矛盾的是,理想与现实的距离感正是现实赋予“我”的。现在我不希望有这种距离感,“我”打算要把这种“远方的远”依然归还给现实社会。
既然在现实中无法得到我想要的思想自由,那么我的诗行、我的生命还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没有肉体,我的灵魂就会像风一样来去无踪,那么它任何时候都不会丧失自由,任何人也无法剥夺它。一把琴拆开,无非木头和马尾,而“我”的诗行,也是要用文字和生命来书写的。既然“我”的文字和肉体限制了我的思想自由,使“我”产生了理想与现实无法相通的距离感,使“我”得不到我想要的思想自由,那么“我”连这些也一并放弃吧。
和现实中八九十年代的经济繁荣是靠摧毁旧的信仰来实现一样,理想中思想的绝对自由也是靠现实中肉体的死亡来实现的(也许正是基于这个理解,海子最终自*)。现实中,我的思想被分解为诗行,我的诗行被分拆为文字,那么我的肉体死亡之后,灵魂归一,我曾经不得不诉之于的文字和不得不分解的思想,应该可以重新凝聚起来,并与宇宙(代表空间的“远方”、代表时间的“千年”)相和谐,从而呈现出我的思想生机蓬勃(野花一片)的本来面目吧。
这一点,人类历史---“如镜高悬”的“明月”作为旁观者可以为“我”的观点作证,也对此时此刻的草原进行审视和纪录。
“我”来的时候是只身,而“在草原上”,我也找不到一个同路人、一个灵魂的伴侣,走的时候也只能是“只身”。
“琴声呜咽泪水全无”,“我”的全部悲哀在于,理想与现实、肉体与精神、个人与社会的不协调,“我”为此一唱而三叹。
“生”是“死”的开端,“死”是“生”的起始,“我”在自己的内心对人类历史以及“我”自己此刻所处的社会状态和精神状态进行了一番审视,并对自己的未来作出了预想和规划,我认定,肉体的死亡才是心灵解脱的唯一方式,我的灵魂会由此获得永生。
尽管“我”已经意识到了有些冲突是宿命的或者不可调和的,作为人世的一个孤独过客,“我”已经迫不及待地要离开了,但是,“我”还没有确定是否立刻让自己的肉体死亡,或者说,还没有选择好死亡的方式,所以,“我”只得催促时光(打马)加速流逝,好让自己承受痛苦的时间缩短一点。
生命,毕竟是人最珍视的东西,一般来说,人的自*念头不是突然产生的,自*行为也不是突然实施的,它必然先有铺垫、有挣扎,甚至也可能,如某些人所说的,自*倾向是基因决定的。从这些思索和感悟中,我们可以看出,海子的思维已经进入了一个死胡同,即使他暂时还没有走到生命的尽头,他离自己的末日已经不远了。
实际上,绝对的自由在现时、现世的任何地方都不存在,它也不可能存在于过去或将来的任何地方,它纯是人头脑里的乌托邦。
鉴于理想的不可实现,诗人常常不自觉把自己放在受害者的位置上,他的痛苦也是从这一点上生发的。
从语言中流露出来的性格看,海子是偏执的,他始终不愿意妥协,“千年岁月”,草原都是这么过来的,他却仍然为自己的生存状态感到悲哀不已,他仍然不愿意“与世推移”而打算以死亡来求得解脱。
但三唱“我的琴声呜咽泪水全无”,我们也可明显看出,海子是承受着巨大压力的,虽然单从本诗我还无法得知这些压力具体从哪里来。
从全诗来看,海子思考人生的终极问题并试图找到出路,他是一个有着深刻思想的人;而本诗语言简练、寓意深刻、结构精巧,的确反映了海子作为一个成熟诗人的深厚功力。
但22岁就思考人生的终极问题,并终于在25岁时就主动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则无疑显示了他作为普通人的早慧、偏执与脆弱。
从局外人的角度来说,我也觉得海子的思维并不是严谨的,比如,他认为“远方只有在死亡中凝聚野花一片”,逻辑上并不严密;他的思想不够成熟、胸怀也不够宽广,他太过执着于自身和个体的感受,无视或者看不见他人。
但无论如何,对于我们的社会而言,多年以来,我们一直没能让一个杰出的诗人看到任何新的希望和出路,而是眼睁睁看着一个高贵的生命一步步走向自*,既是我们社会的损失,也是我们这些苟活的人的耻辱。
另外,我一直没弄明白诗题,我不知道“九月”有什么特别的含义,有没有哪个老师可以指点一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