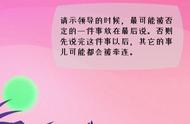每年这个季节,土地流金的颜色就悄悄爬上远近的禾和苞谷。而我,也急切地从城里溜出,走进父亲充满希望和喜悦的田里。
屋前屋后的田垄,秋色涂满层层叠叠的一行一格。而每一行每一格,又都充满丰收的幸福。秋收前的夜晚,风顶着一轮明月,听稻谷唠唠叨叨地述说。一江秋水,糅合着青黛与月辉,逶迤于高山脚下。
回乡的第二天早晨,天只微微亮,浓雾还漫卷在田垄里与土地呢喃,父亲就站在土坪里,朝贪睡的我喊:“收禾!”睡眼惺忪走出门,秋天的凉快径直撞来,浇得我身上叭叭打颤。抬头,月西沉,从一丛黄叶的缝隙里漏了下去,很快不见踪影。
我们这地方山多,高峰对峙,沟深壑险,对于外面省力省时的收割机,只有羨慕的份。我和父亲用肩膀抬着一台打谷机,沿田垄深入。
都说起早的鸟儿有食呷,可因为我们起得太早,鸟儿还眷恋在暖和的窝里。待我们的脚步声沙沙逼近,它们才倏地惊醒,一翻身,极不情愿地匆匆飞走。
我们把打谷机放进田里。我摸了把镰刀,俯身放倒一片稻禾。太阳逐渐醒来,从雾气里露出圆脸,钻上东山斑斓的山坳。不远处听见人响,是沙沙收禾的响声,他们踩动打谷机的欢快,把我感染得心头兴奋起来。
一个男音骤然吆喝了一声山歌,高亢又火辣。父亲直了腰细听。我也挺起身来,阳光之下,田垄里金黄重叠着金黄,一层一层顺着梯田的走势起伏,爬上高高的山腰。我深深地吸了口潮湿的空气,满腔的清新。
山脚前我家那栋黑瓦苍檐的房子,炊烟升腾,我希望母亲能把柴火灶上黑漆漆的腊肉煮了。在城里,老家的地道腊肉不知馋了我多少回。想着腊肉,我的劲莫名大了,一只脚踩着打谷机的木踏板,带动脱粒的滚筒转得飞快,双手握紧稻穗翻动抽打。
今年的禾,父亲种得好,施肥也精,所以谷子筋骨好,沉甸甸的。不一会,我便踩了一尾柜。然后父亲稍微择除了禾叶,捞谷进了竹箩。一担竹箩,足足一百五十斤重!我用肩膀掂了掂。
秋收越来越热烈,一挑挑谷子被我们肩挑车拉,晒干入仓。村子里的稻田剥脱了稻谷的金黄,仅剩下高高低低黝黑的稻禾茬子。
收完谷子和苞谷,时间也到了一年农历的九、十月份。村里会在这个时候准备庆祝秋收的节日。
这时,村里就异常热闹,选择一处大田垄或者一块大土坪,家家都拿来了新谷米,还有新苞谷发酵酿的酒,然后把木桌子排好,全村老小一桌一桌地坐满。父亲此刻必定喝点小酒,尽管他平时滴酒不沾。母亲也会喝一点,红着脸庞吃菜。有人借着酒气,在稻田里跳最古老的舞蹈。这种舞蹈的步法和舞姿单一、夸张,却透出一股山间的热情和朴拙。
父亲讲,新化过去都是打着锣去开荒挖土的,人们在地头一字排开,敲一锣挥一锄,整齐划一,泥土翻边。这种多人统一的劳作,我没见过,但从人们的舞蹈里,我大约能领略其风采。
节目的高潮在捉稻田鱼。一丘田里的鱼养了差不多一年,尾尾膘肥体壮。起先人们忙着追鱼捉鱼抢鱼。等鱼捉得差不多了,就有人突然闹起来,把身边的人推进水田里,用泥涂满他们的身子。谁身上涂的泥巴多,其实是对他今年辛劳的褒奖,也预示他来年的收成好。一转眼,凡村里种田的好把式,都被人涂得只剩两只眼睛骨碌碌转动。
月亮已近梢头。稻田里的人跳了舞,唱了山歌,捉鱼打闹,不知不觉,人也便倦了,三三两两说着高兴的话,相携回家。
稻田,好像又回归了宁静。
而身后,稻田中的篝火还在燃烧,火红火红的,像门板上一串串线穿的红辣椒。
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作者:刘群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