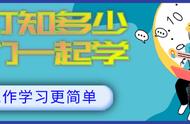撰文|王志军
另一生:诗人的诞生
先来想象一个场景:整整90年前,遥远的东加勒比海向风群岛中部,一座被称为圣卢西亚的火山岛上,诞生了一个黑白混血的小男孩。当时那里还是英国殖民地,为茫茫大海包围,远离大陆和主流文明,居民是各移民种族的混融,没有完整的传统、文化、历史,闭塞、原始、混乱,可以说是一片虚无。如果不是因为地球是圆的,那里多半会被认为是世界的尽头。而这个小男孩,婴儿期就失去父亲,由当教师的母亲养大。他会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呢?

这很令人好奇。面对极端的落后和匮乏的教育,他成长中如何摆脱普遍的命运而获得更高的视野呢?看起来困难重重,几乎没什么希望。就像他多年后回忆的,缺少文化滋养,“秧苗随意插入土壤,其扎根的深度与种族绝望的程度成反比。”要想在贫瘠中长成大树,非要点奇迹不可。
艺术就是这个奇迹。
或者说,人这种神奇的生灵,和艺术结合起来时,能获得的超越阶层、文明代差的力量比通常想象的大得多。一开始这男孩承继父业,学习绘画,开发了心灵视觉。之后通过诗歌,找到了更强、更自我的声音。在他后来的自传长诗《另一生》中,他记录最初读到一本诗集的神秘瞬间:
每过一行
读的人就流露出一行行的欢欣
撩动着他周围的空气
就从这本书里,另一生恍若重新开始。
这个另一生,是他作为诗人,而不是社会人的一生。其开端是自我觉醒,投身艺术的新生——诗人的诞生。从此男孩看待这个世界,就有了一种更高的视野。现在读者应该知道了,这男孩就是沃尔科特。成年后,他在《安的列斯:史诗记忆之碎片》中的一段话正好对应了这重生的瞬间:“现在,一个男孩打开了练习本,心怀感恩的喜悦,又有些受宠若惊。他在页边的限制下,写下一行又一行诗;那里或许闪耀着无名岛山顶的光,珍藏着我们的微不足道。”无名岛,微不足道——被漠视的地方和事物。可对诗人来说,这就是他的全部。
我们必须得再次强调他面临的环境:没有传承,欧洲文化是陌异的,对群岛既有蔑视,又有令人不舒服的驯化。当地仅有的文学,更多表达着控诉与绝望。失忆的历史和当下的沉重,梦魇般压着每个在那儿生活的人。要想开创道路,一切都要自己摸索。

好在那里有丰富、绚烂的事物,艰难却真实的生活。在失忆的国度,所有东西都值得被记忆。他要做的,正是为这一切未被命名的事物命名。这何尝不是一种幸运呢?《另一生》的结尾说的就是这种感受:
我们有福了,因为我们拥有一个处女般、不曾涂画的世界
我们拥有了亚当的任务,为万物命名。
面对纷繁的有待命名的事物,其激情和振奋可以想象。于是我们读到,《热带动物寓言集》中的炫目的博物志,《圣卢西亚》对村庄、动植物不厌其烦地罗列,《星苹果乐园》透过海岛看世界——他在这些事物上倾注想象和隐喻,赋予它们独特个性。他也一直关注那里正发生的事:人民、分裂的文化、族群的命运。
这就让诗人的诞生,有了双重含义。一方面是亚当式命名的开始。在蛮荒海岛,带着惊奇清点一切。命名在他这儿有特别蕴意,有文明传承的诗人没这么多未被书写的事物。为此,他把各种技巧,隐喻、方言、叙事等,都用在了他开创的事业。另一方面,他感到自己必须为正发生的事担起责任。要寻求改变,单靠个人太过艰难。但脆弱的心灵,以良知驱动,同样能赋予现实以历史感:不只沉浸于事物的美,还深刻领悟其内涵,及其与人的处境的关系。
亚当、克鲁索、上帝
随着他的成熟,那种最开始就现出端倪的身份意识,凸显了出来,成为他创作的一条主线。
他身上的黑人血脉和热爱的英语带有的宗主国色彩是有冲突的。“我如何能无视非洲,又能活下去?”

就像童年进入青年,身份焦虑带来忧郁、痛苦、迷茫甚至绝望。但这一点他无法选择,必须接受。他意识到西方文明和加勒比海本质间的巨大鸿沟,西方语系中加勒比不可能被准确描述。当地人都面临同样的困境,向往变革又渴望和解。可以说,身份中内含的冲突,构成了他诗歌的原生动力。
克罗索成了他表达身份意识的一个象征。这个笛福小说中的人物,流落荒岛,身陷没有文明历史的虚无之地,也因此获得了命名的初始特权。这和诗人内心感受是对应的,一种包含着苦涩的幸福:“感谢你们被逐出伊甸园后,带我领略了另一个乐园的奇妙。这就是我继承的遗产,你们赠予我的礼物。”《漂流者》《克鲁索的日记》《克鲁索的岛》等直接写克鲁索的诗,通过原型改写,反思了加勒比地区的民族性和尴尬处境。亚当是乐园中的命名者。而克鲁索,第二亚当,是一个文明世界的遇险者,历史被割断,处境更荒凉。他不能只靠亚当那种无忧无虑的纯真来看世界,发现诗意,而要从新的处境中出发创建新天地。
而这个新开创的世界,必然是西方认知所不习惯的。他笔下的加勒比事物变成了主角,那些丑陋、平庸的人,变成了平民英雄,史诗人物。《另一生》中他自问:“为什么要为这些哑巴的事物哭泣?”因为这是他自己的世界,不写,就永远消失了。
他从未摆脱克鲁索那种巨大的孤独。在世界各地旅行生活,似乎只让他更渴望家乡。在英格兰游历的诗《火车》:“有一半的我,还在家乡。”身份焦虑无法通过远离得到消解,写于美国的《北方与南方》:“当我从小地方的药店,收到找回的零钱,/收银员的指尖,依然对我的手,畏缩不前/仿佛她的手会被它烧焦——好吧,没错,我是猴子。”而在《纵帆船“飞翔”号》中,身份意识的反思上升到了新的高度,人和故土的关系,意味着更多的责任和使命。他终生带着这样的身份感和对加勒比的忠诚,将焦虑转化为创造力,以人类的爱慢慢平衡孤独带来的疯狂。即便是无法带领民众提升的苦恼,也因诗中逐渐成型的新加勒比而部分地缓解了。
于是这个加勒比的命名者,第二亚当克鲁索,变成了上帝,或者说:诗人沃尔科特。他比克鲁索在更高的层面,为其造物注入思想和性格。他晚期的诗轻盈,凝练,开阔。始于《仲夏》,在《浪子》《白鹭》等诗集中愈加明显的焦虑缓解后的自如,意味着使命即便不能说最终完成,也带来了一个更好的结果:和解。
一种新语言
语言作为诗人的命名工具,效力在其独特性。
正如沃尔科特自己说的,“要想摆脱奴役、获得拯救,就必须铸造一种超越模仿的语言,一种具有启示力量的方言,让它为万物命名。”诗人当然是要做语言的发明者,革新者。但沃尔科特的情况,因他私生子般的感受而有些复杂。在英语特别是古典文学的继承权上,他多少感到有点不合法。他强烈渴望创造新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