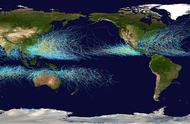陈柏霖饰演的张士豪
和单纯的怀旧不同,《蓝色大门》不是自顾自地营造青春的纯净梦境,它让观众将目光投向自我,重新看见和捡拾成长中那些尴尬无措的体验。它没有那么痛楚和剧烈,但一个人总会在长大成人的节点,内心经受震荡,迎接一场属于自己的小小风暴。
电影在拍摄时使用了大量的近景和特写、长镜头,人物充分地占有画面。观众可以清晰地观察少年们被汗水打湿的发梢、被风吹起的衬衫角、闪躲的手、在面具之下的拥抱,完成一场对青春的观看。台北燥热的夏天里,轰天的蝉鸣和海岸边的风声有时甚至盖过了人物的对话,笔头与纸接触时沙沙作响,夜晚的游泳池被月光照得发亮,好像能闻到消毒水的气味。所有感官都被浸泡在那个漫长的夏日,这一生少有的怎么浪费也过不完的夏日。
2
得知自己的作品入选了「21世纪20部最佳台湾电影」,易智言发表感言时说,「当外人说《蓝色大门》很甜,我觉得孤独根本是苦。」
影片里有诸多重复的呓语。张士豪跟在孟克柔后面,反复问,「哈喽,那你为什么要我吻你?哈喽?」「你什么意思嘛,你什么意思嘛,你什么意思嘛?」在拍《蓝色大门》前,导演易智言常常给麦当劳拍广告,他觉得,小孩子或是青少年说话的特色之一,是会不厌其烦地重复某一件事,语言更丰富的意义反而得以浮现。
和张士豪理直气壮的复读不同,孟克柔的复读是沉默、缺乏勇气的,她不停地在体育馆的墙壁上写,「我是女生,我爱男生。」在体育馆,面对张士豪对她的一遍遍声讨,她只是用尽力气站立着,最后终于抵挡不住,跌坐到椅子上。他们都想在这样的重复中得到自我的确证,像对着洞壁呐喊,回返而来的,依然是少年单薄的声音。

孟克柔在体育馆墙上写自己的心事
易智言在1997年开始创作《蓝色大门》的剧本。大约在13岁时,他完成了性向的探索。但那个年代,他无法就此与外界沟通和求援,再加上内向的性格,从青春期开始,易智言感到边缘和寂寞。他把自我发现的过程、对成长的体认,交给了孟克柔和张士豪来呈现。
电影里那面写满学生心事的墙,是来自易智言的阅读经历。他看过一本书,里面讲述了一个这样的故事:一个毕业生为了写论文,回到母校访问学妹,学妹带她去看同学们曾经在墙上写下的文字,大概的意思是,「为什么社会上不能容许像我们这样的人?」看到这个细节,易智言很惊讶,「这几句话带给我很大的震撼和灵感,我们要怎么样才能来表现年轻人走过青春,到此一游的心境呢?所以才有那面墙的出现。」
影片是可以品尝出孤独的苦涩的。林月珍收集了张士豪有关的物件,却连上前打招呼都感到胆怯,只能抱着双腿掉眼泪,「我是不是很没用?」孟妈妈告诉孟克柔,丈夫死后,自己「就是这样活过来的」,接而望着漫漫黑夜,许久才闭上眼睛。得到答案的孟克柔,眼角湿湿的,和所有期盼长大成人、驱散青春期的无奈和不安的人一样,她也好想赶快看到「活过来」的那一天。
电影上映的第二年,易智言到拍摄地附中做交流。学生们问起,蓝色大门为什么是「蓝色」的?影片最后孟克柔提到妈妈和体育老师,是什么涵义?他说,请不要问这样的问题,因为他也不知道。「我觉得台湾的教育给学生一个很奇怪的观念,好像什么东西都一定要有意义……但是为什么它们一定要有意义?」
正身处青春的人,不会思考那些意义,他们有充足的时间发呆、幻想,然后忙着跑来跑去实施它。他们不必学会珍惜,有权利将时光白白浪费在看似毫无意义的探索上,用生活透露给他们的那些可有可无的线索,勇敢地揣测自己的未来。
在那本电影同名书籍的扉页,易智言写道,「我们生命中,曾有某个夏天值得我们记忆,我们不会记得哪个政客的胡言乱语,不会记得谁是第三个上月球的太空人,然而我们会记得某个夏天,我们多么出乎意料地突然变成大人。」
和青春期相比,成人生活逐步丧失这些间歇和闲适,以至于失去了发现惊奇的能力。显而易见的是,这个节点正在被紧绷的教育模式提前,自由伸展的时间被压缩,一个百无聊赖的夏天变成了稀缺品。那些至今仍在重温《蓝色大门》的人,试图在电影的时光里,把那个夏天过一遍,再过一遍。

3
《蓝色大门》的拍摄时间,2000年,台湾影视正在实验性的摸索过程中,生机勃勃地探讨不同的生命话题。导演易智言承认,那段自由探索的时期,让他有机会用一些名不见经传的青少年来当电影的主角。
拍摄《蓝色大门》时,桂纶镁只有17岁,读高二。遇到副导演的时候,她正在西门町捷运站的出口等捷运,因为和男朋友吵架,心情糟糕。那天她穿着篮球背心,头发乱乱的,脸很臭,却被副导演认为,这就是孟克柔。从小受到家庭周全保护的桂纶镁,是个单纯天真的乖乖小孩,听说要拍戏,很干脆地把照片和电话留给了他们。她是如此容易信任别人,易智言形容她,「从具象到抽象,从外在到内心,都非常干净。」
陈柏霖同样是在西门町被副导演看见的,那时他正在街边埋头吃冰。他比桂纶镁大几个月,在准备大学升学考试。即使对演戏一窍不通,他还是接受了邀请,理由朴素,只是想过一个不一样的夏天。他害羞得要命,导演易智言第一次跟他面试、做访问,碰到回答不上的问题,他就笑,就躲,要溜到台下去。
在成为张士豪、孟克柔之前,他们跟着其他的角色候选人一起上了两个月的表演课,渐渐熟悉彼此。两人有天然的默契,常常同时做出一样的反应和动作。最后他们都得到了出演机会,成为了后来「一起长大的好朋友」。
多年以后,陈柏霖和桂纶镁在诸多采访中讲起拍摄的细节,都提到导演易智言对他们的影响。面对两个同样在青春中摇摆的少年,比他们年长20岁的易智言给他们推荐了许多书籍和电影,提醒他们,「你要很诚实地面对你自己」。
片中有一场骑行的戏,桂纶镁骑着脚踏车,突然很想一直骑下去。于是她这么做了。剧组人员冲她呼喊,她也不肯停下来,就这么没有尽头地骑着。她后来接受采访时说,「那时候我才17岁,好像就是跟着所有的体制和期待去前进。孟克柔这个角色和易智言导演,打开了我对于人的认识,我好像之前都没有关于一个人既定的框架。因为这部电影我才开始问关于自己的问题。」

桂纶镁饰演的孟克柔
结束拍摄的那天,她哭得伤心,不停地掉眼泪,害怕这辈子再也遇不到这些相处了几个月的好朋友。共同度过的夏天很快结束了。离开剧组,桂纶镁回高中继续完成学业,考上了淡江大学的法文系。大三那年,她前往法国留学了一年。在法国,她读波伏娃,和同学们讨论自己的存在,思考究竟要成为怎样的人。
她和陈柏霖都选择了继续做演员,但找来的大部分片约,都要求他们骑单车、演高中生。为了摆脱既定的框架,21岁那年,陈柏霖选择离开台湾,去香港拍摄《千机变2》,「其实真的很不想去,但是逼自己一定要去。」听不懂粤语,难以适应电影工业的快节奏,他抽了人生的第一支烟。那时候他对自己很失望。他记得,自己小时候明明最讨厌爸爸抽烟,还因此吼过爸爸,说以后绝不会变得像他一样。
再后来,他去日本发展,有时候白天拍戏,晚上给别人画插画,学乐器、旅行,逼迫自己学语言和当地文化。用他的话说,这20年是用「探险」的心态在工作,像一场持续良久的游学。他慢慢接纳了生活的跳跃和随机,努力消减自我厌恶和怀疑。
2012年,29岁的桂纶镁因为作品《女朋友,男朋友》成为金马影后。同年,陈柏霖通过《我可能不会爱你》拿下第47届金钟奖视帝。两个好朋友一直保持紧密的联系,桂纶镁描述这些年二人的关系,是「并肩走在夜里」,共享恐惧与幸福。
由于《蓝色大门》的烙印实在太深刻,在公开的场合,导演易智言绕不开的问题是,和陈柏霖、桂纶镁是否还有联系?还有没有再一次合作的可能?他在个人主页上做过一次回应:「这几年怕见到他们,因为充满躲债的歉疚,感觉像生了孩子没有养都丢给保姆。」
这当然是一句玩笑话。在他看来,他们三个人已经是家人的关系,如果真的要为家人做一个东西,必须要好,要真诚,这需要时间。
这20年,易智言也走得十分辛苦。《蓝色大门》后,他的作品屈指可数,不超过4部。最近一部作品《废弃之城》花费了他12年的时间准备和制作,经历了合伙人散伙、母亲病重、向公众宣告出柜,剥离掉电影,他觉得自己的人生一无所有。这部动画电影,讲述的依然是一个少年的故事,是易智言坚持发出的属于「局外人」的声音。
第57届金马奖颁奖典礼上,《废弃之城》获得最佳动画长片奖,颁奖嘉宾正是桂纶镁和陈柏霖,易智言发表获奖感言时,他们在舞台侧边注视他。桂纶镁甚至因为心情激动,快站不住,牵起了陈柏霖的手。三个人在台上深深拥抱。
2018年,《蓝色大门》的取景地——台北师大附中的游泳池即将拆除。作为对泳池的告别,师大附中在蓝色的泳池底部放置了幕布,露天放映了一场《蓝色大门》。那天,易智言、陈柏霖、桂纶镁三人又聚在一起。他们穿着校服,跺脚跳舞,重演了一次两人在片中用鞋子踩毁情书的场景。「17年后回到这里,感动得像个孩子一样,情绪也暗涌着无法言喻。也许……我们真的留下了一些什么了吧。」陈柏霖这么回忆道。
作为后来者的我们有幸看到,20年后,离开那扇蓝色大门的他们分别成为了怎样的大人,并为此长舒一口气。还好,他们都还在诚恳地创作和表达,没有丢失年少的朋友,还在热烈生活。20年前的每个细节都有一个令人慰藉的回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