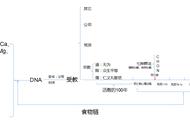在生命的最后阶段,
甚至在死前三个月之久,
很多病人与他人的话语交流减少了,
心灵深处的活动增多了。
这是濒死的人的一种需要:
离开外在世界,与心灵对话。
(2)
一项对100个晚期癌症病人的调查显示:死前一周,有56%的病人是清醒的,44%嗜睡,但没有一个处于无法交流的昏迷状态。
当进入死前最后6小时,清醒者仅占8%,42%处于嗜睡状态,一般人昏迷。所以,家属应抓紧与病人交流的合适时刻,不要等到最后而措手不及。
随着死亡的临近,病人的口腔肌肉变得松弛,呼吸时积聚在喉部或肺部的分泌物会发出咯咯的响声,医学上称为“死亡咆哮声”,使人听了很不舒服。
但此时用吸引器吸痰常常会失败,并给病人带来更大的痛苦。应将病人的身体翻向一侧,头枕的高一些,或用药物减少呼吸道分泌。
濒死的人在呼吸时还常常发出呜咽声或喉鸣声,此时可用一些止痛剂,使他能继续与家属交谈或安安静静地走向死亡。
没有证据表明缓解疼痛的药物会加速死亡。
听觉是最后消失的感觉。
所以,把你想说的话,告诉他吧,
即使他已经无法回应,但他依然听得到。
不想让病人听到的话,
即便在最后也不该随便说出口。

(3)
这几天,我一再地想——为什么,为什么直到现在,我才读到了这篇文章?
我的父母已先后去世,一直到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光,我都没有能够读到这样的文章。我痛恨自己在无知中铸成大错。
所有的误解都基于一个前提:我们和临终者已经无法沟通,我们有太多的不甘和执念,我们的至亲已经无法讲出他们的心愿和需求,我们只好一意孤行。
但做这些正确的事,
其实只需要一点点起码的医学常识。
我想起在父亲临终前,我抓着父亲的手,他像山泉一样凉。我命令弟弟说:爸爸冷,快拿毯子!现在才知道,他其实并不冷,只是因为循环的血液量锐减,皮肤才变得又湿又冷。
而此时在他的感觉中,他的身体正在变轻,渐渐地漂浮、飞升…这时哪怕是一条丝巾,都会让他感觉到无法忍受的重压,更何况一条厚厚的毯子!
我想起直到父亲咽气,医生才拔下了连接在他身体上的所有的管子,输气管、输液管、心电图仪…同时我们觉得他几天几夜没进水进食,总是试图做些哪怕是完全徒劳的尝试。
母亲清早送来现榨的西瓜汁,装在有刻度的婴儿奶瓶里,我们姐弟每天都在交流着爸爸今天到底喝了多少水。
现在才知道,他其实并不饿。
那时候,
他已从病痛中解脱出来。
天很蓝风很轻,树很绿花很艳,
鸟在鸣水在流,
就像那些诗歌、童话里描述中的那样,
他已经准备好,去到另一个世界了。
这时,哪怕给病人输注一点点葡萄糖,都会抵消那种异常的欣快感,都会在他美丽的归途上,横出刀枪棍棒。

(4)
父亲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在最后谵妄状态中,却忽然变得喋喋不休,而且是满口的家乡话。我担心他离我而去,我想喊住他,他毫不理会。
现在才知道:那个时候,
他不是在于外界交流,
而是在他自己的心灵中。
当时的父亲,也许正在儿时的童趣中,
在意气风发的青春中,
在他一生念念不忘的美好往事中——
回现这一生所有的美好。
我们应该做的,只是静静地守着他,
千万千万不要走开。
临终者昏迷再深,也会有片刻的清醒,大概就是民间传说的回光返照吧,这时候,他必要找他最牵肠挂肚的人,不能让他失望而去。
我还记得父亲此生表达的最后愿望,是要拔去他鼻子上的氧气管。可是我们两个不孝子女是怎样地违拗了他的意愿啊,我和弟弟一人一边强按住他的手,直到他的手彻底绵软。
现在才知道,对于临终者,最大的仁慈和人道是避免不适当的、创伤性的治疗。
不分青红皂白地“不惜一切代价”抢救,
是多么的愚蠢和残忍!
最终,父亲走了。医生下了定论,护士过来作了最后的处理。一旁看热闹的病人和家属说:“你们这些儿子、女儿,快喊几声爸爸啊!”
可不知为什么,我竟然一点也哭喊不出来,弟弟也执拗地沉默着。
直到现在我才知道:
听觉是人死前最后消失的感觉,
爸爸没有听到我们的哭泣,
不知道他会高兴还是难过?

(5)
自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起,就都要面临死亡。每一个人。
我明白。没有人能逃得开这最终的一课。只是现在才知道,大自然竟然把生命的最后时光安排得这样有人情味,这样合理,这样好,这样的自然而然。
是自作聪明的人横加干涉,
才让亲人的死亡,变得痛苦而又漫长。
一天上午,我突然发现我对面的同事泪流满面,一个50多岁的男人的失态让我诧异。
忙问他怎么了,他告诉我看了这篇文章,想起了他母亲临终前情形。他说就像上文描述的那样,觉得母亲冷了给她穿保暖的衣服,盖厚厚的被子,觉得母亲几天没有进食,不停给她输液。
他母亲很想回家,可他坚持让她住在医院。他自认为尽了孝心,可是没想到给她带来莫大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