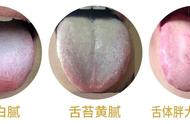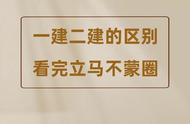来源:中国青年报

早高峰时的西二旗地铁站 实习生 杨子怡/摄

姜胜正在巡道

王凯华在做列车出库前的最后准备

曹宇正在晚高峰前点名

金台夕照站的线路工休息室

轮乘中心堆放的速溶咖啡
北京地铁每天都在发生让人意想不到的故事。有的地铁司机一天要喝11包咖啡,地铁司机每天要重复960多次手势动作。一名巡道工每个月都会磨破5双棉袜,每年要检查12万个铁轨零件。早晚高峰时,车站广播员要把一句话重复1800多次。
平均每月都会有20多只鞋,70多个背包玩偶挂件掉落在西二旗站台下面的道床上。站务员曾在那里捡到一个装有5本房产证的公文包。
已经沿着10号线,把金台夕照到分钟寺这截北京最繁华地段走了630多次的巡道工,却从来没有走进过头顶上的任何一栋建筑。
一家地铁站旁的便利店,每天接待的第一位顾客,永远都是地铁员工。
北京运营着全世界最繁忙的地铁系统,仅地铁司机就超过6000名,相当于两所大型中学的人数规模。2017年共有38.7亿人次乘坐北京地铁,比同年全国铁路客运总运量都要多。
这座城市几乎一年开通一条新线,只用了不到15年时间,地铁线路图就从“一圈一线”变成了现在的“电路板”,新开通的16号线每公里造价达到了12亿元。
很多人每天都乘坐地铁,却对这个庞大的系统知之甚少,白天乘客不懂地铁夜里的黑,24小时它一刻都没停止过紧张的运行。
司机
11月一个周二的下午5点,地铁司机王凯华冲了当天的第七包咖啡。列车从休息室外驶过,桌子上的杯子和钢勺因振动发出轻微的碰撞声。起身前,他停顿几秒感受心跳的频率,希望咖啡能让它略微加速。
再过15分钟,列车会准时停靠在北京地铁1号线四惠东站的站台,王凯华要接替交班的司机,开始紧张且单调的晚高峰运营。他要对抗的,是困意——这个职业最大的难题之一。
为了提神,地铁公司曾安排专人在东单站给司机发“秀逗”糖(一种口味较酸的糖果),也曾给司机配发“重力感应提示器”,挂在耳朵上,只要头低到一定角度,提示器就会振动。
如今,在四惠东站司机休息室里,十几箱速溶咖啡堆放在墙角,足足有两米多高。这是向司机“无限供应”的“福利”,最多的时候,王凯华一天喝了11包咖啡。
在四惠东站,即便是十几年的老乘客也容易忽视,由东向西站台一侧的白墙上,那扇并不显眼的铁门。
1号线的“轮乘中心”就隐藏在这扇铁门后面。司机把地铁从苹果园站开过来后,下车在这里休息,等待下一列需要自己驾驶的班次。从家里赶来上班的司机也会先到这里,换上制服,做开车前的最后准备。
大部分时候,这间屋子都保持着沉默的氛围,司机们偶尔有几句交谈,也多与工作有关。
王凯华的话同样不多,这个29岁的地铁司机已经有7年的“驾龄”,这样的时间足以改变他的性格。
王凯华每天的工作场所是不到3平方米的驾驶室。为了防止眩光,列车行驶时驾驶室里不允许开灯。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他都穿行在幽暗里,前方是看不到尽头的隧道,周围是一成不变的灰色水泥。
驾驶室和乘客车厢间是一道不到10厘米厚的铁门,把列车隔离出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边是明亮如白天的车厢,每天载着不同的人,发生着不同的事情。他们聊着不同的话题,充斥着各式各样的情绪。
另一边的王凯华只能感受到“孤独和枯燥”,他已经在同一条线路上往返了2500多个来回,每天要重复960次标准化动作:指示灯或者信号灯亮起时,他都要用手势指出来,同时还要说出相应的口令。
“我闭上眼就能判断出车的位置。”他熟悉每一段区间的特点,能感受出列车撞击钢轨时,发出的不同声响。那些有细微差别的颠簸,他感觉也“相当明显”。
他还记得司机考试时,有一项科目是“猜速度”。考官把速度表遮住,考生要凭感觉估算出列车行驶速度,“一般误差都不会超过1公里/小时”。
1号线一共70辆列车,在乘客眼里这些地铁都是同一副模样,但王凯华清楚每一辆车的“小脾气”:有的车劲儿大,满载时牵引依然不吃力,有的车制动好,进站停车稳。
在1号线隧道里,他更喜欢从西往东开,因为“车站越来越宽敞,站台上的人越来越多,心情也跟着舒畅些。”相反的路线,只会越来越压抑。
他羡慕那些开地上线路的轻轨司机,“至少能看到一年四季的变化,晴天阴天、下雨下雪时都不一样。”
每次跑完一趟车,王凯华都会到轮乘中心的门外抽一支烟,那里永远都不会只有他一个人。门口的两个垃圾桶里,烟头已经堆出了尖。
在隧道里待久了,王凯华每天都要重新适应光明。他最怕列车从四惠站驶出隧道的那一瞬间,刺眼的白光直射到他的眼睛,甚至能让他短暂“失明”。
还有些光明是来不及准备的。几乎每天,车厢里都会有乘客隔着玻璃对着驾驶室拍照,每次闪光灯突然亮起,王凯华的眼前就会一片煞白,然后陷入几秒的黑暗。
乘客对地铁司机的好奇不仅付诸相机。王凯华在工作期间没功夫回头看,但是驾驶室的挡风玻璃上能隐约反射出背后正在发生的事。有时隔离门上那个竖条形的玻璃,从上到下挤满了人头,“每个人都对我的后脑勺笑,很诡异”。
还有人干脆边看边敲门,想要一个不可能得到的回应。
地铁司机除了忍耐枯燥,精神也要时刻紧绷。
北京地铁站的站台前端,都设置了一个计时器。早高峰期间,王凯华从苹果园站启动列车时,计时器开始从“100”倒计时,这说明列车在这一站早点100秒。列车开到国贸站时,头顶上的计时牌已经开始正计时,这意味着列车已经晚点。
在1号线,正计时的数字每跳动1秒,就会有300多人上不了车。
即使在平峰运营时,王凯华也没法放松下来。
“虽然列车现在的安全性已经很高了,但是一想到我后面还拉了1000多人,我就紧张。”王凯华皱了皱眉头说。
时间久了,王凯华甚至会出现精神恍惚。有时从一个站出发后,他会怀疑自己刚刚是不是忘记打开车门。
“干这个之后,我都有了强迫症,家里人再也不说我丢三落四了。”王凯华说。
最尴尬的是行车时忽然想上厕所,遇到这种情况,司机还要向行车调度中心请示。得到同意后,司机要从停站上节省出时间。或者是起身、下车、开门的动作快一些,或者看站台上乘客少时,早点关门。
“有时厕所要分几次才能上完。”王凯华露出尴尬的笑容,“节省出的时间有限,不能耽误发车。”
如果轮到晚班,一天运营结束后王凯华要回到车辆段宿舍睡觉,第二天一早再跑一圈后晚班才算结束。早上发车前一个小时,会有专人喊他起床。上车前,王凯华会拿着手电围着120米长的列车转上两圈,做例行检查。随后上车,接触轨供电,列车缓慢出库,进入正线。
有时早晨下班时,王凯华会刚好遇上早高峰。他到轮乘中心换下制服,然后扎进站台上的人群,和他们一起挤进车厢。这个时候,没人知道他的身份,他只是一个需要回家的普通人。
王凯华记得自己第一次驾驶正式运营的列车,快要到达国贸站时,为了对准站台停车位置,他提前减速制动。列车缓缓前进,隧道前方开始出现光明,接着他看到了站台上大批候车的人群。在此之前,他一直把自己看作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那是他第一次有种被迎接、被期待的感觉。
西二旗
下午5点15分,在城市另一端的西二旗地铁站,站务员党卓振正在进站口外布置限流的栅栏。晚高峰即将到来,天色逐渐变暗,空旷的高架车站就像个风洞,几个乘客走上站台,裹紧棉衣,把头缩进衣领里。
晚上6点半,西二旗站的客流量达到峰值,站外的长队沿着限流通道缓慢移动,站内已经被黑压压的人群塞满。人们呼出的热气向上蒸腾,有人敞开了棉衣,相比下午,站厅里的温度上升了6℃。
党卓振说,西二旗地铁站是“每天都在发生奇迹”的地方。
在这里,平均每月有20只鞋、70多个背包玩偶挂件掉落在站台下的道床上。车站特意准备了拖鞋,方便那些挤掉鞋子的人回家。站务员在清理轨道时,捡到的最贵重物品,是一个装有5本房产证的公文包,失主“感谢到不行”。
西二旗站是北京最拥挤的地铁站之一,每天有30万人次在这里乘车,比春运时北京西站每天的客流量都要大。
一个新来的站务员没经历过西二旗的“盛况”,在早高峰维持秩序时,被汹涌的人流挤上车,直到知春路站才挤下车返程。
这里是13号线和昌平线的换乘站。在昌平线上的沙河站,站务员每天早上5点刚打开车站门,外面等候的人群就已经排起了长队。早高峰时,沙河站的队伍能排2公里长,很多人“推开家门就开始排队”。
西二旗站每天的人流就像潮汐。早上涨潮时,满载率超过140%的列车从昌平线开来,乘客在这里换乘、下车,晚上退潮时,人们再从这里出城,回到住处。
早晚高峰时,车站广播员要在4个小时内重复1800多次“列车到站,先下后上,请在车门两侧候车”,每次广播到最后,他们都会“眼花、几乎要晕倒”。
如果一个人想要在早高峰的西二旗成功挤上地铁,那么就算他已经通过安检,平均也需要再花费16分钟。司机要保证在昌平线上的每个站都早点,到西二旗时才能留出足够冗余,“因为西二旗站必定晚点”。
人最多的时候,在这里等候上车的队伍能排到20多米长。车门一开,原本静止的队伍马上开始小碎步移动,人们甚至能感到站台振动。有的人上了车,包落在了外面,有的包被挤上了车,人却卡在了车外。
西二旗站区副站区长李思野见过千奇百怪的上车方式,有人双手抓住地铁扶杆,双脚悬空,身体与车顶呈接近20度的夹角搭在人群之上。
一个退休后在西二旗服务了8年的文明引导员,总结出在西二旗成功上车的“秘笈”:“小伙子打头阵”“侧身突围”。
高峰时车厢里的乘客经常挤到顶住车门,造成车门无法机械锁闭,站务员要手动把两扇车门强行拉上。这要求站务员必须有足够强的臂力,以至于现在,西二旗站只有男性站务员才有“资格”站在早晚高峰的站台上。
因为处在互联网产业圈的圆心,每天从西二旗站下车的人和上车的人一样多。一位老太太曾经这样形容乘客在西二旗下车的场面:“高峰时车门一打开,地铁就像‘哗’地吐了一样。”
即便如此,哪怕只是晚了一秒钟,下车的乘客也会被拼命往里挤的人潮硬生生带回车厢。西二旗站的一位值班站长曹宇经常会在车门关闭前,看到一只忽然从人群中伸出的胳膊。几乎不能犹豫,站务员就要迅速抓住,把这只胳膊的主人拽出车厢。
大部分时候,西二旗站的乘客都能保持平静的情绪,但仍无法避免偶尔发生的冲突。曹宇发现,乘客“干架”的概率,夏天比冬天要高,早高峰要高过晚高峰。
“夏天比冬天火气大,早高峰急着上班,晚高峰没那么着急回家。”曹宇分析。
每天面对如此复杂的早晚高峰,维持整个车站秩序的只有27名员工。综控员要时刻盯着电脑屏幕,上面不停移动的红条,代表列车的运行状态。站务员则在售检票、接送列车间轮流换岗。
曹宇刚调到西二旗当值班站长时,压力太大整晚睡不着觉,最后被医生诊断为精神衰弱,“喝了半年中药”。
因为是高架线路,车站里是典型的“夏热冬凉”。夏天时,“站务员的衣服没有干过”。到了冬天,穿堂风从“两头透气”的车站毫无障碍地通过。去年最冷的一天,车站二层站台上的温度达到-26℃。
“最冷的时候,我们车站的站务员分不出男女。”李思野笑笑说,“都把自己裹得只剩眼睛,衣服里面挂的全是暖宝宝。”
和地铁司机一样,地铁站务的晚班也要负责当天的晚高峰,和第二天的早高峰。一天的运营结束后,清理完站台轨道的员工回到地铁站负一层的宿舍。时间往往是深夜1点,休息时间才会到来。
3个半小时后,新一天的工作开始。第一列开往西直门的列车45分钟后就要到站,站务员要在这段时间内完成所有的准备工作。
5点整,党卓振打开站门,外面已经有背着编织袋的老乡正在等候。他们要赶火车,是每天西二旗首班车上最常见到的乘客。
党卓振来到车站旁的便利店,叫醒趴在桌子上睡觉的店员,买了一瓶牛奶、两个三明治。店员告诉记者,自己每天迎接的第一个顾客,永远都是过来买早餐地铁员工。
终点站
李思野喜欢站在车站的二层连廊上向下观察,这里总会发生很多意想不到的故事。
西二旗站是个属于年轻人的车站,这里被各种软件园、科技园和创意园包围,有大量自嘲为“码农”的程序员,也有手里握着几个项目的创业者。
李思野发现,每到节日就会有很多捧着鲜花或者礼物在站台上等候的小伙子。每年情人节,晚上结束运营后,车站里到处都是散落的花瓣,也有成束的鲜花塞在垃圾桶里。万圣节时,李思野曾见过一群“兵马俑”排着队走上地铁。
每逢毕业季,车站里就会多出很多西装革履、背着双肩包的年轻人,出站口也会聚集一群散发租房广告的中介。
西二旗地铁站是一个喜悦和悲伤汇集的地方。有人刚刚挂上一通电话,就在车站里忍不住笑出声。也有人垂头丧气,领带松开,木然地站在站台上。
这里也是个汗水和泪水混杂的地方。夏季早高峰时,车门一开,总会有三四个小姑娘“刷刷”晕倒。苏醒后,她们几乎都会告诉工作人员,自己因为急着上班没有顾上吃早餐。因此,除了拖鞋,车站也常备了糖果应对突发情况。
这里有人失恋,有人失意。党卓振曾在晚上结束运营后,碰到蹲在站台上“哭到崩溃”的女孩。也见过瘫坐在地上,不顾形象的中年男人。
与西二旗站不同,在7号线终点站焦化厂站,每天最后几班地铁在这里停靠后,就要继续向前开进车辆段。站务员要到车厢“清车”,他们经常遇到抱着背包在车上睡着,不知坐过多少站的乘客。每逢周末、节假日,车站里都会有醉酒的乘客,讲不清自己的家在哪里。
“这是终点站,该回家了。”每次试图叫醒这些人时,站务员都会这么说。
还有一些刚来北京的外地老乡,明明要去西客站,结果两个小时后,坐了一圈又重新回到了焦化厂的站台上。
地铁站就是这样的一个集合,都市里的现代人在这里集中亮相。它就像城市的一个平行世界,映射出人世百态,展示出人们真实的样子。
不断延伸的地铁线路也见证了这座城市的生长。7号线焦化厂站刚开通时,只有一条土路通向车站,晚上来上班的站务员有时甚至会迷路。
8年前,西二旗站刚运营时,每天只有6万人次的客流量。李思野几乎看着周围的楼房高度和车站的客流数字一起上升。
这么多年来,有人每天都会出现在地铁站里,有人会在某一天突然消失。西二旗的地铁每天还是会准时停靠在站台,就像这座城市,从没有中断过它原本的节奏。
巡道工
司机和站务员都休息后,地铁线路工人就要开始工作了。每天零点后,北京的地铁隧道里都会有200多个工种、超过1000名工人在同时忙碌。
这里不是摩天大楼、熙熙攘攘的北京,这里是地下30米,没有半点声响的北京。隧道里的空气混合着灰尘和机油的味道,列车闸瓦和钢轨磨损的金属碎屑覆盖在水泥地面上,手电照上去,会发出星星点点的光泽。
26岁的姜胜负责10号线金台夕照站到分钟寺站的巡道工作,他头顶上方是北京最繁华的区域,央视新大楼、国贸商城、银泰中心就处在必经之路上。每晚地面上的酒吧把音量开到最大,KTV里的派对欢唱正酣时,姜胜也在地下开始了他的工作。
他工作的地方,和最偏僻的隧道没有太多差别。这里只有钢轨、电缆和水泥,因为修建年代较早,就连灯光都要黯淡几分。
4年来,姜胜已经在这条线路上走了630多次,连方向都没变过,但他从来没有走进过头顶上的任何一栋建筑,也没见过那些商场和购物中心里面的样子。
“没什么事去那干啥?”姜胜的生活几乎只有工作和睡觉,隧道外的世界似乎与他没有太多联系。
每天上班,他下午6点半就要从密云区的家中出发,3个小时后到达金台夕照站。他的休息室在站台尽头的一间小房子里,没有窗户。
房间里除了一些轨道抢修设备,一个柜子,两张高低床,再没有别的物件。最近房间的灯坏了,他打开手电当做光源,和工友一起坐在床上翻手机,等待最后一班地铁从门外驶过。
他负责的这段线路长7.8公里,一年下来要在隧道里走1400公里,检查超过12万个轨道零件。他的工具包里装着各种型号的锤子、扳手、改刀,有12公斤重。动身时,书包发出轻微的金属碰撞声。
损耗最快的是袜子,姜胜每月最少要穿坏5双棉袜。他自称“脚王”,“干这份工作前,全家我走路最慢,现在走路,家人要小跑才能追上。”
姜胜说之前最怕陪女朋友逛街,现在可以逛到女朋友走不动。他的微信运动排名里,几名巡道工工友长期霸榜。
“脚王”最难忍受的,是孤独和压抑。每天在空无一人的隧道里走上接近3个小时,周围空气和光线一样死寂。大部分时候,他都低着头把眼光集中在手电照射的铁轨上。但总是在某个瞬间,他会被深深的孤独感笼罩,“超想找个人说说话”。
已经当了17年的巡道工李师傅也有同样的感受。隧道因挖掘方式不同分为方形和圆形,相比之下,他更喜欢方形的隧道。
“圆形隧道就像一根管子,看不到出口。”李师傅感叹。只不过,大部分时候他都要行走在圆形的隧道里,就像一条困在水管里的鱼,只有一个方向。
他说巡道工过的是“美国时间”,每天都黑白颠倒。时间久了,不管自己在不在家,妻子都会在每天凌晨3点半左右醒来,这是他工作日每天到家的时间。
李师傅每天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洗脸,在隧道里两个多小时,“洗脸水都是黑的”。他发现不知什么时候,自己的“起床气”变得很大,每天睡醒后,就会无缘无故生气。
他负责的线路上,有一段1.6公里的弯道,路基在这里设置了一定的倾斜坡度。背着10多公斤的工具包,身体重心转移到右侧,日复一日朝着同一个方向在这段路上走过1500多次后,李师傅感觉“右腿比左腿短了一截”,平时走路也会觉得右腿抬腿困难。
巡道时,李师傅会用锤子敲击铁轨。通过撞击发出的不同声音,反馈出不同的力度,他就能判断铁轨内部是否结实,或者断裂。
隧道里没有太多“新鲜”的东西。冬天时,李师傅在洞子里见过一些猫狗的尸体。到了夏天,隧道里会有蝙蝠,他经常一锤子下去,一群蝙蝠呼啦啦地从头上飞了过去。
大部分时候,巡道工作都很难有收获。但每次微小的发现,都是关系到列车运行安全的大事。
李师傅曾发现过两根钢轨连接处,一处超过两厘米的缝隙。如果不及时处理,列车车轮不断碾轧造成钢轨错位,严重时甚至可能发生脱轨事故。
每天凌晨3点左右,姜胜和李师傅会分别从各自的隧道出来,走上站台。在综控室做完登记,确保没有工具落在隧道里后,他们一天的工作才正式结束。
他们是一天中最早打开地铁站门的人,外面的街道上空荡荡的,路边总有黑车亮着双闪。这时的温度降到一天中最低,但却是他们一天中最开心的时刻——冰凉的空气灌进鼻孔,终于重返地面了。
李师傅要坐夜班车27路公交车回家,每次车里都会坐满了代驾司机,有人聊着晚上发生的故事,有人发出沉重的鼾声。车窗外,路边的早餐店已经开门,穿着棉袄的夫妻正在忙碌,水蒸气在灯光下不断升腾。
这些场面让他感到安宁。两个小时后,第一拨儿乘客即将到达站台,沿着他刚刚检查过的轨道,开始一天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