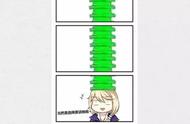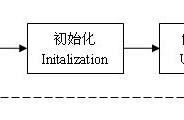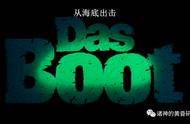《敲诈》(1929)
十年之后,两位导演的生命中都出现了影响他们后半辈子的事件:那时,希区柯克正在与大卫·O. 塞尔兹尼克(David O. Selznick)就他前往好莱坞的合同讨价还价,而鲍威尔则结识了亚历山大·柯达(Alexander Korda),正是后者把他介绍给了埃默里克·普雷斯伯格(Emeric Pressburger),他成为鲍威尔的御用编剧。
两人同样对电影情有独钟,都反对现实主义的美学,都喜欢以客串出演的方式来标明这是他们本人的作品,从某种程度上说,鲍威尔就是没有去成好莱坞的希区柯克;他所提出的「合成电影」(composed film)概念也和希区柯克的「纯粹电影」(pure cinema)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偷窥狂》和《精神病患者》有很多类似之处。它们都拍摄于1959年晚些时间,它们的成本都很低,它们讲述的都是貌似可爱的年轻人,但童年的经历造成了他们的情感残疾,并让他们成为连环*手。
更有甚者,它们都直接展现了对女性的暴力和扭曲的性爱,这都对审查制度和评论家们提出了相似的挑战。

《偷窥狂》(1960)
但是,《偷窥狂》和《眩晕》之间的相似性虽然没有前者同《精神病患者》看上去那么明显,却更为强烈。
当希区柯克想要缓和评论界对《精神病患者》的恶评如潮时,他声称,无论影片描写的人物和事件有多邪恶,这部作品对他而言都只是一个开玩笑的娱乐片;鲍威尔从来没这么说过他的《偷窥狂》,而希区柯克也从来没有否认过《眩晕》的严肃性。

它们都是极度浪漫主义的作品,都以爱情与死亡的纠缠爆发为剧终,这让那个活下来的人(安娜·马西[Anna Massey]、詹姆斯·斯图尔特)以及和他们站在一起的观众身心俱焚、无所依靠。随着岁月流逝,评论界对这两部电影的评价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虽然相同的事情也发生在《精神病患者》上,但其戏剧性仍然不及《眩晕》和《偷窥狂》;想当年,它们都是被人嘲笑或指责的失败之作,但现在,它们无论是在学术界的电影研究中,还是在批评性的文字中,都占据了至关重要的位置。它们拍摄于一个电影工业和电影文化都在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它们走在时代的前列,而属于它们的时代也终于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