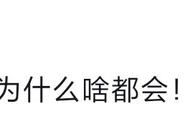历代的士人君子之所以醉心竹林,流连忘返,并非仅仅为了逃避现实社会,而是为了寻找一种精神寄托。人具有两重性,一是社会的人,肩负着社会和家庭的责任;一是作为个别的人、具体的人,他要确认自我价值,体验人的自由创本质,这种精神需求不是社会单方面能够给予的。克服这种社会与个人矛盾,到大自然中去纵情山水,是弥补心理缺陷的一种方法,可获得暂时的心理平衡。而绿竹猗猗静谧幽雅的环境,成为理想的去处。唐代诗人王维历经“安史之乱”,饱尝尘嚣烦恼之苦后,抛弃功名利禄之念,隐居蓝田乡下建竹里馆,潜心修行,彻悟佛法,静习禅定,使心境归于淡泊自然,“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诗人此时是何等的自由、愉悦、超脱!比王维稍晚的大诗人白居易,也是仕途几经挫折,晚年退居洛阳,在“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的家园中,诗人在读佛书习禅定之余,“日晚爱行深竹里,月明多在小桥头。”处于修竹篁韵怀抱中的诗人,心宁神静,体验到较多的自我价值,生命之光得到升华。他还在《养竹记》中将竹比作“贤人君子”,高度赞美竹子的“本固”、“性直”、“心空”、“节贞”等品格和情操。

枝叶柔柔,凤尾森森,龙吟细细,清秀俊逸的修竹之美,不知倾倒了多少丹青大师,为之挥毫泼墨。唐宋以来,以竹为题材的画竹名家辈出,幅幅竹画各以神姿仙态光照人寰。唐代画竹名家萧锐将所画十五竿竹赠与白居易后,诗人读竹感其意,作《画竹歌》:“植物之中最难写,古今虽画无似者;萧郎笔下独逼真,丹青以来第一人。人画竹身肥臃肿,萧画茎瘦节节疏;不根而生随意生,不笋而成由笔成。”爱竹成癖的苏东坡向画竹大家文与可学画墨竹,他对文与可的“胸有成竹”的绘画理论推崇倍至。诗云:“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庄周世无有,谁知此凝神。”在中国美学中,“淡”是一个极高境界,“作诗无古今,惟造平淡难。”集古今画竹之大成,达到如此高境界者,首推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他对画竹技法和理论的发展、完善,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竹林这一通身流溢着恬淡虚无幽幽灵光的伊甸圣土,孕育出竹子文明给人以感染和力量,使人去品味人生顿悟人生。爱竹咏竹画竹,实是爱人咏人画人。苏东坡的“萧然风雪意,可折不可辱”;郑板桥的“乌纱掷去不为官,囊橐萧萧两袖寒;写取一枝清秀竹,秋风江上作鱼竿。”以诗言志,借竹的形象抒发自已不媚权贵,格守淡泊正直的人格和情操。竹,不正是高风亮节的象征吗!

“未出土时便有节,及凌云处尚虚心。”这是中华民族优秀品格和情操的写照,也是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深深浸透竹的印痕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