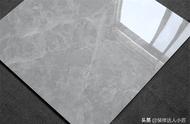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戴海斌
一
周作人(1885-1967)生前检讨个性,自认为“浙东人的气质终于没有脱去”,而颇重视地域民性默化潜移之用,“我们一族住在绍兴只有十四世……这四百年间越中风土的影响大约很深,成就了我的不可拔除的浙东性,这就是世人所通称的‘师爷气’。……他那法家的苛刻的态度,并不限于职业,却弥漫于乡间,仿佛成为一种潮流,清朝的章实斋、李越缦即是这派的代表,他们都有一种喜骂人的脾气”(《雨天的书》自序二)。此处举作“浙东性”代表的章、李二位未必认可自己为“法家”,不过一则“眼高一世,目无余子”,一则“性狷介,又口多雌黄”,他们持论苛刻、惯于骂人的习气,确也合乎“满口柴胡,殊少敦厚温和之气”。

周作人(1885-1967)
李慈铭(1830-1894)与章学诚都是绍兴会稽人,同府同县,他很早读过乡先生著作的抄本,却无多少佩服。同治十三年(1874),谭献(1832-1901)主持浙江书局,补刻印行《章氏遗书》,也赠予李氏一部。《越缦堂日记》中有关的“实斋识有余而学不足”讥议,多为人知(详拙文《读〈张舜徽壮议轩日记〉札记之二|章学诚何以“弘识孤怀救末流之弊”?》),同一日记尚有另一评论:
大抵浙儒之学,江以东识力高而好自用,往往别立门庭,其失也妄。江以西涂辙正而喜因人,往往掇拾细琐,其失也陋。(并参《越缦堂读*》“实斋杂著”条)
章学诚于乾嘉朴学大盛之日,未甘比附风会,发明“浙东学术”一说,为其特识。李慈铭此处总结“浙儒之学”取径,归章氏入“浙东”,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正将前者讥评他人“村陋无闻,傲狠自是”(《文史通义》内篇三,《朱陆》)这八个字掷了回去,旨在批驳其人之“妄”。虽然同一地所产之人,他显然并不以乡前辈为然,也不欲以地域自限。后来钱锺书为《复堂日记》作序,比论李慈铭和谭献评骘实斋的相异之处,不仅直言李氏“矜心好诋,妄人俗学,横被先贤”,也注意到“李承浙西乡先生之绪,嬗崇郑许”,“以章氏乡后生,而好言证史之学,鄙夷实斋,谓同宋明腐儒师心自用”。此处“先贤”,指同出“浙东”的章学诚,“浙西乡先生”,即谭献。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
张舜徽多次读过《越缦堂日记》。二十岁左右,全书五十一册(起咸丰癸亥[1846],讫光绪戊子[1888])便已“粗涉一过”;1944年3月26日-4月1日,居宁乡陶家湾北平民国学院,阅毕《补编》十三册(起咸丰四年甲寅[1854],讫同治二年癸亥[1863]);1947年1月3-6日重读之,“因感于近人推崇李氏无所不至,恐未足以副其实,故思于此五十一册之书再寻温之”。他说“李氏幼习诗词,性喜讥弹,观日记中评骘人物,语多轻率”(《张舜徽壮议轩日记》,440页)。李慈铭诋章学诚“读书卤莽”,张舜徽曲为辩护,而谓“不悟学诚精处,全在识解夐绝时流”,那么,对于同出浙产的“荀学斋主人”作何观感呢?
二
李慈铭本人撰有《国朝儒林经籍小志》一类有关清学成绩的总结叙述,站在“汉学”立场,将乾隆朝开修四库全书作为一个振兴的转折点,日记中极力表彰清儒,“诸君子抱残守阙,龂龂缣素,不为利疚,不为势绌,是真先圣之功臣,晚世之志士”(同治二年正月廿四日记)。张舜徽视此为“不情之言”,并且反唇相稽,直谓乾隆开四库馆,戴震以校书入翰林,史林荣之,乃群趋于贪繁务博,以辑佚考订为事,所谓“汉学”实始于斯,此为“干禄弋名”;乾嘉学术极盛时,隘陋自蔽,流毒至今,汉宋门户终不能除,古今文之争终不能息,此为“操戈树帜”。
李慈铭承乾嘉汉学之余绪,博治经、史。咸丰十一年(1861)告友人书有曰:“近惟日治经史,遍考近儒撰述。盖考证之学,国朝为最,国朝尤以乾嘉之间为最盛。能读其书者,庶于经史无误文别字,缪辞枝说。士生其后,可谓千载一时之幸。”(见咸丰十一年六月十九日记,其“遍考近儒撰述”,或与次年着手撰写、至同治三、四年间成书的《国朝儒林经籍小志》有关。)张舜徽读书至此,有感于乾嘉风气束缚士林,近世流变,每下愈况,忿然而言:
夫为学奉乾嘉大儒为师法,可也,谨守其书不敢踰尺寸,不可也。使徒奉新疏数部,览不及数卷,辄欲谈经说字,有如无源之水,得盛雨为潢潦,其不可恃甚明。吾平生所识学人不为少,每察其架上图书,无不庋置清人经疏札记,号称博雅。尝谓清儒之病在于佞汉,近人之病又在于佞清。今观莼客所记,则知士林斯病自道咸以来然矣。百年痼疾,其谁起之!
此段议论可与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论时代思潮”一节参观,虽然两人对于“汉学”的评价并非一致,但思潮流转例分数期,不外生、住、异、灭,学风变迁,多循斯轨。张舜徽论清儒学术,“别为三期”,1942年10月5日记:
自开国迄于乾隆之初,大儒四起,同以致用为归,气象博大,此一期也。自四库馆开,学者竞以考订校雠为事,学尚专精,门庭渐褊,此又一期。自道光迄于末造,涂规分离,互相倚摭,破碎已甚,效用益微,此晚期也。
以其眼光衡之,官修《四库全书》实为清代学术一大转捩点。此前诸儒治学“气象博大”,亦未标榜“汉学”之名,与后来专门名家者异趣。他引章学诚《丙辰札记》,指出自四库馆开,学问之途一变,“乃出一种贪多务博而胸无伦次者,于一切撰述,不求宗旨,而务为无理之繁富”,“明知其载非伦类,辄以有益后人考订为辞,真孽海也”。汉学流弊所至,固非始事者能及料,然而李慈铭以近代之人“确守乾嘉诸老家法” (《清儒学案》卷一八五《越缦学案》),罹“佞清”之病而不知,实在大不合时宜。

徐世昌主纂《清儒学案》
李慈铭论国朝“说经之学”,以“桐城姚郎中鼐”“著书满家而无当古义”,“大兴翁学士方纲”“虽名古学,出入无主”,皆在“所屏”之列(《国朝儒林经籍小志序》)。《越缦堂日记》除攻击章学诚而外,词连姚鼐、翁方纲,诋为“愚而无用”“往往谬妄”(见《越缦堂读*》“惜抱轩文集”“惜抱轩尺牍”“复初斋文集”诸条)。张舜徽盛推姚、翁二氏并章学诚为“乾嘉三通儒”,前说正中其大忌。1944年3月30日记:
(李慈铭)日记中诋斥姚姬传、翁覃溪过甚,至目为不学妄人,而不知两家救弊之言深切明要,在乾隆学术极盛时实足为中流之砥柱,不随风气转移,且能持正论以转移风气,非豪杰之士不逮此。惜莼客未能窥两家深处,又从而鄙夷之,宜其学不能大也。
《清人笔记条辨》“越缦堂日记”条亦谓“李氏于乾嘉诸儒,诋斥翁覃溪、姚姬传、章实斋为最厉”,“此皆评贬太过,不足以服三家也”,进而辩护:“乾嘉士子自髫龄迄于皓首,大率竭精力、困智虑,疲老于补苴襞绩之役,其积痼可知矣。此三家之言,实消积之良药。其补偏救弊之盛心,何可没也?”
李慈铭的人物月旦评,“论涉并世儒林,轻蔑湘贤至力”,“目王湘绮(闿运)为江湖唇吻之士,又谓何子贞(绍基)久享时名,实无真诣,较王子寿为劣,及读郭筠仙(嵩焘)《礼记质疑》,则总论之曰:“盖湖南人总不知学问也。”此句重话,最触到湘人痛处。为回护乡曲,张舜徽不吝直斥“此等轻妄之言,适足见其矜倨自高之气”,复加曲释:“盖李氏一生好轻诋人,吹毛所瘢,睥睨当世,加以年逾五十,而犹困于场屋(李氏于光绪六年始成进士,时年已五十二)。以愤懑发为言谈,无往而非讥斥矣。”(《清人笔记条辨》,342页)此说迹近人身攻击,殊无学理可言,未免已有“诛心”之嫌。最后,仍须说明湖南人“真学问”究竟何在——
考其平生持论,大抵依附乾嘉诸儒,不敢越尺寸,而不知湖湘先正之学,本与江浙异趣,大率以义理植其体,以经济明其用,使以李氏厕诸其间,只合为吟诗品古伎俩耳。孰轻孰重,不待智者而自知。乃自困于寻行数墨之役,而不见天地之大,遂谓湖南人不知学问,其偏狭亦已甚矣。
此处发明“湖湘先正之学”,确见其大,不过,品衡李慈铭的学问仅有“吟诗品古伎俩”,未必合乎事实,更有意思的是,张舜徽端视李氏为乾嘉汉学余绪,似完全忽视了(或也可说接纳了)其人尚有表彰“宋儒”、推崇“义理”的另一面。这就仿佛李慈铭责难章学诚,全在“考证粗疏”“读书卤莽”处着眼,而对后者《易教》《经解》《原道》《原学》诸篇以及“官师治教合一”之说,乃至批判汪中、袁枚的那一些“卫道”观点,不置一词。
我们很容易想到鲁迅对《越缦堂日记》的批评,其第一条便是“钞上谕”,这是“提防有一天要蒙御览”,“觉得从中看不见李慈铭的心,却时时看到一些做作,仿佛受了欺骗” (《三闲集·怎么写(夜记之一)》,1927年)。确实,读李慈铭的东西,不免嗅到一股“道学”气味。民初学人为作“学案”,已指出“博极群书,勤于考订,兼尊宋学,谓可以治心” (《清儒学案》卷一八五《越缦学案》)。他的平常言论多肯定宋儒卫道治心的“发明义理之功”,屡谓“汉儒守经之功大,宋儒守道之功大”,“欲学汉儒之治经,当先学宋儒之治心,一生不敢菲薄宋儒,良以此也”(参看卢敦基:《汉学,宋学,抑或汉宋兼采?——试论李慈铭所属的学术营垒》)惟就“学术”一层而言,谓“兼遵宋学”则可,谓“汉宋兼采”稍过,李慈铭于两者去取之间终有分际,他说“晚世说经,总以有家法者为贵……后世有述者,或汉或宋,皆所不祧,而与其为宋,不若为汉”(《越缦堂读*》“易守”条)。
三
张舜徽看待李慈铭,一面窄化其学问范围,铆定在“汉学”门墙内,一面拷问其学问程度,疑其“佞清”近似叶公好龙,无疑有如釜底抽薪。日记一则曰:
莼客持论虽张汉学,亦但追慕时尚,而非真有得于己。究其受病之由,乃以渠所致力者,终身寄在乾嘉诸儒篱下讨生活,而不能岸然自拔耳。
再则曰:
李莼客于经学、小学所造甚浅,而极力表扬汉学。
按李慈铭早年乡居,“喜为歌诗、骈文”,三十五岁时自撰卧室春联:“余事只修文苑传,闲身且置户曹郎。”咸丰九年(1859),入都门后,“反而为考订章句之学”,及至晚年,经史研究渐有规模,世人亦以考据家目之,光绪十五年(1889)作《六十一岁小像自赞》,有曰:“是儒林邪?文苑邪?听后世之我同。独行邪?隐佚邪?止足邪?是三者吾能信之于我躬。”文中“儒林邪?文苑邪?”之反问,实则自问自答,因为他自负“所学于史为稍通,所得意莫如诗”(《白华绛跗阁诗初集自序》,《越缦堂文集》卷二),足以儒林、文苑两兼。
对于上述认知,作为后世读者的张舜徽并不谓然。1944年3月29日记:“李莼客自道所学,谓生平所不忍自弃者有二:一则幼喜观史,一则性不喜说部。(咸丰六年四月十五日记)乌呼!此自文之辞也。”李欲兼长并美,张则抑此扬彼:
余观其平日涉览,全在宋元明人说部书,经史俱非所长,于经学尤荒芜。至于究心乙部,亦特常窥钱(大昕)、王(鸣盛)、赵(翼)三家札记,以资口给,而未见有读史日程也。彼虽自云欲取说部以考订正史,撰为《史剩》,又尝欲续邵南江(晋涵)之志,从事南宋九朝以成一书,皆徒托空言,非彼所能任也。
其实,李慈铭本人也承认,早年问学,耽于辞章,尚未得窥经史堂奥。同治二年(1863)致友人书有云:
弟之于学,少无所师。阙帻早孤,又生稍晚,吴越间经师已皆奄化,时时拥比设帐者,盖多不读注疏,梼昧之质,遂无自启。十五六后,喜为歌诗、骈文,昼夜殚精,以为至业。既渐渐得名,益复爱好,迨得读《学海堂经解》,始知经义中有宏深美奥、探索不穷如此者,遂稍稍读甲部书。自汉及明,粗得厓略,而年亦既二十四五矣。(《复桂浩亭书》,《越缦堂文集》卷四)
张舜徽指出“此虽追述年少读书时事,然其一生趋向,不能越斯范围也。故自少至老,仍是文苑中人”(《张舜徽壮议轩日记》,739页)。汪辟疆(1887-1967)也认为其学问所长在彼而不在此,“越缦喜谈经学,实非所长,一生学术,乃在乙部,披阅诸史,丹黄满帙,其博闻强记为时流所叹服,诗文尤负重名”(《近代诗人小传稿·李慈铭》)。当代学者颇重视李氏之“诗学”,复加以系统整理,而认定:“李越缦一生学术荟萃于《日记》,其学贯通四部,大抵以能守传统学术之正宗为其根本性质。四部之中,略以史部为较长,而其心得之有系统者,则断然当在集部之学。”(《越缦堂日记说诗全编·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