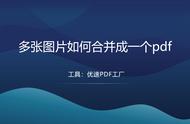亚历杭德罗对此作出了解释:“伊丹豪分享的思考还得结合历史上随着摄影产生的一系列议题考虑。
摄影曾被认为是现实的复制品,人们对摄影作者身份在概念上产生质疑,因为传统观念中的作者是图像的创造者,只有这样图像的版权才归他们所有。
实质上,伊丹豪所做的就是挑选世界上的一些碎片并将其展示给大家,这与摄影的做法一样。”
伊丹豪决定和选择的图像,是那些与他“所见”完全相同的景象,是那些就像是他本人所拍摄的图像一样的图像。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说,当复制品最接近人眼所见时,却离真实最远的原因。

他说过的一段话,也许可以回答“复制”所具有的意义问题。
“照片跟相机之间的关系其实不只是去复制眼前极为相似的物体,它同时也具有某种意义,或者是拥有某种唤醒故事的力量。我相信摄影的这个部分,也觉得其非常重要……
我并不是让摄影本身持有某种意义,而是原本单纯地对眼前物体做拷贝的东西,在观看的人眼中变得不仅仅是复制,而是有其特殊意义。
画面整体都在对焦框内,如果以欠缺中心的方式去拍摄,也许就会忽略认知的部分。
事物本身的轮廓如果越清晰反而看起来会越抽象。人们看着我拍摄的作品时或许能够抱持着某种抽象的感触吧。”

在伊丹豪看来,对公共图像的直接利用所具有的“复制性”是具有意义的。
然而这种意义是公众赋予的,这种赋予又是基于对这些图像抽象性的认识所产生。
这意味着,当我们不把这些图像视为地图的时候,才有可能真正理解伊丹豪的《塔兰泰拉舞》系列作品。

2015 年时,伊丹豪曾经在采访中说:“我不知道摄影是否有极限,因为我甚至还没有站在入口处啊。
对我来说,摄影还是有无限的可能性。我也想知道,摄影的极限会是什么?”
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系列作品,大概可以看作是他对摄影界限问题的思考和回答。
对话伊丹豪
请介绍一下你自己,什么时候开始从事摄影?
伊丹豪:我从来没有在学校系统学习过艺术。进入大学后不久我就退学了,因为不知道自己将来想做什么。
后来,我发现很喜欢时尚行业,比如时尚品牌的公关或者时尚杂志编辑,因此我开始在邦卡时装学院学习。
也是在那里,我遇到摄影,并有机会在课堂上进行拍摄,这让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似乎很擅长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