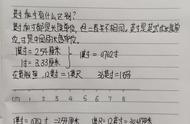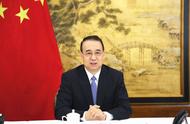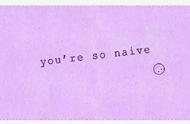陈世旭 郭红松绘

西安大雁塔雄伟壮丽,吸引众多游人前来一览胜景。 新华社记者 邵 瑞摄
很多次路过西安,很多印象模糊了,唯有大雁塔,始终清晰。
一
没有送行的人群,只有灞桥杨柳依依,山川庄严温柔。所有成就一个世俗文人传世名声的故事,都始于那一次的悄然离去。
身后是喧嚣暂歇的皇都,无尽的长路,无可预知的前途,只有星星在黑暗的天空格外明亮。一个孤独的旅人,为直探原典,冒越宪章,私往天竺,投身塞外的大荒,风节凛凛走向接踵来临的凶险和苦难。怀抱大乘菩萨“难行能行,难忍能忍”行愿,委命求法以惠利苍生。
月黑与风高,火焰与雪水,美酒与膏粱,香艳与温柔,与一个执着的行者无干。昼伏夜行,袈裟掠过长云的黯淡。那一抹衣袂的飘忽,不屈不挠,越五烽,渡流沙,渐行渐远,在时光里点染湮开,在传说与传说之间缓缓游走。不知道一重又一重深锁的重门后面,会不会有人相信莲花的纯净;不知道会不会有那一天,欣慰地发现,走过的千里万里,都是曾经走过的路;不知道在多少年后的某一个黄昏,手上的经卷会不会在安睡中落下。
驼铃叮当。茫茫戈壁拉长了数千年的光阴。朦胧中眺望,恍惚站在云端。历史的尘烟,湮没在飘渺的时空。岁月风蚀了没有植被的沙丘和没有生机的骨骼。瓦砾和残本,遗留在绿洲风口,在大漠烽烟里沉沉入梦。
但根深蒂固的信念,不能替代。
三年跋涉,五万里孤征,抵达天竺。又五年,遍游全印众国,遍学大小乘各种学说,究竟各派理论分歧,通晓经、律、论三藏。返回那烂陀寺时,被奉为佛教最高学府的主讲。曲女城佛学辩论,十八国王、三千大小乘学者、外道两千人,论主玄奘,立“真唯识量”。任人问难,无人能破。一时名震五印,万人景仰。大乘尊之为“大乘天”,小乘尊之为“解脱天”。英国史学家史密斯说:“无论怎样夸大玄奘的重要性都不为过。中世纪印度的历史漆黑一片,他是惟一的亮光。”
二
曾经水草丰美的世界,早已进入神话。只剩下,活着千年不死、死了千年不倒、倒了千年不烂的红柳。而万里黄沙,掩埋了多少不该掩埋的细节。
雁塔握云,俯视三千世界。站在高高的楼头,我瞩望在季节嬗变中的飞雁。塔上的铜铃,在微风吹拂中日夜摇响。慈悲凝固成亘古,净化了世俗的心灵。在西安这个清凉的早上,霞光灿烂,你微笑着向我走来。
那一年,缁衣笀鞋的圣者,携着巨量的梵筴和佛经,以及无上崇高的国际声誉,风尘仆仆,筚路蓝缕,踩着离去的脚印,回到出发的中土。
来去之间,相隔着一十八个春、夏、秋、冬。
十八年的盛衰荣枯中,故土在热切地等待远行儿郎的归来,等待一颗历经千劫百难不死的灵魂。
洛阳宫仪鸾殿。二月春风似剪刀。碧玉妆成的宫柳,万条垂下绿丝绦。
属于圣者的疆土,以一种神圣的方式,奉献给跨越万水千山的赤子。
因征战而驻跸洛阳的太宗立即诏见,与之并坐。
而对于玄奘,西天归来的终点不过是另一个起点。
圣者所以是圣者,在于他从不回顾,所有的悲欢都已成灰烬。即便为半生的坎坷,也不会流下一滴清泪。穿越岁月的苍茫,早晨与十八年前的早晨依然相似。
圣者注视的永远是前方的路途: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依旧横亘着难以逾越的千山万水;而从一个心灵抵达无数心灵,是一条永无尽头的道路。
唐长安城最宏伟壮丽的皇家寺院慈恩寺建成,迎请高僧玄奘担任上座法师。首任住持方丈,主持寺务,领管佛经译场,开始了更为宏伟壮丽的译经和创立佛教宗派工程。其间历时两年,主持督造大雁塔,供奉从天竺带回的佛舍利、贝叶经及金银佛像。
皇皇大唐,万邦来朝。
外国商贾、使团、参习佛教的留学僧,纷至沓来。
三
站在大明宫南望,长安的天际线顶端,就是慈恩寺大雁塔。现存最早、规模最大的唐代四方楼阁式砖塔,古印度佛寺的建筑形式随佛教融入华夏文化的典型物证。唐长安城保留至今的标志之一,这是当时世界佛教最高的学府,最高的学术领袖是唐玄奘。
去摩挲“二圣三绝”的碑文?去猜测贝叶真经的谜语?去礼拜释迦如来的足迹?去寻觅地宫珍宝的秘密?去想象“雁塔题名”和“曲江流饮”的春风得意?
所有这些,对于我都不重要。
我最愿意流连的,是嵌在南门券洞两侧玄奘负笈和玄奘译经的画图。
雁塔复制的是佛门常见的舍生故事,矗立的是圣者非凡的不弯曲的意志。
玉华宫恢弘的殿堂,木鱼与钟鼓穿透了阴冷与沉寂。烛光和青烟里,呈现出陌生而又熟悉的圣者轮廓:
一个谦卑无怨的工匠,孜孜矻矻,给世界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财富,也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身影。
两度断然拒绝帝诏,拒绝位高权重的仕途,唯愿“毕身行道”,“守戒缁门,阐扬遗法”。
信誓旦旦,源自山川大地一般的自信。
年近半百的玄奘埋首青灯黄卷,把余生的心血和智慧全部付与译经。寻常人消磨的无数日子,三藏法师种下了荫庇众生的参天大树:
经论75部,每卷计万言,总计1335卷,占整个唐代译经半数以上,是另三大翻译家译经的一倍多。尤以质量远超前人,是译经史杰出典范。《大般若经》,卷帙浩繁,梵本计二十万颂。600卷的巨著,玄奘不删一字。
《大唐西域记》,12卷。记述所亲历110个及得之传闻的28个城邦、地区、国家的疆域、气候、山川、风土、人情、语言、宗教、佛寺以及历史传说、神话故事,像一把火炬,照亮了“曾经一片漆黑”的印度历史的天空。一千三百年后,英国考古学者和印度学者手持英译《大唐西域记》,在古老的印度大地上按图索骥,陆续发掘出众多佛教圣地和数不清的古迹,甚至据此发掘出了现今印度的国家象征——阿育王柱的柱头。
开创大乘佛教法相宗。依楞伽、阿毗达摩、华严、解深密、菩萨藏等六经,及瑜伽,摄大乘,译成唯识论十卷,此宗乃立。予中国哲学史以深远影响。
凡此种种,给浩若烟海的世界文化史留下无可忽略的辉煌篇章,无可争议地歆享中外文化交流以及和平使者的世界之誉。
唐麟德元年(公元664年)。译出《咒五首》1卷。“玄奘自量气力不复办此,死期已至,势非赊远”,从此绝笔翻译,并对徒众预嘱后事。
正月初九,病势严重。
二月五日,夜半圆寂。
朝野数万人众送葬,将其灵骨归葬白鹿原。
这是玄奘东归第十九年。
或许这是世界的尽头,你一个人的星空,你一个人的巅峰。而我有幸感受这来自永恒时空凝聚的巨大的,渺小的,深邃的,闪亮的,沉郁的,清晰或迷茫的一切,仰望“千古一人”。
丈量生命价值的不是时间。回首处,莫道西风独自凉。听着咒语我看到你的方向,念着箴言我闻到你的焚香。你不曾远离,只不过在另一个轮回修行。在你盘腿坐过的地方,依旧有灵魂的吟唱,蓝天下的道路洁白而宁静。此刻,我以虔诚的膜拜,站在你的面前。心中漫过永久的柔情,融化是全部的语言。
古都缄默,雁塔肃然。渺渺香烟,弥漫来来往往的因缘。天地间传之久远的,是黄钟大吕的声音。
无论一人,一族,一国,千里万里的路程,始于坚韧不拔的跬步。而大雁塔,是历史留下的一个永远的精神路标。
(陈世旭,江西南昌人,当代作家,上世纪80年代至今,主要从事文学写作,出版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随笔集多种,其中,《小镇上的将军》《惊涛》《马车》《镇长之死》等曾获全国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