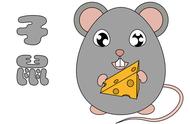犁米/文

八十年代以前,我老家那个地方比较穷,如果谁家闺女出嫁、孩子娶媳妇,一般选在春节后那几天里举办喜事。为啥呢?一是趁着农闲时节,热热闹闹的举办婚礼;二是天气冷,宴席上剩余的饭菜能多放段时间,不至于因天气炎热饭菜变馊造成浪费。
当时,农村里电视机还不普及,文化生活非常单调。当然,也有比较活跃的村子,组织村里的青年男女彩排一些简单的歌舞节目,进行新春文化娱乐活动。然而,大多数的村子却无人牵头干这件事。所以说,那些年,老百姓巴不得谁家孩子娶媳妇、办婚事、闹洞房、抢喜糖,随着娶媳妇的人家热闹那么几天。
印象中,本村一姓孙的大户人家,早年参加过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前身为山东人民抗日游击四支队),因其在故里私塾当过先生,国学知识非常渊博,文化基础非常深厚,后被四支队司令员洪涛指定为部队文化教员。解放后,担任了原莱芜县卫生局局长职务。七十年代中期,其离休后回到家乡居住。半年后,其三子与本村一位年龄相仿的姑娘定了亲,并约定来年正月初六结婚。春节过后的初六那天,整个小山村张灯结彩,沉浸在一片喜气洋洋中。
他们家族大、辈分高、有威望,自年初二开始,就有本家的、外姓的亲戚朋友帮忙发喜帖、砌锅灶、劈木柴、称盐打油、买菜割肉,一派人来人往、门庭若市的样子。
这只是婚事的前奏,最热闹的要数结婚的当晚,还未等赴宴客人散席,那不大的四合院里,就挤满了前来闹洞房的青年男女,虎视眈眈地把守者婚房的门口,将还未吃完饭的新媳妇堵在洞房里。那陪新媳妇赴宴的客人,一看院子里挤满了那么多闹洞房的人,也找各种理由三三两两的、知趣地离开了。新媳妇一看这架势,也想跟在她们的身后溜之大吉,无奈被两名眼疾手快的小叔子辈分的小伙子挡在了洞房里。其中,一个抱住新媳妇的腰,后进来几名年轻人抬起新媳妇的腿,在铺有大红被子的婚床上颠起了屁股蹲,直到新媳妇告饶,分别给这几位小叔子点了喜烟后,他们才停止了这种有点粗暴的婚闹。为了不再受到这群愣头青们的戏虐,新媳妇急中生智,对着闹洞房的小青年说道:“我给你们唱支歌吧?”
“好,只要大家听着好听就饶了你。”人群中发出了一片的欢笑声……
于是,新媳妇清了清嗓子,羞答答地唱了起来:
燕山高又高
清泉水长流
群雁高飞头雁领
*带咱向前走
咱们乡亲的主心骨
生产致富的好带头
和咱们心连心
汗水往一快儿流
汗水往一快儿流
啊……啊……
“大家说好听不好听啊?”
“不好听!”
“还要不要啊?”
“要,再来一个!”
人们不依不饶,起哄着、欢闹着……
“撒喜糖了、撒喜糖了!”
闹房的人群中不知谁喊了一声,新房里的人蜂拥而出。只见在婚房侧旁的正房门口处,新媳妇的二大伯醉醺醺的一手端着个葫芦瓢、一手掐着两盒“泉城”牌香烟,高声地喊道:
“今天是孙长平与张秀英结婚的大喜日子,特意撒高粱胎喜糖和‘泉城’牌香烟。”
“二大爷,你不识字吗?那是高粱饴。”
人群中不知谁揭了二大爷的短,让二大爷脸红脖子粗地反击道:
“新媳妇怀胎生子,不叫高粱胎叫什么?瞎掺和!抢糖喽……”
话到、糖到、烟到,人群轰地一下乱作一团,个子高的就像排球运动员拦网那样,双脚离地举起双手就将飞到眼前的喜糖接在了手中,那些个子矮、接不到空中喜糖的,于是就两手着地瞎子摸鱼般的在地上画起地图来。趁此机会,那遭受了百般刁难的新媳妇,在小姑子妹或者大姑子姐的掩护下,早已脚底下抹油溜之大吉了。
这闹洞房也是有讲究的,长辈不能闹晚辈媳妇、大伯哥不能闹弟弟媳妇,只有晚辈闹长辈媳妇,小叔子闹嫂嫂,如果违背了这个纲常伦理,过后在新媳妇面前抬不起头来,更让乡里乡亲们瞧不起的。也有辈分高的年青人浑水摸鱼,夹杂在闹房的人群中站在外围瞧热闹。但是,常常在其他人的数落与谴责声中,借着昏暗的灯光灰溜溜地离去。

那个时候,物质匮乏,有的人家一年都吃不上一块糖,有的在外做事或当工人挣工资的家庭,偶尔给嘴馋的孩子买上几块糖吃,但也不是那种软、绵、甜的高粱饴,而是硬且粘牙的那种水果糖。所以说,有时候抢喜糖要比闹洞房热闹多了。
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村里一刘姓人家是十里八乡都知晓的名门望族,其家人多在上海、南京、安徽、济南等地政府部门、国营大企业担任领导职务。八一年正月初四,是他家二儿子的结婚日。那天,在上海某企业任*的堂叔回老家参加侄子的婚礼,顺便买回了二斤上海产“大白兔”奶糖,准备犒劳参加婚礼的客人。为答谢乡里乡亲们对刘氏家族的支持和捧场,后来刘家族人决定将“大白兔”奶糖搀合着些水果糖,撒给前来闹洞房的人。
这消息一下像长了翅膀一样,迅速传遍了小山村。还未等太阳落山,刘家大院里就挤满了里三层外三层前来抢喜糖的人,那阵势简直比村里放电影还热闹。晚宴结束后,那些前来抢喜糖的人不去闹洞房,反而伸长脖颈、眼巴巴地望着新媳妇公婆住得正房屋子,焦急地等着里面的人出来撒喜糖。
“今天是刘雪增和李艾桂结婚的大喜日子,为了答谢老少爷们前来帮场,今晚给大伙撒‘大白兔’奶糖!”这时,刘家的一位后生,嘴里丝丝地吐着酒气,舌头上卷着带过滤嘴的喜烟,向院子里前来抢喜糖的人群吆喝道,“大家抢喜糖要注意安全,保证达到人均两块喜糖。”只见他一边手舞足蹈、比比划划的说着,一边用左手端着一个红色的圆形塑料盒,漫不经心走出屋门,站在了门前的石台阶上。那托盘样、红色的塑料盒上盖着一张大红纸,想必那红纸下面就是人们期待已久的“大白兔”奶糖了。
“听说吃一块奶糖,赶得上吃一斤猪肉的营养价值高了。”
“我奶奶今年七十多岁了,一辈子也没吃过奶糖,今晚说啥我也得抢一块奶糖,让奶奶尝尝‘大白兔’的味道。”
“别再磨叽了,俺牙缝里的馋虫快要爬出来了,赶紧撒吧!”
人群中,一时躁动不安起来,嗔怪声、嬉笑声、打闹声、催促声,此起彼落,愈演愈烈……
正当人们叽叽喳喳闹得不可开交之时,一阵噼噼啪啪的落糖声传入人们的耳中,那大白兔奶糖有的落在人们的头顶上、有的掉在人们的脖颈里、有的打在人们的脸面、胸脯上,更多的则是落在地面上。那抢糖的人,你不让我、我不让你、头碰头、面对面、腿缠着腿、腚拱着腚的在地上推太极、摸起糖来;抢着糖的紧紧地攥在手心里,使出吃奶的力气想从人圈里退出来;那没抢着糖的,则是长江后浪推前浪,退回来又围上去,叠罗汉般的你压我、我压你,挤压扭结成一个望而生畏的人疙瘩。
让人唏嘘不已的是,刘家院子里长着一颗碗口粗的枣树,树跟前堆着一滩未融化的春雪。那撒糖的后生,或许用力过猛,天女撒花般抛得满院子里都是喜糖,眼看着喜糖落到了雪堆上面,眼看着几十只抢糖的手就像逮麻雀一样,在雪堆里上下翻飞地抄了起来。眨眼间,抬筐大的一坨春雪,竟然被几十只手掌抓挠成了一滩雪水。幸运的从雪里捞到了三两块“大白兔”,运气不佳的,手心里只剩下一把春雪,更有那倒霉的,喜糖没抢着,过年时穿上的新棉袄,则被人当成了擦手布,新棉袄的后面抹画上了许多深浅不一的泥道道,成了典型的“抢糖不成蚀把米”。那抢着糖的,沾沾自喜地躲在灯光的背影处,小心翼翼地从口袋里,掏出“大白兔”奶糖剥起糖纸来。当剥到那层透明的食用纸时,怎么剥也剥不下来,有人提醒他,那薄薄的透明纸是粮食做的,放在嘴里也能吃。于是,饿狗般的一下就填进了嘴里,生怕到手的喜糖被人抢走了。也有那抢到喜糖舍不得吃,只是将喜糖放在鼻子下面闻闻奶糖的气味。然后,小心翼翼地将糖放进贴胸的口袋里,急急地向家中跑去,把抢到的喜糖让给弟弟、妹妹或者上了年纪的老人吃。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那时候闹洞房还算守规矩、讲文明的,尤其是喜糖味道特别的香甜,至今还回味无穷呢……
作者简介:犁米,企业家日报驻山东记者站副主任、《当代散文》编辑部主任。
壹点号当代散文
找记者、求报道、求帮助,各大应用市场下载“齐鲁壹点”APP或搜索微信小程序“壹点情报站”,全省600多位主流媒体记者在线等你来报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