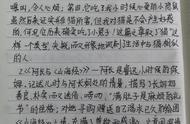从去年起,仿佛听得有人说我是仇猫的。那根据自然是在我的那一篇《兔和猫》:这是自画招供,当然无话可说,——但倒也毫不介意。一到今年,我可很有点担心了。我是常不免于弄弄笔题的,写了下来,印了出去,对于有些人似乎总是搔着痒处的时候少,碰着痛处的时候多。万一不谨,甚而至于得罪了名人或名教授,或者更甚而至于得罪了“负有指导青年责任的前辈”之流,可就危险已极。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大脚色是“不好惹”的。怎地“不好惹”呢?就是怕要浑身发热之后,做一封信登在报纸上,广告道:“看哪!狗不是仇猫的么?鲁迅先生却自己承认是仇猫的,而他还说要打‘落水狗’!”这“逻辑”的奥义,即在用我的话,来证明我倒是狗,于是而凡有言说,全都根本推翻,即使我说二二得四,三三见九,也没有一字不错。这些既然都错,则绅士口头的二二得七,三三见千等等,自然就不错了。
我于是就间或留心着查考它们成仇的“动机”。这也并非敢妄学现下的学者以动机来褒贬作品的那些时髦,不过想给自己预先洗刷洗刷。据我想,这在动物心理学家,是用不着费什么力气的,可惜我没有这学问。后来,在覃哈特博士(Dr.O.Dihnhardt)的《自然史底国民童话》里,总算发见那原因了。据说,是这么一回事:动物们因为要商议要事,开了一个会议,鸟,鱼,兽都齐集了,单是缺了象。大家议定,派伙计去迎接它,拈到了当这差使的阀的就是狗。“我怎么找到那象呢?我没有见过它,也和它不认识。”它问。“那容易,”大众说,“它是驼背的。”狗去了,遇见一只猫,立刻弓起要来,它便用得,同行,将写着符梁的猫介绍给大家道:“象在这要”但是大学都重笑它了。从此以后,狗和猫便成了仇家。
国来量人走出森林虽然还不很久,学术文艺却已经很可观,提是书强的装源,玩具的工致,也无不令人心爱。独有这一篇童话用实情不漂亮:结怨也结得没有意思。猫的弓起脊梁,并不是希图冒充,故造摸架子的,其咎却在狗的自己没眼力。然而原因也总可以作一个原因。我的仇猫,是和这大大两样的。
其实人禽之辨,本不必这样严。在动物界,虽然并不如古人所幻理的那样舒适自由,可是增苏②做作的事总比人间少。它们适性任情,对试对,错就错,不说一句分辨话。虫蛆也许是不干净的,但它们并没有自鸣清高;莺禽猛兽以较弱的动物为饵,不妨说是凶残的里,但它们从来就没有竖过“公理”“正义”的旗子,使牺牲者直到被吃的时候为止,还是一味佩服赞叹它们。人呢,能直立了,自然是一大进步;能说话了,自然又是一大进步;能写字作文了,自然又是一大进步。然而也就堕落,因为那时也开始了说空话。说空话尚无不可,甚至于连自己也不知道说着违心之论,则对于只能嗥叫的动物,实在免不得“颜厚有纽”。假使真有一位一视同仁的造物主,高高在上,那么,对于人类的这些小聪明,也许倒以为多事,正如我们在万生园里,看见猴子翻筋斗,母象请安,虽然往往破颜一笑,但同时也觉得不舒服,甚至于感到悲哀,以为这些多余的聪词,但不加成有的好黑。然丽,既经为人,便也只好“党同伐异”学着人们的说语,随俗来谈一谈,——辩一辩了。
都看到这了,点个关注吧。
经典图书朝花夕拾第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