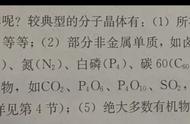童年记忆中,春天总是在“吭哧吭哧”嚼着折耳根的声音中度过的。
折耳根应春季而生,春天来的时候,它像深埋在地下的竹笋似的,一下子全冒出了地面;春天走后,它又如人间蒸发般突然消失不见,再也寻不着它的影子,来无影、去无踪。
挖折耳根,是我和妹妹小时候最开心的事,贫瘠的土地上长出来的折耳根,根茎细弱,根须多,叶子卷曲,一看就是营养不良,这种是入不了我们眼的。寻得一片阴暗湿润的土地,扒拉开杂草,一片片褚红色、泛着点油光的叶子便露了出来,迫不及待的用锄头挖起来一大块泥巴,再用手轻轻的去掉包裹着折耳根的泥土,这个时候要非常小心和细致,稍一用力,折耳根便折断在了泥土里,运气好的话,手掌大的一块泥,便可择出一小把。这种带大片叶子的折耳根吃起来酸味比较浓烈。
如果不喜欢吃酸,则需要去寻找更加肥沃的沙土地,这时候,连锄头都省了,只要看着有个小指甲盖大小的叶子,用手刨去疏松的沙土,白白嫩嫩的一截、粗比中性笔芯的根茎映在了眼前,还有未来得及破土的折耳根也一并被刨了出来,这种在白嫩的根茎头处,带有一小截粉嫩的牙尖,没有一点多余的根须,在阳光的照耀下,更显得白皙柔嫩,像初生的婴儿肌肤,拿在鼻端轻嗅,有一股甜甜的又夹杂着一丝原始的青草香味儿。
这种是最好吃的,来不及拿回家,拍干净附着的泥土,拿一根轻轻的放进嘴里,脆脆的、甜甜的、微微的酸,充斥在身体的五脏六腑,不需要任何的调料,有生之年尝一尝这来自大自然、最原始的味道别有一番滋味儿。
另一种味道也让人难以忘怀,洗干净的折耳根放进白瓷盘里,铺上一层葱花、蒜粒、红椒粒、青椒粒,倒入酱油、醋,撒一点白糖,“刺啦”一声,一勺热油浇下去,香味已经溢满了整个厨房,妈妈还未来得及拌开,已经被我和妹妹抢着端上了餐桌,两双筷子不停地伸向盘子,眨眼功夫,盘底只剩下一点碎屑,但是我们连这一点碎屑也不肯放过,把它拌进米饭里,就着这一盘野菜,我们便可干掉一碗白米饭,它带给味蕾的满足感绝不啻于一顿红烧肉。
离家越久,越想念那个味儿,钢筋混泥土的城市,哪里能寻得那样的一片净地呢?在市场上买过两次,一次买的是没有叶子,只有白色的根茎,一根足足有半寸长,拌上调料,吃着明显有一股药味儿;另一次是买了带叶子的,不过每一根都同样大小,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样,一盘将尽,也没品出一点折耳根的原本味道,至此,便死心了。
后来,在贵州吃到了一份折耳根炒腊肉,腊肉的醇香和折耳根的清香混在一起,倒是头一回遇见,也不失为一次美味的体验。可惜的是,不知是腊肉的咸,还是老板多放了盐,最初几口过去,再吃,便感觉是一勺盐进了胃里,再也无法下咽,可惜了这里面的折耳根,要是像我小时候那样凉拌着吃,该是多么美味。
虽然最原本的折耳根味道吃不着了,但它又以另外的方式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这便是鱼腥草,鱼腥草是折耳根的药用别名,有清热、解毒、利水之效,常用作治疗肠炎、痢疾、肾炎水肿、乳腺炎、中耳炎等。小时候,妈妈常常将已经开过花的、比较老的鱼腥草混着一点五花肉熬在一起,据说是女孩子喝比较好,我每次都要喝上好几碗,这样一碗夹杂着肉味和鱼腥草鲜香味的汤倒进肚里,从唇齿到胃都被熨烫的服服帖帖。
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不论是儿时凉拌的折耳根,还是熬成汤的鱼腥草,它们都将离我越来越远,忘不了的味道只能永远地被封存进记忆里,隔一段时间便拿出来翻一翻、晒一晒,表示我与它们还在联结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