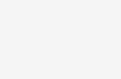西南联大时期(左为李荣,中为汪曾祺,右为朱德)
跟萧珊女士同年,汪曾祺也于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不过汪曾祺留下教书,最青春的7年留在了昆明,之后才返回上海工作。不过,先生曾多次重返昆明,昆明虽好,可能大学时期的一些记忆更能让人记忆犹新吧。他还说,昆明是自己的第二故乡,因为除了高邮,北京,就属昆明待待最久。可能除了昆明话他说的不顺溜外,俨然一个“老昆明”,在昆期间写下了《七载云烟》、《天地一瞬》、《斯是陋室》、《昆明年俗》等完完全全写昆明生活的就有43篇,虽然那时候生活艰苦,但是,昆明的雨,昆明的花,昆明的菌子,昆明的翠湖和茶馆,在他眼里,都是美好。

《昆明的雨》片段
可以说,昆明对他来说是乡愁,他对昆明来说又是知己。有人说,读他的文章,可以看到昆明如世外桃源一般地令人向往,也因此,人们来昆明旅游,也经常到翠湖走走,文林街瞧瞧。一生偏爱吃喝到他,却把昆明的雨写的饱满,令人舒适,一种魂牵梦绕的昆明情结,总让人回到他的年代感同身受,古稀之年还千里回昆,寻觅年代足迹,而这篇文章却是他1984年才写的,先生回想起了呈贡的干巴菌,青头菌,还试图描述清代昆明莲花池边吴三桂和陈圆圆的故事,“雨又下起来了”,先生会走上小街,跟店家要点猪头肉和半市斤酒,雨一直下,就一直感受着……

实际上,汪曾祺先生的恩师就是大名鼎鼎的闻一多先生,而闻一多先生这时还教授这《古代神话》,所不同的是,闻一多先生能够讲几句昆明话,比如“你们到这点来整哪样?”值得一提的是,闻一多先生是湖北人,汪曾祺先生是江苏高邮人,这可能也是闻一多先生容易习得昆明话的一个原因吧。

而闻一多先生的昆明旧居就在翠湖边上,西仓坡走到底就能看见的闻一多文化艺术走廊。这里也是先生在1946年7月15日做完《最后一次演讲》被暗*的地方。实际上闻一多先生在昆明搬过8次家,住的最久的还是司家营17号与朱自清先生在一起建设昆明清华文学部之时,他在这里住了2年多,不过生活还是过的清苦,1942年初,龙头街的物价虽然比城里低一点,但鸡蛋也要2元一个,花生20元一斤,鸡45元一斤,牛肉16元一斤,而教授的薪水不过千元左右。为了省钱,他上下课经常靠走路,由司家营的田间小道,过盘龙江霖雨桥走到岗头村,再沿公路到学校,上完课又回到司家营。1944年5月,先生还为生计兼任昆华中学(昆一中)的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