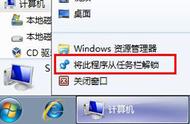作者:邹 红
1934年7月,曹禺处女作《雷雨》发表于《文学季刊》。次年4月,一个由中国留日学生组成的话剧社团“中华同学新剧会”(又名“中华话剧同好会”)将这出戏搬上舞台,27日到29日,在日本东京的神田一桥讲堂连演三场(一说后来又加演了两场),就此拉开了曹禺剧作在海外传播的序幕。尽管这轮演出用的是中文,导演、演员都是中国留学生,甚至台下观众也以中国留学生为主,但提议排演《雷雨》的却是两名日本青年——武田泰淳和竹内好。正是他们在1934年暑期将发表在《文学季刊》上的《雷雨》剧本推荐给中国留学生杜宣,才有了后来载入史册的东京演出。

《雷雨》法汉对照本

《北京人》英译本

日本民艺剧团在东京用日语公演《日出》剧照
海外演出经久不衰
从1935年《雷雨》在日本东京演出开始,直到21世纪,曹禺剧作在海外盛演不衰,给一代代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海外传播方面形成了与其他现代文学大家不同的特点。
曹禺剧作与日本似乎有着某种不解之缘。曹禺的第二部剧作《日出》,在剧本刊出一年之后,于1937年3月19日至21日在东京上演,地点还是一桥讲堂,演出者也还是一群中国留日学生,而此时距《日出》在上海卡尔登大剧院首演不过一月有余。
很自然地,日本成为曹禺剧作在海外演出的重镇。据学者曹树钧《曹禺剧作在日本的演出和研究》介绍,“从1935年到1985年半个世纪之中,在日本本土先后演出过《雷雨》《日出》《原野》《家》《蜕变》《明朗的天》6个大戏,几乎曹禺的主要剧作在日本全都上演过”。其中既有上述中国留日学生的演出,也有国内专业剧团如上海人艺的演出,而更多的是日本专业剧团如东京的民艺剧团、稻之会剧团的演出。新世纪以来,曹禺剧作在日本仍时有上演。如2006年11月,北京人艺首度赴日在东京演出三场《雷雨》;2017年10月和2018年2月,由旅日华人组建的东京话剧艺术协会两次演出《雷雨》。
曹禺剧作在日本以外的亚洲国家也多有演出,如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菲律宾等,尤以韩国和新加坡为最。韩国的情况与日本相似,自上世纪40年代以来几乎上演了曹禺所有重要代表作,且其演出主要为韩语;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则因华人众多的缘故,演出者多为华人社团。
上世纪50至60年代,中国与苏联及一些东欧国家同属社会主义阵营,文化交流频繁,曹禺剧作因此得以登上这些国家的话剧舞台。据相关报道,上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苏联多家剧院上演了《雷雨》,罗马尼亚、捷克、阿尔巴尼亚等国也将《雷雨》搬上舞台,匈牙利则选择了《日出》。上世纪80年代后,曹禺剧作再度受到关注,苏联、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国都有新排《雷雨》上演。
1946年3月,曹禺应美国国务院之邀访美。同年8月,美国华人演出了中文版《北京人》,这应该是曹禺剧作在美国的首演;1949年4月,英文版《北京人》在洛杉矶城市学院上演,演出者为洛杉矶州立大学和城市学院戏剧专业的师生。1953年4月,英文版《北京人》在纽约再次上演。1980年春,曹禺二度访美,由此引发了曹禺剧作在美国演出的新一轮热潮。曹禺访美期间,哥伦比亚大学曼西小剧场和纽约辣妈实验小剧场分别上演了《北京人》和《日出》;1982年,英若诚在美以客座教授的身份指导密苏里大学戏剧系学生排演了《家》,以上演出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得到美国戏剧界好评。此外,1986年1月至2月,南开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学生在美籍教授费希尔指导下排演的《雷雨》赴美巡演,先后在明尼苏达大学、斯坦福大学等10所高校演出11场,增进了中美间的文化交流。
除了以话剧形式传播之外,歌剧《原野》也出现在域外舞台上。1992年1月,华盛顿歌剧院制作的歌剧《原野》在美国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上演;1997年7月,上海歌剧院携《原野》赴德国和瑞士演出,扩大了曹禺剧作的海外影响。
经典剧作翻译研究受重视
《雷雨》也是曹禺第一部被译成外文的剧作。1935年《雷雨》在东京演出时,东京帝国大学的日本学生影山三郎观看演出后,认为这是一部应该让更多人了解的作品,遂与中国留日学生邢振铎合作将《雷雨》译成日文,于次年2月由东京汽笛出版社出版。1953年,影山三郎又据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51年新版《雷雨》对之作了重译,由未来出版社出版。除《雷雨》外,曹禺的其他重要作品如《日出》《北京人》《原野》《蜕变》《胆剑篇》等也相继被译成日文出版。
就在影山三郎将《雷雨》译成日文后不久,中国学人姚莘农(姚克)也开始了对《雷雨》的英文翻译,其译文于1936年10月到1937年2月分5期连载于《天下》月刊。这是《雷雨》的第一个英译本。1946年曹禺访美期间,曾与美国戏剧家、导演李吉纳尔·劳伦斯共同整理过《北京人》的英译本,但未公开。1958年,中国外文出版社出版了由王佐良、巴恩斯翻译的英文版《雷雨》;1960年,巴恩斯又将《日出》译成英文。这些译本对曹禺剧作在英语世界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1949年、1953年在美上演的《北京人》用的就是曹禺和劳伦斯的整理本,1986年南开学生剧团在美演出的《雷雨》剧本则是费希尔据王佐良、巴恩斯译本改编的。
曹禺剧作其他语种的翻译亦颇为可观。田本相在《曹禺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中谈到,《雷雨》除了有英、法、德、意、西班牙语等译本外,在越南、朝鲜、韩国、蒙古等国也有不同译本出版,日本最多。其中越南在上世纪40至60年代翻译出版了《雷雨》《日出》《明朗的天》《胆剑篇》《北京人》;苏联于1961年翻译出版了两卷本《曹禺戏剧集》,收入《雷雨》《日出》《北京人》《明朗的天》4部剧作;韩国在1946年首次将《雷雨》译成韩文后,自1989年开始又陆续翻译出版了《日出》《原野》《蜕变》等多个韩文译本。
与演出、翻译相伴而来的是海外学人对曹禺剧作的研究。继早期的观后感、剧评和介绍性文章之后,约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海外曹禺研究渐趋专业化、学术化,出现了一批较有深度的研究著述。
海外各国的曹禺研究中,日本学人可谓用力最勤,不仅起步早,涉及面广,而且多有真知灼见。其最有代表性者,如庆州大学教授佐藤一郎在1951到1954年间发表的系列论文,充分肯定了曹禺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地位和融中西于一炉的艺术创造性。年轻一代学人饭冢容,作为日本曹禺研究领域的后起之秀,从1976年以来陆续发表了多篇有关曹禺及其剧作的论文,分析曹禺剧作与外来影响的关系。此外,饭冢容向日本国内介绍中国曹禺研究的文章《关于钱谷融的〈《雷雨》人物谈〉》《最近的〈北京人〉论》以及向中国学界介绍日本曹禺研究状况的《日本曹禺研究史简介》、考查中日话剧交流史实的《中国话剧的发展与日本》等,在中日曹禺研究领域都受到重视。
苏联学者B·彼特罗夫为两卷本《曹禺戏剧集》撰写的介绍文章《论曹禺的创作》,全面评述了曹禺的创作道路及作品风格,认为曹禺是一位卓越的剧作家,获得了全民族、全世界的声誉。再如美籍华裔学者刘绍铭1970年出版的《曹禺论》,是他1966年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有关曹禺剧作所受外来影响的见解颇有可取之处。台湾学者胡耀恒,韩国学者韩相德、李康仁等的博士论文也以曹禺为研究对象。这无疑表明曹禺及其剧作在海外学人心目中的价值,也预示了未来海外曹禺研究还有更大开拓空间。
堪称中国话剧一代宗师
曹禺剧作最早登陆日本,又在上世纪50至60年代受越南、苏联和东欧诸国关注,上世纪80年代集中在美国上演,上世纪90年代被韩国大量译介,与国家间的文化、地缘、政治关系等有十分密切的联系。此外,曹禺剧作在海外的传播也存在偶然因素。倘若不是武田与竹内两位将剧本推荐给杜宣,1935年《雷雨》在东京的演出也许就不会发生。再比如说,倘若没有费希尔教授在南开大学的热心指导和多方联系,恐怕也就不会有南开学生剧团的赴美巡演。
但自另一角度看,偶然之中又包含了某种必然。我们注意到,随着海外剧评人和研究者对曹禺剧作认识的渐趋深化,对曹禺作为剧作家的评价明显呈上升态势。
以日本的曹禺研究为例。早期的评论其实并非都是称誉,1937年,土居治就认为曹禺的《雷雨》《日出》“不过是习作而已”“不能给予过高的评价”;但佐藤一郎1951年发表的《关于曹禺的〈雷雨〉》则认为:“曹禺是中国现代戏剧的确立者和集大成者”,他“吸收并消化了丰富的西方现代戏剧传统元素,在此之上形成了他中国化的独特风格,进而创作出具有世界性价值的一系列作品”。应该说,佐藤一郎的上述见解的确表现出某种前瞻性,也从一个侧面证实:我们对曹禺及其剧作的认识越是深入,就越能感受到他作为一个剧作家的伟大之处。美籍华裔学者刘绍铭也曾认为曹禺剧作“浅薄”,但1980年在美国与曹禺会面后,他坦言:“如果我今天重写《曹禺论》,我对他剧作的评价,会高许多……在中国话剧史上,他实在是一代宗师。”
因此,真正决定曹禺剧作走向世界的必然性因素,是其本身所蕴含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是曹禺作为剧作家的卓越才华。正是曹禺剧作的丰厚底蕴,决定了它外行可观热闹,内行能窥门道。关注社会问题者不难从中看到封建大家庭的专制,希望了解人心者也可感受到人性的多样与复杂,而喜爱戏剧创作者则可将其作为学习的范本,导演、演员更将排演曹禺剧作视为荣誉,尽全力于二度创作中一试身手。
这样我们便不难明白,为何《雷雨》会成为中国话剧海外演出场次最多,同时也是外文翻译语种最多的剧作。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本文配图由曹禺之女万方提供。)
来源: 人民日报海外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