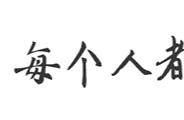乌尔里希·德吕纳(Ulrich Drüner)的《瓦格纳传》是一部雄厚扎实的大传,洋洋洒洒、宏阔恣肆,主题鲜明深刻,与其说它书写的是享誉世界的德国大音乐家理查德·瓦格纳(1813—1883)的生平事迹,不如说它研究的是“瓦格纳神话”是怎样炼成的。

《瓦格纳传》(德)乌尔里希·德吕纳译林出版社
瓦格纳如何“自我神话”
《瓦格纳传》一书引言即以《传记有多“真”?》为标题,指出了瓦格纳自传《我的生平》一书的不靠谱,以及传记作者们对“瓦格纳神话”的进一步强化。
作者德吕纳说,由于早期的信件出版并不完善,已知的直到1849年流亡之前的瓦格纳信件的数量,不足以描述他生活的准确情况,因此,瓦格纳前半生的生平至今都依赖于他的自我描述。德吕纳依靠其他人的信件、日记,当时的记载和文献等材料,利用21世纪的一切手段去复核一切有疑问之处,推论瓦格纳个人陈述里的那些矛盾之处,力求呈现这个自1840年以来日益强大的神话的整体性和复杂性,以看清瓦格纳的动机、策略和行为方式。
瓦格纳在自传《我的生平》里对其前妻明娜多有恶言。明娜因此被人们认为是自私嫉妒的恶妇、愚妇。德吕纳核查比对了瓦格纳的早期信件以及明娜本人的存世信件和文件,书中直接呈现的引文片段显示,瓦格纳曾热烈澎湃地爱过明娜,而明娜也“敬爱和崇拜”着丈夫的音乐。德吕纳还把两人的感情描述为母亲般的温柔和孩子般的依赖,她的理性一度引领他走出迷茫,她陪同他一起逃亡,以至于马车翻覆压在她的身上,造成了流产,再也不能*。

瓦格纳肖像
对前辈也是如此。“我是迈耶贝尔的学生!”瓦格纳曾经以此致敬这位比他大22岁的前辈音乐家的提携。但后来,瓦格纳把迈耶贝尔视作大敌,一有机会就在各种场合诋毁迈耶贝尔。导火索是因为迈耶贝尔把瓦格纳从大歌剧院引荐到文艺复兴剧院,没多久,文艺复兴剧院就*了,瓦格纳认为这是迈耶贝尔的阴谋。德吕纳遍查迈耶贝尔的记录和剧院相关人等的材料,包括瓦格纳后来针对迈耶贝尔的指责,所有能找到的都只是瓦格纳单方面的看法,没有任何书面信源能够证实迈耶贝尔对瓦格纳有恶意。

巴黎文艺复兴剧场,瓦格纳曾在此举办三场音乐会。因被迈耶贝尔引荐至此,剧场*后,瓦格纳对迈耶贝尔多有诋毁。
对于那些帮助过他的人,瓦格纳后来的态度总是糟糕的。瓦格纳指责出版商施莱辛格是剥削者,德吕纳对比当时的物价水准和音乐家薪酬,认为这种指责是不合理的。瓦格纳利用喜爱他的国王、路德维希二世的赦令平息自己与柯西玛的绯闻,使得国王处于尴尬的境地,柯西玛当时是瓦格纳的好友、乐队指挥汉斯·冯·比洛的妻子,这则绯闻也令柯西玛的父亲、大音乐家李斯特颇为难堪。
这部作品并非流于表层的叙事体传记。德吕纳的目的不在于讲述故事,更重要的是,探讨作为浪漫艺术家的瓦格纳的生活策略。正如德吕纳所说,瓦格纳是在什么样的困难条件下创造的艺术,这个问题像一条红线一样贯穿本书。
瓦格纳冀望获得权力,攀登个人荣耀的顶峰。攀登的过程必须要遇到很多困难,这样才够传奇,才能成为偶像,且这些困难当然都不能是自己的原因造成的,而是出自于爱情的不如意、婚姻生活的不美满、朋友的背叛、敌人的设陷、时代对艺术和艺术家的漠视等等诸般理由,只有突破了这些窘厄困境的艺术家,才是伟大的,才成为众人眼里的神话。
从“人格神话”到“民族神话”
德吕纳拿着解剖刀,一层一层剥除瓦格纳的神话外衣,然后,一步一步地进入了瓦格纳的内心世界。除了对瓦格纳个人的性格特征进行分析之外,德吕纳还侧重于对组织和社会环境、政治发展、艺术和文化影响进行历史的考察,把瓦格纳放回了他的时代。
19世纪的欧洲,音乐家并不像现在那样受人尊敬,充其量不过是二流地位的艺人,如果没有一群贵族的扶持和一群追随者的支持,很难有大成就。在瓦格纳的例子中,只是那些被牺牲的男人女人似乎与他的关系曾经更加亲密,也就更显得瓦格纳无情罢了。

瓦格纳在特里布申的三角钢琴
在瓦格纳制定的战略人生规划中,遇到的最大困难实际上是金钱问题,但这不怎么符合“神话”的逻辑,也会暴露他在财务上的无能,所以,瓦格纳要制造一个“劲敌神话”,英雄必须身陷危境,与敌人搏斗,才能成为被众人赞颂的英雄。瓦格纳接受了19世纪的社会法则,接受了他从中世纪美学里获得的启示,从而改写了他在巴黎的落魄遭遇,把自己的失败者经历塑造成了贫穷、无畏、怀才不遇而努力奋斗的艺术家神话。
德吕纳分析了“奢侈”和“爱情”在其中的作用。瓦格纳酷爱收集精致昂贵的家居用品,这是缠绕他终生的财务问题的源头,但是,这些奢侈品在感性创造力方面能够引发瓦格纳的灵感,瓦格纳描写过自己触摸沙沙作响的锦缎,在帷幔、香水、图画等物品围绕下产生的中枢神经兴奋感。对于瓦格纳的艺术创作来说,“不能实现之爱的戏剧性”是他的戏剧作品的重要主题,而他也把自己对生活、爱情的体验与对戏剧人物的认同感形成了映射”。
瓦格纳的复杂性还体现在,他不仅要创造“人格神话”,到了后期,他还将其上升为“民族神话”。这部传记对瓦格纳美学思想的形成和演变有很多剖析。瓦格纳回避了自己在迈耶贝尔这位犹太人老师那里学到的“主导动机”创作理论,刻意减轻了自己美学思想里的黑格尔源头,而强调了较晚才接触的叔本华哲学对他的影响。晚期瓦格纳强调德意志国家意志,认为“国家复兴”必须在国家主导下进行,奉行一种差异化的反犹策略,在作品里积极塑造“日耳曼天性”、“理想主义的宏伟类型”和“梦想中纯粹美丽的原初的人”。
“恶棍”还是“精神导师”?
瓦格纳写过三部自传性作品,包括《自传草稿》(1843)、《告友人书》(1852)和大部头的《我的生平》(1865-1880)。自传和回忆录往往是“伪装的艺术”,自恋的瓦格纳擅长这门艺术,把真正的自我层层伪装。因此瓦格纳传记的作者需要抵制这类艺术的诱惑,花更大的力气去发现面具背后的真相,从这个角度来说,德吕纳的传记做得相当好。
德吕纳长期学习音乐和音乐理论,以研究瓦格纳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此后从事音乐工作和瓦格纳研究。这部《瓦格纳传》剖析了瓦格纳的生平思想与其作品产生的密切交汇,对瓦格纳的音乐创作有许多专业阐释,包括对《唐豪瑟》《帕西法尔》《女武士》《尼伯龙根的指环》等作品的精彩评述,对《音乐中的犹太性》等文艺理论作品的清晰洞察等。德吕纳虽对瓦格纳的“自我神话”有批评,但站在艺术的角度,他也表达了一些理解和回护。

瓦格纳《帕西法尔》第一幕手稿
德吕纳援引现代心理学的“建设性受挫”概念,指出持续的创造性亢奋不仅需要被引发,还需要保持。他评价瓦格纳是个极端自私者,但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私者,他“被他的魔鬼攫住”了,他是为了他的艺术,他是如此地沉醉其中,他的力量不仅是针对外部的,还以一种自我毁灭的精力针对着他自己。
晚年的明娜发出她的质问:一个才华横溢的人是否就有了做恶棍的权利呢?以明娜的立场而言,的确可以称瓦格纳为“恶棍”。
20世纪的知识分子,视瓦格纳为“恶棍”的也不乏其人。比如法兰克福学派代表西奥多·阿多尔诺。阿多尔诺严厉而尖锐地抨击了瓦格纳,从私德到作品的艺术水准。阿多尔诺认为,瓦格纳作品对于犹太人的丑化是低级的,以笑声搁置了正义;瓦格纳把自己遇到的困难归咎于犹太人的阴谋,是让人无法容忍的妄想狂;瓦格纳的人物浅薄无聊,音乐中的寓言僵硬刻板;瓦格纳音乐的形式结构和旋律结构在技术层面尚还存在着许多矛盾……
相比而言,尼采的态度更公允。众所周知,尼采一度将瓦格纳视为知己。他们都对“现代性”抱有深刻的怀疑。瓦格纳的音乐剧在年轻的尼采心中唤起对重建德国精神生活的希望。在神话的一种轮回以及启动意识之神话构造的潜能的意义上,尼采寄希望于形而上学的慰藉,赞赏瓦格纳作品创造神话的力量。但尼采后来选择了与瓦格纳分道扬镳,因为他感觉到瓦格纳的事业是“让有意识的妄想取代现实性”,就不再允许自己让理性失去效用,而沉溺于审美的神话的幻想。尼采反对瓦格纳,是美学道路的自觉选择,在瓦格纳逝世之后,尼采在悼文中写道:“我们要相信我们的星辰友谊,即使我们不得不成为尘世上的敌人。”
鉴于瓦格纳的深远影响力以及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方面造成的后果,围绕瓦格纳的讨论是不可能消散的,理查德·瓦格纳是历史无法忽视、让人仰望的巅峰人物,“瓦格纳神话”总会得以缔造,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责编:张玉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