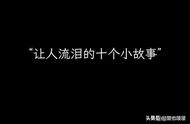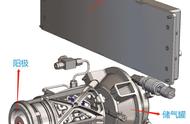父亲走了
作者:余兴喜
我亲爱的父亲于2024年3月12日农历二月初三的下午6点半,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父亲出生于1932年农历壬申年五月二十二,今年虚岁93。
二月十二,安葬了父亲,回到父母亲长期生活的地方,也是我们兄弟姐妹出生的地方——周圪崂老家的家里。这里已经没有了前几日丧礼期间的喧嚣,我也没有了这些天的忙碌和劳累,突然觉得心中“空”得发慌。一种非常强烈的感觉,我得再为父亲写点什么。
这些天,有好多人写了悼念父亲的文章和诗词,张贴在十多块展板上;昨天的追悼会上,又有好多人发言。因时间限制,不少人没有得到发言的机会。大家在文字和发言中回顾了父亲的很多往事,对父亲评价极高,我看了、听了都深受感动。好多人拿父亲与历史上的伟人、圣人相比,有人说他就是伟人、圣人。我知道,他们这么说,都是带着感情的成分。客观地说,父亲肯定不是历史书中的伟人、圣人,但他在某些方面或许会胜过某些伟人、圣人。
在昨天的追悼会上,我讲了父亲可以引以为傲的几个方面:一是聪明好学,能力超群;二是重视教育,矢志办学;三是竭力为公,改变面貌;四是重信重义,热心公益;五是刚正坦荡,自律自强;六是独立思考,坚守原则;七是勤俭持家,父爱深沉。这几个方面,肯定不能完全概括父亲的品格和贡献。关于父亲,我曾在2021年12月写过一篇《大大》(我们兄弟姐妹一直把父亲叫大大),献给父亲91岁生日。尽管父亲说这篇文章把该写的都写了,但我总觉得还是挂一漏万。本篇文字就算是对《大大》一文的一些补充吧。

(2024.3.12农历二月初三当天的照片)
(一)
很多人讲到了父亲的聪明好学、心灵手巧,说他是木匠,也是铁匠、皮匠、绳匠、裁缝。农村用的柴油机等各种机器、车辆、农具他都能修,而且全都是无师自通。公社农机修配厂从成立时到包产到户后撤销,父亲一直是厂长,或许能说明大家对他的技术和能力的认可。这次追悼会上有人讲到父亲建设万家畔大桥的事。黄蒿界公社(后改为乡政府)办公地曾经在万家畔,万家畔的“畔”就是河畔的意思,这个河就是黑河。由于万家畔位于黄蒿界版图的北部,全公社多一半地方的人去公社(乡政府)办事必须在万家畔过河。河上的桥几十年来都是用木桩做支撑的木桥,即使修了公路后仍然是这样。这样的桥遇到稍大一点的洪水就会被冲垮,只能垮了再修,差不多是年年都要重建,父亲也曾多次参加过这座木桥的重建。1977年,公社决定修一座结实一点的桥,但公社没钱,还是要就地取材。经与父亲研究,决定修一座砖拱桥,并请父亲主持修建。父亲果然不负众望,桥修好后,一直用到1995年。这座桥跨度达18米,当地人一直叫它万家畔大桥,在靖边县县志上也有记载。就现代建桥技术来说,这样的桥梁可能没有什么难度,但对于一个从来没有上过学,从来没有学过、做过拱桥建造的人来说,能成功建成这样一座砖拱桥,不能不让人称奇。
在父亲眼里,很多人都太笨。我们从小到大,经常听到父亲说的一句话就是“怎么会有这么笨的人!”

(1995年父母亲在美国)
(二)
他这么说,似乎是一种“恨铁不成钢”,并没有不尊重他人的意思。他对所有人都尊重,所有人也都尊重他。父亲古道热肠,乐于助人,热心公益。我在《妈妈》一文中所写的妈妈对很多人的接济,其实也是他们共同的行为。记得我小时候和后来在农村时,村里人经常找父亲给他们修理农具、家具以及做装铁锨把之类的活,尽管纯粹是义务帮忙,父亲从未拒绝过,都是利用工余时间给他们做得妥妥贴贴。这次父亲葬礼上,由几个自然村联合办起来的庙会送来挽幛。我问是咋回事,老会长说这个庙会是父亲承头办起来的,“没有你父亲就没有这个庙会”。在清理父亲遗物时,发现父亲手写的《祭祖文》、众多墓碑碑文设计图和家谱等文稿,原来家族里祖坟立碑,去榆林老家续家谱,父亲都是承头人。

(2012.1.29在海南)
(三)
最让大家佩服的,还有父亲的见解。村里人、亲戚遇到什么事,往往喜欢来找父亲说说,听听他的意见。这次很多年轻人的悼念文章和发言,都提到父亲对他们的教诲。
父亲对任何事,都要独立思考,琢磨明白,从不轻信,也不人云亦云。他认为不对的事,他从不参和。对于过去的历次运动和社会现象,甚至各种国内、国际大事,他都有自己独立的看法。这一点上,往往比很多高级别的干部、专家学者都强。
我经常想,父亲一个没有上过学、没有多少文化的人,为什么经常会有那些堪称真知灼见的见解呢?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从来不迷信任何人,不迷信任何说教,从常识出发,从“理”出发,以及他的似乎是与生俱来的逻辑思维能力。父亲认为,万事万物都有个“理”管着,他干活比较“巧”,自己琢磨设计了土测量仪、加大柴油机皮带轮(参见《大大》),依据的是“理”;人与人相处,不论是家人之间相处还是世人之间相处,都要依“理”,依“理”就和顺,不依“理”就起矛盾;社会上甚至国际上,一件事做得对不对,就要看合不合“理”。
今年春节前我回去陪父亲过年,大年三十中午,我和五弟兴亮陪父亲到广场上走走。我们边走边拉话,坐下来休息时说到1966年公社开始批走资派。一开始他认为现在很多干部不好好为老百姓办事,是应该整治整治了,因此开会他也积极参加。当时公社社长是姬广业,这个人“茬硬”,加上公社*长期不在位,管事多,得罪人也多,所以第一个被批的走资派就是姬广业。其实后来回过头来看姬广业属于好干部,顶上姬广业的干部也不多。马季沟队多年来两派闹矛盾,那年队里的黑豆被人偷了,公社派人去调查无法破案。公社干部回去后的第二天还是第三天,队里又有人去公社报告说发现线索了。公社干部再去调查,原来是从丢黑豆的地方到某人家里一路都有掉下的黑豆。公社干部确认他们先前调查时在四周都仔细看了,当时并没有现在所看到的掉下的黑豆,判定是有人想栽赃。此事最终无法破案,也就搁置起来了。批判姬广业的时候,批判者质问姬广业:“马季沟的事为什么不处理?”姬广业答:“没闹清楚。”又问:“为什么没闹清楚?”姬广业答:“能力不够,没本事闹清楚。”又问:“为什么没本事?”父亲说,他当时一听,这还是些话?不讲道理么。从此以后,他再也不参加这样的批判会了。父亲因为耳朵背,说话声音大,邻座椅子上的一位中年男子听了父亲的话很惊讶,对我们说:“哎呀!这个老汉不简单。”
那时候搞“斗私批修”,“很斗私字一闪念”,提倡“大公无私”。父亲说,因为大多数人在公与私的问题上先替自己打算,这么提倡有道理,就是要让那些私心重的人私心轻点。但要完全无私,一闪念也没有,世界上应该没有这样的人,而且也没必要这样要求。公和私并不完全矛盾,公家的事、私人的事都要做好,遇到矛盾时把公家的事摆在前面就相当不错了。自家的事都管不好的人能管好公家的事?老百姓选生产队队长,敢选那些连家里都管不好、日子过得一塌糊涂的人吗?当干部要公道、公平、心正、君子、肯吃亏,一心一意把公家的事办好,但不需要你只顾大家不顾小家。
父亲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公家的事情要做好,自己家的事也要做好。他是一个肯吃亏的人,那时候给生产队做木匠活、铁匠活,工具都是自己买的,在生产队只挣工分,而且很多活都是工余时间做的。他当队长,几乎每天都是最晚收工的。晚上除了开各种会,在家里还要在煤油灯下写写画画,做各种设计和安排,而这一切都是没有报酬的。这些都堪称大公无私,但父亲说,要把公家的事办好你就不得不牺牲个人利益,但完全无私他做不到也不愿意做,也不希望别人这么做。父亲两度给合作社和生产队当会计,前后加起来有六七年。记得我们小时候经常有县里、公社干部来家里查账,一查就是好几天。父亲的账目从来没有查出过任何问题。正是因为他的公道、公平、心正、君子、肯吃亏,他才得到了大家的普遍信任。
在做人处事上,父亲也有一套自己的原则,而且从不突破。父亲喜欢用一些谚语或古书上的话来说明他的做人原则,教育和要求后代,如“若要好,打个颠倒”,“吃得小亏不吃大亏”,“平时不做皱眉事,世上应无切齿人”,“为人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敲门”,“求人不如求己”,“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上致君,下泽民,扬名声,显父母”,等等。

(2021.4.1在北京)
(四)
我们小时候,家里人多但劳动力少,连续好多年都要“出粮钱”。那时候,生产队干活的苦本来就很重,但父亲为了家里有“出粮钱”的钱,让一家人过上好一点的生活,让我们弟兄们都能接受比较好的教育,经常利用晚上和下雨天等工余时间做木活,有时候晚上干活干到很晚。
父亲对子女们要求严格,平时对子女们也比较严肃,很少流露出他内心柔软的一面。我在《大大》一文中写过,我1976年当兵离开父母后,1979年第一次探家,在离家约两三里的西梁下车后往家里走,父亲不知怎么很远就认出我来了,我从坡上往下走,父亲从坡下往上跑,相遇时看见父亲哭得像个孩子,眼泪和鼻涕一起往路上滴。这些天在老家,利用早晚没事的时间,我走了很多留下父亲踪迹的地方,每个地方都有让人无限思念的故事。我三次来到当年与父亲相遇的那段路,这条路现在已经没人走了,依稀可见曾经的路的痕迹。

(父亲为我流泪的地方,依稀可见曾经的路的痕迹)
(五)
父亲的身体一向强壮,但人上了年纪,身体上难免会出一些毛病。
六十岁以后,每到冬天,就会有点气管炎的症状,哮喘,咳嗽。父亲常对我们说这是遗传的,说我奶奶和几个舅爷爷都是这个毛病,都是因为这个病去世的,他可能也躲不开。今年春节,我给父亲又带回来燕窝,父亲说他的气管炎就是吃这个吃得完全好了,现在不用了,看谁需要给谁吧。
父亲从2015年以来做过4次手术:
2014年,在北京朝阳医院做了个全面的身体检查,发现有腹主动脉瘤。医生建议先观察一年,如果没变化就定期检查,如果增大了就考虑手术。一年后的2015年10月再在北京朝阳医院复查,发现瘤体增大。之后在北京安贞医院重新检查确认,10月27日在该院做了覆膜支架手术。
2021年3月,因小便有颜色,发现膀胱上长了个东西,被诊断为膀胱癌,需要手术。由于存在髂动脉瘤,为保证膀胱癌手术中髂动脉瘤不发生意外破裂,3月11日,在北京航天中心医院血管科做了髂动脉瘤栓塞、髂动脉球囊扩张及覆膜支架手术。3月17日,在同一家医院的泌尿外科做了膀胱肿瘤激光切除和膀胱血块清除手术,并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膀胱灌注化疗。当时给父亲说,这是膀胱和尿路感染,癌症的事一直没有告诉父亲本人。手术后,没有再犯。
2023年6月6日下午,在周圪崂参加一个葬礼的现场,父亲突然出现心梗症状并肚子疼,在及时服用缓解心梗的药物后,父亲被紧急送到县医院。CT检查发现动脉血肿,医生认为有主动脉破裂风险,按医生建议,三弟兴华、四弟兴光他们用救护车连夜把父亲送到延大附属医院心血管医院。延大附属医院心血管医院进行了降血压等处理后,建议去西安的大医院。这样,又重新叫了救护车连夜送到西安,7日凌晨到达西安交大第一附属医院。当时的情况是肚子疼,呼吸困难,血氧低,动脉血肿,胸腔积液多。为慎重起见,我们找了北京、西安的多位专家咨询或会诊,最终于6月15日做了胸主动脉覆膜支架手术。手术后,没有出现手术前医生说的可能瘫痪等大的问题,但这场大病,让父亲的身体状况大不如前,走路走不动了,血压也高了,前列腺的问题也严重了。
除了这4次手术,还有几次较大的伤病,最终都有惊无险。2022年底的新冠流行时父亲因为肺炎正在输液,不可避免地感染了新冠,好在有朋友帮忙及时找到药,让父亲躲过一劫。

(2024.2.17正月初八还在骑他的三轮车)
二月初三,父亲的侄孙治宏在内蒙乌审旗四大队的家里给儿子办喜事请客,家人加客人有近两百人。父亲去了以后精神很好,大家都过来跟他打招呼,他也很高兴地跟大家说话。他觉得有点累了,就躺了一会儿,坐起来时可能有点猛,突然感觉腰疼,对身边人说:“我不对了,可能是血管出问题了,我得赶紧走。”兴华等人立即开车送父亲去县医院。有人拍了父亲上车时的照片,时间是下午5点10分。6点零7分在县医院开始做CT,发现腹部动脉出血,等做完CT,就量不到血压了,大约6点半左右人就走了。
我们过去经常给父亲说,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尽量不要弯腰,不要剧烈活动,一旦血管破了就没得救。最终,问题还是出在血管破裂上。
一个多月前回家陪父亲过年时,跟父亲睡在一个房间,睡在妈妈的床上。躺在床上,我们拉了很多话。父亲给我念叨,谁谁走得快没受罪,谁谁走得快没受罪。这次,也算如他所愿了,走得快,没受罪。在他走之前,还集中见了那么多他想见的人,就是没来得及见他远在外地的儿女。很多人说,父亲离去的方式,一如他一生做事和为人的风格,简单干脆,麻利栓整,干干净净,利利索索。
父亲离开的时间是二月初三下午6点半,跟两年前母亲离开的日子正好差一整天。有人说,如果今年正月不是小尽的话,就是同一天同一时刻。不知道冥冥之中,是父亲与母亲有约定,还是他为了儿女们方便?明年的这个时候,我们将同时给父亲过周年、给母亲过3周年。
父亲走了,从此我们就再也没有父母亲了。父亲走了,也带走了我们那么多的牵挂和期盼。
(2024年3月20日初稿于陕北老家,4月8日定稿于北京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