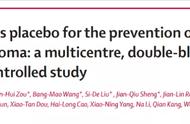一眨眼就是腊月。
虽是数九寒冬,冰霜铺地,但村庄蕴藏着灵性朝气、生机活力,彰显着英姿焕发,春心萌动。
池塘瘦了,河水静悄悄,似乎在等候着什么?等候村姑、村妇的相约,等候棒槌击打的跃动;草枯萎了,耷拉着脑袋,窥视,村庄人家“春”的大红喜字的张贴;聆听,村庄里的炮竹声声,它就可以穿上翠绿的新衣手舞足蹈了;树叶落了,但树干、树枝汁液汹涌,热血沸腾,昂着胸、伸直着腰向村庄眺望。春到,为春节喝彩!为春日鼓劲!
麻雀扑棱一声飞出屋檐,落在树梢,观望东方红红的云彩。
最先把麻雀吵醒的是我的母亲。她已把昨天洗净的几竹篮萝卜切成块状,倒在大盆里的木砧板上,双手抡起菜刀,一起一落,一落一起。咔嚓轰隆地响,似擂鼓。块状的萝卜碎了,只有黄豆粒般大小,把这拂下,又把块状的萝卜拢到砧板上,双手握刀,就这么一起一落,萝卜碎了。大点的不过黄豆,小点的只有米粒,俗称萝卜籽。这是过年做米粉萝卜粑、萝卜圆子的主要食材。过年,图的就是团团圆圆,那一家不做一些,吃一个正月。
萝卜、米粉在乡村是寻常之物,没有物稀为贵之身价。但在母亲精心调配下,它们的完美组合不光是充饥的美食,也是延续农耕饮食文化的力作。哪像现在的早点,虽然品种繁多,张嘴就让人生厌。
它的独到之处当在它的原始的、繁琐的制作过程中。
米是籼米、粳米皆可。先把米在清水里浸三、五时辰,淘干净,淋去水,在石臼(也称石凼)里用石锤压碎。石臼,是二尺见方的麻石,从一方镂空,镂空的底是椭圆形,口呈方形。底小口大,可装十多斤斤谷物。石锤一头圆形球状,另一头方形,有一方形榫眼,插进手握粗的木棍,称石臼锤。把米放入石臼,手握石锤柄,举起石锤向盛米的石臼用力砸下,一下,一下……米成齑粉。再用纱筛(筛眼只有针尖粗)筛下,筛下的粉末方称米粉。大一点的粉粒倒入石臼,继续操作……
“田家秋作苦,邻女夜舂寒。”这是李白夜宿五松山下看到的舂米图,听到的舂米声。那是把稻碾成米的舂米声,是凄凉的,是悲苦的。
又是一个千年,我的乡村父老为了过年,为了过年的欢欢喜喜、团团圆圆,在村口的石臼旁,用我们祖先最先进又最原始的方法把米碾成米粉,烹煮美食——米粉粑、萝卜圆子。抡起石锤的是男人,他蹲的马步,手抓石锤柄,双臂用力是耍棍的拳术,把东乡武术的门道与日常的农事结合得天衣无缝。十几斤的石锤变成几十斤的重力落在石臼里,一下,一下,轻松,欢快。筛粉的是女人,一手紧扣筛箩圈,轻扭手腕,360度旋转,另一只手指轻敲筛箩圈,不紧不慢,不急不躁……月光下或是太阳下,雪白的米粉相衬着红扑扑的脸颊,是那么闲适自然,那么和谐和气。
米粉娇气得很,要细心呵护。紧接着要晒干,要炒熟。炒米粉时小火慢摇。用草把烧,火势强弱易于掌控。锅铲在锅里翻拌米粉速度要快要匀,不能让米粉粘锅而焦黑。米粉炒至微黄即可,如我母亲说的半生不熟的就是上乘。米粉粑、萝卜圆子的好吃,不粘牙、细腻柔软,大概就在炒粉的技艺上。
原汁原味的食物当是传统的原始的手工制作而无需五花八门的佐料,这米粉粑、萝卜圆子即是。记得母亲把适量米粉、萝卜籽倒入木盆,撒上切碎的大蒜叶,放盐兑冷水,搅拌,干湿有度,不沾不粘。抓一粉疙瘩在手,用手指把粉疙瘩向一起拢捏,再用双掌心快速旋转,乒乓球般大小的萝卜圆子就端端正正地摆放在竹筛里了。白呈微黄,一二瓣青绿的蒜叶点缀其上,看着,是一副憨厚敦实的模样,怎不让人喜欢?
米粉粑身价要昂贵得多。它是将萝卜籽、豆干、大蒜放油炒熟做馅,若是再加廋肉则是富得流油了。米粉也用冷水调和,把粉疙瘩团成球状,后捏成碗形,装入其馅,拢捏封口,双手心旋转成圆球,再双手轻压轻拍。米粉粑——五指可罩,园心微鼓,周边如刀锋,其馅不露,那技艺可谓是炉火纯青。儿时一粑在手,焐着,那热量传身,就觉得通身舒畅。
蒸粑也有门道。先把铁锅烧红,在铁锅周围浇一点香油,把粑从锅心放起,有序排列至锅沿,然后把萝卜圆子倒在上面,按上锅盖。大火旺烧,当锅内冒出哧哧声,用水瓢从锅沿旋转一周浇水,用毛巾覆盖在锅沿周围,以防热量散发。大火,小火,焖。掌控火势,以贴锅的米粉粑不焦黑为顶上功夫。
蒸熟的米粉粑、萝卜圆子放在纱布垫好的竹篮里,吊在堂心屋梁下的铁钩上。油炸类的鱼圆子、肉圆子也放在上面,胜似现在的冰箱,可储存一个正月。要吃,随取随烧,很是方便。那时,小孩子嘴馋,望着竹篮里的萝卜圆子,如小猫盯着腌晒的鱼肉怎想弄一点吃吃,趁着大人不在家,偷吃萝卜圆子的事时有发生。隔壁的小巴货就是在凳子上架凳子,偷拿竹篮里的萝卜圆子,不慎倒地,摔断了腿。虽然及时医治,但还是留下微残,走路一拐一拐的,人们由“枞阳大萝卜”而戏称他“萝卜腿”。现在说起,还为那时过年贪吃的趣闻轶事而忍俊不禁。
作者:章乐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