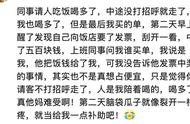时光速走,放假了,回妈妈家住几天,这个我成长的地方,阳光热烈,草木新鲜。周边新修了柏油马路一些老旧的楼房已经不见踪影,矗立起高楼,焕发了新的生机,但那条巷子依旧,还透着朴素和宁静,巷子尽头,是一片青砖黛瓦,那个以前晒谷子的空地依旧被打扫的干干净净,几株不知名的草在这扎了根之后就在这摇它的叶子,晒场上支起了几个架子,晒着邻居婶婶种的李子,婶婶还耐心的把李子去了核,到时候用冰糖一熬煮,那味道酸甜可口回味无穷。
场院的东南角有一颗枣树,是梁伯栽下的,有些年头了,虽然枝干不怎么粗壮,但依然不影响它年年枝繁叶茂。每年这个时候,这棵枣树都是这个场院里最引人注目的存在。密匝匝的枣儿挂满枝头,把枝压得很低,稍高一点的孩子只需踮起脚就能摘满一口袋,一群更小的孩子早就跟在他屁股后面想要分得哪怕一颗枣,分到了枣已经顾不上洗直接就身上擦了擦一口吃到嘴里,把父母说的刚摘下的晒热的枣吃了是要拉肚子的告诫全然忘了,哪怕这个时候这枣还没有熟透,但它依然是孩子们日日的期盼和等待。终于,一轮更毒的太阳过后,又一阵猛烈的风过后,枣已经熟透了,红的像颗颗宝石,有些啪啪的落在地上了,梁伯就招呼大家来摘枣了,于是孩子们开心了,场院里的叔伯婶子拿了筛子或舀水的勺子或小脸盆都摘了些回去。这枣脆甜脆甜的,极大满足了大家对这个夏天的期望与认可。
梁伯照例把剩下的枣摘下平铺在竹篾上,晒它几天就变成了红枣干,熬汤放几颗,平时抓一把放在兜里就当零食了,既有营养又甜糯好吃。
但是今年,不知道是怎么了,已经到了这吃枣子的时候啊,依旧密匝匝的枝头挂满了枣,可就是固执的青涩着,不见红不见熟,这群孩子依旧在树下打了几天转,没尝到甜的他们显出失望和不可思议的神色之后决定放弃了。
大人们说再等等吧,估计今年雨水太多了,估计今年要熟的晚些……
一天夜里,我分明听到了枣儿落地的声音,我知道,第二天一定是热闹美好的一天。
在这个小城这条小巷成长的我即使后来常常要与它告别,但只要回到这里,依旧是扑面而来的熟悉与亲切。
还很早,太阳才刚爬过这小巷不高的围墙和这里不高的屋顶,场院里撒下一片柔和的光,母亲拿着竹扫把扫场院的沙沙声让我觉得这世界如此温柔美好。母亲早起总是要先把场院清扫一遍,没有一天落下了,即使下雨天,她依然要穿着雨衣把积水扫到沟里。有时扫下来,她的衣服都被汗浸湿了,我们劝说她何必天天扫,她说大家都要往这走,住在这块,扫干净总是更好的。那年母亲摔断了腿,扫不了,也不忘把家里人叫起来替她去打扫,贪睡的我们总是极不情愿的起来,嘴里还要嘟囔几句:天天扫也没谁颁奖给你…母亲也不多说,只是督促我们打扫完,后来,我越来越能理解母亲的做法。一大早扫尘一整天清爽。
夏天的太阳总是亮的很早,太阳已挤满了场院每一个角落。也叩开了每户的大门,兰英嫂子吆喝着她的一双儿女起床的声音钻进了耳朵:还不要起来吃,面都要糊了,再不起,我就倒了,让你们饿着…
老九哥端着个大碗的面蹲在门前大口地吃起来,还不忘咒骂这该死的天气:热的简直没法活了…很快老九哥吃完就拎着家伙什与太阳对抗去了,似乎每一个拼命谋生的人都不舍得在早上悠闲的吃口早饭,生怕耽误了一下就少赚了很多钱,就对不起老婆和孩子了,带着一家子的希望和期盼匆匆地出门了。
兰英嫂子的儿子,我们都叫他小九九,因为长的和他的父亲老九一模一样,干瘦,连秉性都一样,兰英嫂子这样说的,这父子俩是一样的德性,经常让人生气。这不,小九九已经喊起来了:又是面条,天天吃这个,腻了,要去外面吃,拿钱。这话利索的俨然是个少爷,也的确是少爷,老九兰英夫妻拿这个儿子是没有办法的,宠的很,穿的用的都是好的,儿子就是命根子已经深深刻在这对夫妻的骨子里,以至于他们一直用自己的方式宠爱这个儿子。即使他们也明白小九九的骄横却一点办法也没有。兰英嫂子照例拿个扫帚作势要打这个不知心疼父母赚钱不易的儿子,但扫帚哪舍得落下去,小九九已骑着他爸花巨资给他买的自行车风一般卷出巷子了。
这时,兰英嫂子的女儿小月已经吃完收拾好碗筷进房学习了,小月是姐姐,总是安安静静的样子,却极会读书,考入了县城的重点高中的重点班,这在老九哥家是件极荣耀的事情,他觉得像他和妻子这样才小学毕业了的人生出的小孩这么能读书一定是他们上辈子积了德。所以,小月考上了高中以后,他们停止了对她的使唤,只管让小月专心读书,以后好光宗耀祖,甚至为了接送小月上下晚自习,老九哥买了辆车子,每次说起这个女儿也总是露出吃再多苦都值得的表情。他们也知晓,在这个时代,读书才是出路,只有读到了书,才不会像他们一样靠力气吃饭,活的这么辛苦。于是为女儿骄傲完的老九哥又为儿子不好好学习发起愁来…
一会,摩托车嘟嘟嘟出了巷子,那是建国哥去上班了,他的这辆摩托车经常会发出拖拉机一般的声音,像是有一团草堵在了喉咙,冒了一团黑烟以后才不情不愿地往前挪去,一副罢工不成的样子,场院的人都从安全的角度劝过建国哥把这车换了,可建国哥却依然对这个家伙不离不弃的还经常清洗,像是对一个老朋友。
接着,建国哥的媳妇康康妈提着袋子准备去买菜了,穿的依然是碎花裙子,一点点风就让这裙摆形成一个好看的弧形。康康妈妈是个嗓门极大,极热情极勤劳的女人。对谁都是笑盈盈的,她屋子的地理位置极大地给她的勤劳提供了场地,在场院的一角要下几层楼梯,是一块平地,旁边一栋两层楼的房子是建国哥的家,平地中央原来是一口井。我对这口井印象是深刻且清晰的,这口深邃的井窥见过我们小时候太多的欢乐与忧伤。
我记得小时候,大人们总是在这口井边洗衣服,一个桶上吊一根绳,把桶丢进井里,手抓紧绳子,靠着手腕的力气左右甩一下,桶就斜下去盛满了水,再把桶提上来,这冰凉沁人的井水就在大家的指尖流淌了,洗菜,洗衣服---夏天把田里摘回的西瓜往井水里一泡,只需一会,切开的瓜就透着一股冰爽,一口下去,说不出的惬意。
有时候井里落下四五个桶,绳子扭绞在一起,我们这些小孩瞬间来了精神,都趴在井口,眼睛死死盯着井里的几股绳,巴不得自家妈妈手里的绳能打败其他的绳,率先打上一桶井水,那得意自是不必说的。后来九八年一场洪水,彻底把这口井毁了,再后来,建国哥用一块水泥板把井口盖上,这上面就成了康康妈大展拳脚的场地了,她在上面摆满了盆盆罐罐,种上了香葱香蒜,种上了辣椒,青菜,围着井边种上了花花草草,还有薄荷呢,微风一过,就飘来阵阵清新。
前一阵,估计吹空调的缘故,喉咙干痛,母亲去井边摘回一些薄荷给我泡水喝,隔天,康康妈就拿来一大袋晾晒好的薄荷,说这晒好的薄荷泡水更不伤胃,嗓门依旧很大,话语还带着薄荷的清香。
到了傍晚,太阳还不肯收起它的威力,整个场院还是亮堂堂的,只有那颗密实的枣树下漏着几点光,留下的是一片浓荫,几个小孩聚在一起不知在聊着什么,手里似拿着卡片,低着头急切地发表着自己的见解,不时还要配上手的动作,漏出黝黑的手臂和一截黝黑的脖颈。家家户户应该在做饭了,兰英嫂子家在炒辣椒,辣味冒出来,直呛喉咙,胖婶家在烧肉,在这大热天,涌出一股肥腻感。让本来被大热天偷走的胃口更是消失得无影无踪。
很快,吆喝吃饭的声音又穿过巷子散到远方了,小九九依旧投入地讨论着手里的卡片,对兰英嫂的吆喝充耳不闻,兰英嫂骂起来了------老九哥回来了,带着一股风尘仆仆的热气,端了碗就端在门边吃起来,“手也不用洗就吃饭,一身的汗,鞋子脱了也不放好,臭的死,你家儿子饭也不吃,你也不说一下,没一个让人省心的”,兰英嫂机关枪一样数落老九哥各种让她瞧不上眼嫌弃的不好的德行,老九哥不时争辩几句,但在兰英嫂更尖利的声音下,立刻弱弱的偃旗息鼓。胖婶和胖伯端着他们的大海碗也坐在门前吃起饭来,依旧是大碗米饭,大块肉配着青菜,他们吃的津津有味,我突然知道了他们身体硬朗的原因了,那就是永远不辜负每一粒粮食,永远保持对生活最朴素的热爱。很快,康康妈也端着碗过来了,照例要去瞧瞧兰英嫂子吃什么菜,照例叫兰英嫂尝尝自己碗里的菜,大家一起急切地向别人诉说一天的喜气和怨气,还不忘咒骂这蒸腾的热气。声音抑扬顿挫,极有穿透力。
这时,胖伯对着巷口一声吆喝,一丝风从巷口钻来,我突然想起小时候割稻子,风似乎凝结在蓝天白云里了,咸咸的汗水浸痛了眼睛,那时,父亲就对着远方一声吆喝,立即就有一丝风恰到好处的让我们固执的继续埋头在田间----
我感动于这里的人们的热情,又佩服他们在生活中积累的智慧。
转眼,父母都老了。这条巷子也老了,但它却时时年轻着,时时涌动着鲜活的生命的气息,永远传递着生活的美好与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