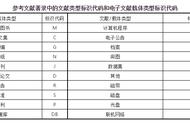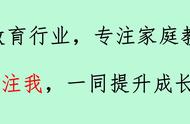“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野鸡闷头钻,怎么上天王山?”“满地都是米,唔呀有根底。”“拜见过阿妈了吗?”“他房上没有瓦,非否非,否非否。”……
这些曾经只在东北深山老林土匪中秘密流传的黑话,随着当年曲波《林海雪原》被改编成样板戏《智取威虎山》而走红于中国大地,成为几代人口中的经典对白。随着历史的变迁,新生代的80、90后对这些曾经的“流行语”早已生疏。还得感谢香港的徐老怪,新版《智取威虎山》在圣诞期间的热映,不仅勾起了几代人的回忆,更让新生代们了解并关注曾经的经典。仅凭这一点,新版《智取威虎山》便功不可没。
对新版《智取威虎山》的肯定之词已经很多,这里不再赶时髦,只借这个话题,谈谈过去土匪们的江湖黑话,也就是江湖人口中的“春典”。
为什么要有黑话
江湖黑话,即春典,也叫“山音”,“切口”或“怯口”。(无限福利:《鬼吹灯》作者天下霸唱在他的小说中将黑话写作“唇典”。)
我们知道,真实的江湖,是一个边缘、底层的社会,其大多数成员,都或多或少涉及非法勾当。在这样的情况下,成员之间彼此的信任是非常难以建立起来的。但同时,江湖人又大多贫困边缘,而且行走四方,迫切需要来自外界的帮助。一口流利的春典,江湖黑话叫“满春满典”,不仅表明你是“自己人”,有助于赢得江湖同道的信任——《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上山之后立刻和土匪对春典、讲黑话即是此意——更是一个人江湖地位的象征。
一些春典,只有江湖中有一定地位的人才可以讲,只有老江湖才会,初出茅庐的人学不到,也没资格讲。比如《智取威虎山》中的“脸红什么”这样的问话,只有座山雕这样的大土匪头子可以讲,下面的小喽啰没资格这么问的。
用今日的概念,黑话,是江湖人中的一套完整而复杂的认证体系,掌握了黑话也就是春典,才能够成为职业的江湖人士。所以过去江湖人对春典非常重视,除非非常信任的徒弟、亲人,绝不轻易传授春典。
英雄好汉们在闯荡江湖之前,都要专门和师父学习春典,所以有有“宁给十万钱,不把艺来传;宁给一两金,不给一句春”的说法。
黑话不好学
春典不仅仅是一个个孤立的语句,概念,说春典时的语气、节奏、态度等等都很重要,稍有错误便容易被老江湖发现,露出马脚。所以伪装江湖人不是背诵几句春典就可以,还要模仿得惟妙惟肖。历史上的杨子荣之所以成为传奇英雄,就在于成功模仿了土匪的黑话而且取得了土匪的信任,这非常不容易。
有一部传统评书叫《永庆升平》,非常精彩,如今已经失传。其实故事的本子很完整,今天还在,但是其中的“书道儿”,今天的艺人表演不出来。比如,其中有许多江湖人士讲春典的段落,今天的说书人很难模仿出那股江湖气。比如这几句:
“合字儿,掉瓢儿,招路把合,龙宫道漂遥儿赤字,居米子海。脑儿塞拈青字,浑天汪攒架漂遥儿,摘赤字的瓢儿肘,居米急付流儿撒活。”
现存的文本中,这几句断句和字有许多错误,笔者在此更正了一下。
这几句话的意思是:
朋友(合字儿),回头(掉瓢儿),仔细看(招路把合),水面(龙宫道儿)船上(漂遥儿)有官员(赤字儿),银子多(居米子海),头说(脑儿塞)带着家伙(拈青字),夜里三更(浑天汪攒)上船(攒架漂遥儿),砍了当官的脑袋(瓢儿肘),大家把银子分了再跑(居米急付流儿撒活)。
想伪装成绑匪,仅背诵下来这几句话是不行的,说话时的语气、节奏都很重要。老评书艺人中不少人精于此道,但今天的人再去学习这些就很困难。
同时,黑话中许多的概念非常接近,必须老江湖才能辨析出来。比如合字儿、排琴、并肩子,都是黑话中“兄弟”的意思——江湖人极少如电影中的国军那样称呼“弟兄们”——但含义有细微的差别。并肩子,一般是关系特别熟稔才这么称呼。合字儿则一般是同行之间表示亲密,拉关系的说法。比如评书里常见,某大侠路遇劫匪,上前答礼:“咱们都是合字儿,人不亲艺亲,艺不亲祖师爷亲。”排琴则是一种尊称,对不熟悉的人表示恭敬,礼让。
就以响马而言,真实的江湖好汉进山入伙,上山后当然不会有新版《智取威虎山》中那样防守严密的混凝土建筑,也不会有评书中经常提到的聚义厅、招贤楼,多是个破庙烂草房子之类的地方。响马的人不会多,几十个人算大股,一般有一个为首的叫“大掌盘子”——现在有人写小说写作“掌穴儿的”,不对,这是曲艺行的用法,绿林响马必须叫“掌盘子”——大掌盘子下面有头驾、二驾。进去后要行礼拜见,这时候一般这么说:“西北悬天一片云,乌鸦落进凤凰群,不知哪里君来哪里臣,一揖到底拜排琴”。这个时候排琴,是对坐上诸位恭敬的说法。
说过这话之后,一般二驾会站起来。如果二驾说的是“西北悬天一枝花,天下绿林是一家”,表示欢迎加入,下面就是见掌盘子,拜兄弟论交椅;如果二驾说“一龙生九子,子子有不同”,这一般是挑战,至少要露点功夫才能进山门。
同行见面有暗号
过去江湖中不同行业,其黑话也就是春典是不同的。而且,不同地域的春典也不相同。有南春北典的说法,南方江湖人说的叫“春”,北方江湖人说的叫“典”。
今天人们知道的春典,多从评书、相声等曲艺作品里面得来。传统评书、相声艺人也是江湖人士,对春典比较熟悉,能够惟妙惟肖地加以模仿。但是,受到知识和地域的限制,艺人们对春典的掌握也只能是有限的。比如老北京话有句“戏果儿”,是指调戏大姑娘的意思。管大姑娘叫“果儿”是曲艺界的说法,江湖好汉叫“姜斗儿”,武林好汉叫“斗花儿”,绿林响马的说法最有意思,叫铃铛。这个说法据说是因为做买卖——即抢劫——时最忌讳遇见未婚女性,很不吉利。这种情况叫“踩了铃铛”。
许多传统评书艺人都能比较好地模仿江湖黑话,但评书是北方艺术,在讲述其他地区的故事时,这种模仿常常会有问题,比如评书《济公传》,讲述的是南宋江浙一带的故事,但是里面“捉拿华云龙”一大段,在评书艺人的口中,江南好汉常常一口北方春典。比如华云龙和雷鸣去酒楼那一段,华云龙对雷鸣说:“合字儿,撒啃窑儿,窥着翅子窑儿的鹰爪孙。”估计会让当时的南方听众觉得不伦不类。
在传统的武术界——过去无武术的说法,这本身就是一个新的概念——一些固定的说法、礼节,也属于广义的黑话。比如武林朋友见面,不能轻易问对方的师承、门派,如果问了,对方答不上来还好,答上来,必须管吃管住,临走送盘缠,否则会引起对方极大的不满,要动手解决的。
武师见面必先抱拳道辛苦,所谓“见面道辛苦,必定是江湖”。抱拳道了辛苦,对方通常会问一句话:“您家里哥几个呀?”这其实也是黑话,意思是打听对方做哪一行。过去武林中分有三正行。开馆收徒弟吃徒弟的孝敬,这叫“支点”,是“老大”。如果您是教拳的拳师,就得得说“家里老大,坐山守海”。镖局里面的镖师,趟子手,有钱人家的教师爷,看家护院,这叫“拉点”,也叫“老二”,干这个的得说“排行第二,看宅守院,外吃一线”。走江湖打把式卖艺的,叫“戳点”,也叫“老三”。干这个得说“老三不成器,走方君子地”。绿林响马不入这几行,叫“看山守业,吃家里饭的”。
黑话白话能说的就是好话
江湖黑话流传广远,对今日的语言有很深的影响。今日许多常用的概念,都来源于黑话,比如“单位”,“大腕儿”、“火了”等等。解放前北方人称妓院为“窑子”似乎也和春典有关。妓院黑话叫库果窑,此外饭馆叫啃窑,茶馆叫淋窑,旅店叫流水窑,澡堂子叫水窑。去什么地方叫撒,撒啃窑、撒淋窑就是去饭馆、茶馆。卖什么叫挑,挑粒粒是卖假药,挑转子是卖假表,挑老烤是卖假虎骨。住在哪,呆在哪都叫迫(pai,三声),迫轮子是坐车,迫漂遥儿是坐船,住店叫迫流水窑儿。说什么都叫念,比如念山音是说黑话,但念啃是“没吃的”的意思,“念嘬”是说人长得丑。念在春典中常常有否定的含义,大概是从“只动口不动手”引申出来的吧。下、掉叫摆,撒尿叫摆柳儿,下雨叫摆金,哭、流眼泪叫摆苏。修理、收拾什么都叫扫,扫蹄儿是修脚,扫苗是剃头,但是扫腕儿是指下等妓女。
香港电影界更是渗透了不少江湖语言,现在看当年邵氏的武打片就能看到非常完整的南方江湖切口对答,细致程度不亚于《智取威虎山》。至于广东话现在常见的属于“拖马”(集合兄弟去打架)、踢窦(端老窝)、散水(赶紧四散跑)、着草(逃跑)等,都是原来的江湖黑话。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黑话的存在并非中国独有,在其他国家也屡见不鲜。比如英国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伦敦东区也是黑帮盛行之地,当地底层民众之间通行的语言,经常让西区的中产阶级听不懂,这其实也属于英式黑话。即使现在,美国的部分黑人聚居区也存在类似黑话的现象,这在许多好莱坞影视作品中都有反应。
但是,总体而言,黑话在今日社会中是趋于衰落和灭亡的。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使得社会边缘群体的数量总体在减少。同时,通讯技术手段的发达和信息传播速度的加快,使得任何群体中的文化现象很容易被全社会所观察到,因此很难形成那种高度保密的一整套完善的话语系统。同时,即使在犯罪分子当中,借助发达的资讯,彼此身份的认证也不再需要黑话这样古老的手段。因此,传统意义上的江湖黑话是在不断消亡之中的,只有在少数文艺作品中,还能看到它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