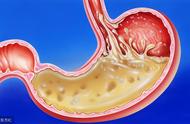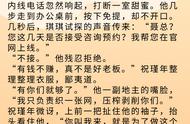《随园食单——不负好食光》,袁枚/著 许汝纮/编注 曹云淇/绘,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20年7月版。
无论从烹饪还是品鉴的角度来看,中国都担当得起“美食自信”四个字。
一百年前,孙中山在欧风美雨大行其道的艰苦岁月中依然能够在《建国方略》中自信满满地书写下“我中国近代文明进化,事事皆落人之后,惟饮食一道之进步,至今尚为文明各国所不及”这一豪言壮语;一百年后,大众视界里也依然时不时便会冒出一部如《舌尖上的中国》《风味人间》《人生一串》一般横扫各大流媒体平台的美食纪录片。而放眼世界,不用提美国各大城市隐隐有与肯德基、麦当劳叫板的熊猫快餐和假借了孔子威名便风靡西方的“fortune cookie”(幸运饼干),便是公认的“世界三大烹饪王国”之一的头衔和坊间中国留学生们用一道菜征服一个校园的传说,便足以将中国美食推向“神坛”。
中国美食的“出挑”似乎理所当然,毕竟五千年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给了中国美食最佳的载体。然而历史真相往往令人感到意外。中国美食文化其实异常“晚熟”:南食、北食直到唐宋时期才逐渐分野,“四大菜系”直到清初才成型,“八大菜系”登场时,中国封建时代已经走向了尾声。大多数传统面点小吃的起源都在唐宋之后(如春卷、烧麦),不少为人所熟知的菜式甚至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才诞生(如大盘鸡、螺蛳粉),街头巷尾老字号餐馆里动辄上溯千余年、勾连起秦皇汉武诸葛亮等名人的宣传文案,只合当茶余饭后的谈资一笑置之,切不可当真了。
如果将中国饮食的发展历程想像成一个函数,那它的曲线图绝不是平缓上升型,而是经历过一段笔直的上升期;如果要在这个上升期里寻找三个关键词,那将毫无意外的会是:清代、袁枚与《随园食单》。

食物史:千年食材汇清代
关于美食,中国有两句家喻户晓的名言:一是《论语》中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二是《史记》中的“民以食为天”。在大众视野里,这两句话似乎最能代表中国的“美食自信”:前者表达了中国人对饮食的极致追求,后者则说明了中国人对食物的无比重视——然而这种“美食自信”,多多少少算是一种误读。
孔子所言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其实更侧重于祭祀时饮食的态度而非对味道的追求。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烹饪、碓舂、切肉工艺均相对原始,将“食”做“精”、“脍”做“细”,体现了厨人与食者严肃真诚的态度。与此相对,孔子针对口腹之欲多有“君子食无求饱”的论断,追求食物的奢华精细,本身便与孔子的理念背道而驰。
孔子的饮食观背后,是其心怀的礼制。其实中国人与食物最早的联结不是味道,而是礼仪。《礼记》所言“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大意即是“礼仪制度和风俗习惯始于饮食礼”;而据《周礼》所载,周王室四千多名治官中一半以上的职责与饮食相关,细品之余不难发现上古食物与生俱来的森严与拘谨。
而司马迁所引的“民以食为天”,指的也不是百姓对食物的盲目热情,而是传统农耕社会生存压力的写照。作为农业古国,中国较之其他文明更早出现了人口生态压力,这一压力在缔造了灵渠、都江堰、大运河等奇迹的同时,也极大激发了中国人对食材的想象力。林语堂在《中国文化精神》中提及中国人“吃遍了整个生物界”,这背后的血与泪实在一言难尽。
所以,中国人的美食文化并非天然通向“味道至上”。先秦以降,中国饮食与养生、医疗结合得更为紧密,两汉时期谶纬之学与仙道之风盛行,饮食养生的风气远较宴席间的觥筹交错更吸引士大夫阶层。与此同时,在张骞通西域之前中原地区的食材尚相对单一,两千年之后中国菜系百家争鸣的盛况,还需要漫长的孕育。
张骞凿空打响了汉胡饮食交流的“第一枪”,大约在南北朝时期,胡椒随着连年战火传入中原,乳酪、羊肉等食物也逐渐在汉人的食谱中亮相。隋唐时期,中原王朝盛极一时,葡萄酒酿法、熬糖法、胡饼制法及以菠菜为代表的胡食大量传入,这些新事物令中国朝宴的水准和丰富程度为之一变,也为两宋时期南食、北食的分野奠定了基础。宋代《东京梦华录》《梦梁录》《武林旧事》等笔记中的面食点心种类繁多,若无饆饠(亦写作“毕罗”,一种包有馅心的面制点心——编者注)、搭纳、音部斗(一种油煎饼——编者注)这些胡食“助力”是不可想象的。
元明清三代除了饮食的汉胡交融外,海外食材也逐渐引入,辣椒、玉米、甘薯、马铃薯、西红柿、豆角等日后中国菜肴中不可或缺的元素都在这一期间登陆。17至18世纪,海内外食材万川集海,各地烹饪技艺逐渐成熟并体系化,最终形成了“四大菜系”——中国“美食王国”的名头,终于可以从“礼仪之邦”四个字里独立出来。
21世纪的中国人如何能想像没有辣椒的川菜?如何能接受没有香菜、小葱当佐料的面与粉?又有谁没受过拍黄瓜、番茄炒蛋、鱼香茄子这些“百家菜”的滋养?言及于此,可以发现中国美食文化其实异常“晚熟”,三代以降数千年时光仿佛是一场漫长的蛰伏,为的只是在清代迎来了食物界的“寒武纪大爆发”。

袁枚
食客史:一生知味数袁枚
古代中国对食物的“淡漠”不仅出于食材的缓慢积累、交融,更在于儒家文化对口腹之欲的“打压”。一方面,孔子“君子谋道不谋食”的教诲让士大夫阶层往往远离庖厨而以修齐治平为己任;另一方面,自汉武帝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士大夫阶层仕途通畅,“学而优则仕”也有着丰富的现实回报。至晚在唐代之前,文人对于饮食之事是少有重视的。
隋唐时期饮食文化尤其是宴席之风虽有较大发展,但在盛世文治武功的影响下,士大夫阶层的追求依然在“提笔安天下、马上定乾坤”之中,“烹羊宰牛”式的盛筵并没有孕育出与之相当的饮食文化。
转折来自于两宋:从个人角度来看,两宋文化昌盛导致读书人与日俱增以至于仕途门槛抬高,同时武功疲弱又令多少人雄志难酬。从朝廷角度来看,宋室有鉴于唐朝藩镇割据之痛,自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始便鼓励朝臣“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之业,多致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用舍行藏之下,也不由得士大夫们不将视线转向饮食了。北宋苏轼以嗜美食闻名,而其半生谪居的仕途,多多少少也体现了当时的饮食与儒家传统追求此消彼长的关系。
元朝统一后,汉族士人愈加边缘化。明清易代,朝廷中枢又多为满族垄断,“学而优则仕”的路途不再畅通无阻,文人的兴趣自然而然愈加转向犬马声色。张岱在其《自为墓志铭》中明言自己“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其实这也未尝不是当时文人集体的众生相。
特殊的时代背景使得“饮食之人”不再被轻贱,于是一大批美食家在清代前半叶应运而生,而其中最为杰出的,非袁枚莫属。袁枚少有才名,23岁中进士,次年选庶吉士,随后历任沐阳、江宁等地知县,在此期间结识了“贵人”与“食友”两江总督尹继善。不过,袁枚在34岁父亲去世后便决意辞官,于江宁小仓山购园置业,并将其改造为“大江南北富贵家所未有”的随园。
袁枚盛年隐居在时人眼中未必是最理性的选择,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从这一刻起,时代风潮与人生抉择将在随园这一方小天地里水乳交融,为他成为一名旷古烁今的美食家做好一切准备。
随园所处的江宁,是当时江南第一大都会,物阜民丰,饮食之风在盛世滋润下倾向铺张。当时袁枚非凡的诗才已经名满天下,以至于“上自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负贩,皆知贵重之,海外琉球有来求其书者”,因远游访友时往往“所至延为上宾”,得以遍尝珍馐佳肴。袁枚好学,遇到美醪奇馔常常会询问烹饪之法,甚至不耻于拜师学艺,由此又搜罗了不少烹技食材。购置随园后,袁枚苦心经营,招募王小余等名厨,得以将各路菜式付诸实践并加以创新。诗文、美食、士人一一交汇,随园很快成为当时文人*客、达官显宦们宴集的首选,平日里客不虚门,大兴宴会时更是“随园一夜斗灯光,天上星河地上忙”。名噪一时的随园菜也就在钟鸣鼎食中成型了。
“不在寻常食谱中”的菜式只能成就随园菜,但还不能将袁枚推向“食圣”的神坛。真正成就袁枚的,是其源于美食又高于美食的饮食思想。袁枚在《与薛寿鱼书》提出“夫所谓不朽者,非必周、孔而后不朽也。羿之射,秋之奕,俞跗之医,皆可以不朽也”,而他自己则将饮食之道视为堪与周公孔子之为相媲美的事业,因此可以毫无顾忌地“每食于某氏而饱,必使家厨往彼灶觚,执弟子之礼”。
能为口腹之欲正名,更能为饮食之道指路。袁枚作诗以“性灵说”为主张,认为诗直抒心灵,表达真意,这一主张也融合到了饮食中:他认为在烹饪之前要了解食材、尊重物性,注意食材间的搭配和时间把握;他反对铺张浪费,提出“肴佳原不在钱多”,食材之美更在于物尽其用;他将人文主义引入饮食,宣扬“物为人用,使之死可也,使之求死不得不可也”;他强调烹饪理论的重要性,以为中国烹法完全依厨人经验不利于传承,故煞费苦心撰写《随园食单》,以求为后世食客厨人树立典范……
袁枚在《所好轩记》的自述中将“好味”置于诸所好之首,这是个人之任性,又何尝不是时代之荣幸。
食经史:百代食单问随园
千年饮食爆发于清代,清代食客折腰于袁枚,那袁枚的食单又收束于何处呢?答案是《随园食单》。
在几百年后各色食谱泛滥的时代里看《随园食单》,往往会觉得它过于简单:两篇“总则”(须知单、戒单)再加十二篇“分则”(海鲜单、特牲单、点心单等),326道菜式的篇幅似乎难以支撑起中国美食大厦。的确,《随园食单》的伟大只有放在中国食单发展史里才能洞悉。
传统儒家思想不允许士人们在物质层面投入太多心力,因此也抑制了饮食专著的创作。汉代以前,饮食典籍均附属于其他著作,直到三国时期曹操编撰的《四时食制》才作为第一部独立饮食著作问世。从现存的残篇来看,《四时食制》仅记载了食材的名称、特色、产地等,距真正的食单还相距甚远。
南北朝时,北魏崔浩《食经》中已涉及食物储藏与部分菜品的制作,虞悰《食珍录》则记录了魏晋以降不少烹饪名品,其中部分菜品亦有制法,但简略到难以操作,如“浑羊设最为珍要,置鹅于羊中,内实粳肉五味,全熟之”。隋唐时期随着饮食文化的发展,已经有一定综合性的食经问世,但涉及到菜品部分几乎为“报菜名”,如谢讽《食经》中诸如“无忧腊”“龙须炙”“浮萍面”等,后人难以反推其烹饪技法。著名的《烧尾宴食单》中对所列菜品有简注,《膳夫经手录》甚至还加入了部分典故,但内容依然单薄,不堪后人援引。
两宋之后雕板印刷技术发展迅速,饮食著述较前朝大量增加,尤其郑樵在《通志·艺文略》中已经将“食经”单独分类,体现了饮食文化在士大夫眼中地位的提升。不过,这些饮食著述同样失之简略,如现存的《膳夫录》《玉食批》《本心斋疏食谱》均仅一卷,《山家清供》虽有两卷百余种菜品,但其原料局限于鸡、兔、鹿、鱼等,范围十分有限。第一部实用性较强的食单要数元朝吴氏《中馈录》,全书六千余字,分门别类收录菜品七十余条,烹饪方法也较为明晰,如“糖醋茄”:“取新嫩茄,切三角块,沸汤漉过,布包,榨干。盐腌一宿,晒干,用姜丝、紫苏拌匀。煎滚糖醋泼浸,收磁器内。”《中馈录》之后,明代《易牙遗意》《宋氏养生部》的体系性已愈加明显,如《宋氏养生部》第二卷分为面食、粉食、蓼花、白糖、蜜煎、糖剂、汤水七制,编排已非常规整。

《中馈录》
从《四时食制》到《宋氏养生部》,中国饮食专著的发展历经千年,但始终没有在理论层面开花结果。清代饮食产业蓬勃发展,士大夫阶层对饮食日益重视,最终在《随园食单》完成了饮食文化从经验向理论的最终蜕变。
《随园食单》序后以“须知单”“戒单”开篇,其中涉及物性、作料、洗刷、调剂、搭配、火候、器具、上菜等方方面面,如“洗刷须知”中的“肉有筋瓣,剔之则酥;鸭有肾臊,削之则净”,“配搭须知”中的“可荤可素者,蘑菇、鲜笋、冬瓜是也。可荤不可素者,葱韭、茴香、新蒜是也”,“上菜须知”中的“盐者宜先,淡者宜后;浓者宜先,薄者宜后”,都是对中国千年烹饪经验一次开创性的总结与编排。而其中又有创新之处,如“先天须知”中认为“大抵一席佳肴,司厨之功居其六,买办之功居其四”,“戒单”中将矛头指向各种形式的铺张浪费等,对饮食实践又极有指导意义。
“须知单”“戒单”之后,《随园食单》以食材将326种菜品分为十四单,分类精细到要区分海鲜与江鲜、特牲与杂牲、水族有鳞与水族无鳞。而在此基础上,菜品均详细记载了食材用料、烹饪制法、注意事项,如“汤煨甲鱼”条载“将甲鱼白煮,去骨拆碎,用鸡汤、秋油、酒煨汤二碗,收至一碗,起锅,用葱、椒、姜末糁之。吴竹屿制之最佳。微用纤,才得汤腻”。“纤”即“芡”,这一条“贴士”,不知方便了多少庖丁厨娘了。
除饮食理论与烹饪技法这些“基本盘”外,部分菜品甚至记载了轶事典故与风味点评,如“鹿尾”条载“尹文端公品味,以鹿尾为第一。然南方人不能常得从北京来者,又苦不鲜新。余尝得极大者,用菜叶包而蒸之,味果不同。其最佳处的尾上一道浆耳”。又如“程立万豆腐”中又有“惜其时余以妹丧急归,不及向程求方。程逾年亡。至今悔之。仍存其名,以俟再访”的叹惋之情。
《随园食单》的考据、文采、广博,放诸于中国古代文人著述中,的确过于单薄;然而在中国饮食典籍中,却是一座“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的丰碑。千年饮食之发展,袁枚毕生之心血,若无《随园食单》将其具象化,中国“美食王国”的传承,势必要失色不少。
清朝、袁枚、《随园食单》是中国饮食文化躲不开的三个关键词。揭开中国“美食王国”面纱之旅,还有什么比《随园食单》更适合的起点呢?不过时过境迁,作为一本古食单,《随园食单》对于今人来说毕竟还是多了晦涩,也因此,时不时就会有一本《随园食单》的今译本、注释本问世,以满足当下“吃货”们的求知欲。的确,一部经典的古籍就是一个精妙的传说,很值得后世的“导演”们一次次“翻拍”的。(江隐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