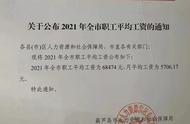原标题:彭士禄:中国核动力的“彭拍板”
彭士禄有两个外号,一个叫“彭大胆”,一个叫“彭拍板”。
他常说,自己一辈子只做了两件事:一是造核潜艇,二是建核电站。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哪一件,他都是敢于先吃螃蟹的人。
中国广东核电集团公司原董事长昝云龙与彭士禄共事20余年。1983年,彭士禄率领10人专家组南下广东创业,筹建大亚湾核电站,昝云龙任专家组组长。
昝云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面对特别巨大的社会工程时,彭士禄作为一名战将而不是统帅,考虑问题有时可能不那么面面俱到,但是他会打仗,总是冲锋陷阵。他是一个讲求实际的干事业的人,没有路也会找出一条路。
对此,彭士禄自己的名言是:“不怕别人怎么说,在别人的议论中走自己认为正确的路。”
2021年3月22日,96岁的彭士禄去世。3月30日上午八点半,依照他生前遗嘱,装有他和夫人马淑英骨灰的可降解环保型骨灰坛沉入他多年战斗过的葫芦岛海域。马淑英是彭士禄留苏时的同学,彭士禄一直叫她的俄文名字“玛莎”。
“没有尾巴好抓、头发好揪”
1956年9月,彭士禄、韩铎、董茵等五人被选送到莫斯科动力学院,与其他35位苏联学生组成特殊班。特殊班共分为四个专业,彭士禄等五名中国学生分在核反应堆等专业。
1958年,五名中国学生从苏联学成回国,韩铎夫人董茵被分配在二机部(后改名为核工业部)机关,彭士禄被分配在二机部原子能研究所。
这一年年底,中国组建了核动力潜艇工程项目,开始核动力装置预研。二机部副部长刘杰对原子能所副所长李毅交代任务时说,今后你们原子能所的“能”字就能在搞潜艇核动力的研究设计上。
李毅又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彭士禄,任命他为新成立的核动力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室没有主任,彭士禄为负责人,但因级别不够,只能当副主任。
核潜艇在任何国家都是最高机密,当时中国没有人见过核潜艇实物,最初的资料只有五张模糊不清的照片,以及一位外交官从国外给孩子买回来的一个逼真的核潜艇模型玩具。
经过两年的苦练,彭士禄带着全室基本过了英语阅读关,摸清了国外核电站、核动力装置的基本情况。他还着重抓了两件事,一是搞调查研究,二是对研究室的年轻人进行培训。

研制第一代核潜艇的四位总师。左起:赵仁恺、彭士禄、黄纬禄、黄旭华。图/受访者提供
“如果没有对我们这50余人进行培训,建立一支基础队伍,后面的事就只是说说而已。后来的许多事实也说明,彭士禄善于抓住主要矛盾,所以他才敢于拍板,做决定。他每次拍板心中都是有数的。”第三任中国核潜艇总设计师张金麟告诉《彭士禄传》作者杨新英。张金麟说,彭士禄也会拍错板,但他善于团结人,这些人在他身边给他当参谋助手,对他做的不正确的决定进行修正,再把他的决策推动下去。
董茵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彭士禄与赵仁恺、韩铎等几位主要骨干搭档,前有韩铎在理论方面替他堵漏洞,后有细致谨慎的赵仁恺在工程方面堵漏洞。
要不要建核潜艇陆上模式堆,是核潜艇研制中的一个重大争论。有人认为建造核动力模式装置代价高昂,且会推迟潜艇下水时间,不如直接造产品。彭士禄等则坚持,不经过陆上模拟直接装艇风险太大,而且造陆上模式堆等于造了一座核动力装置试验堆,可以培训人员,花这个钱是“吃小亏占大便宜”。最后,*和聂荣臻表态,陆上模式堆必须建。
1965年起,8000军民陆续来到位于四川大山沟中的“909基地”,建起了中国第一座潜用核动力装置陆上模式堆。
彭士禄担任了基地的副总工程师。他实际上是基地的技术负责人,担任“副总工程师”还是因为“级别不够”。直到1979年,他才被正式任命为中国核潜艇第一任总设计师。
1970年7月18日,陆上模式堆开始启堆试验,并逐渐升温升压,缓缓提升功率。每提升一档功率,出现的险情也越多。
蒸汽发生器的安全阀出现了漏气现象。这是设计人员按照常规高压设备方案设计的,他们觉得应该有这样一个安全阀,就像高压锅盖子上应该有一个排气阀一样。彭士禄则认为,根据热工计算原理,蒸汽发生器的最高压力是恒定的,不可能超压。既然有点漏气又不好处理,就干脆封死或取消这个安全阀好了。有人说,彭总,你这个胆子也太大了,彭士禄说,骑马拄拐杖,何必多此一举呢?
模式堆还连续几天出现停堆事故。彭士禄拍板,拆除了9个安全信号灯中冗余的4个。他说,过分追求安全,反而不安全。
8月30日,模式堆提升至满功率,运行成功。12月26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
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原总设计师黄士鉴说,当时处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只有彭士禄这样的人才敢这样做。那时你没错还把你当反革命抓呢,彭士禄是彭湃之子、根正苗红的烈士子弟,因此敢说自己“没有尾巴好抓、没有头发好揪”。“工程问题太复杂了,意见不一,一定要有一个负责人,敢于决断。没有彭士禄的拍板,好多工程是推动不了的。”黄士鉴说。
在大亚湾“趟浑水”
1982年,彭士禄当选为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翌年,他从核工业部调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总工程师,南下广东大亚湾,出任广东省核电站建设指挥部指挥长。
他对带去的昝云龙等10名技术骨干说,我们要做三年和尚,还要经历八年抗战,希望大家好自为之,不要犯政治错误、经济错误和生活错误啊。
1983年6月,广东核电合营有限公司筹建办成立,彭士禄担任主任,昝云龙担任常务副主任。9月,国务院成立核电领导小组,国务院副总理李鹏任组长,国家计委副主任黄毅诚任副组长,彭士禄是11名小组成员之一。
改革开放初期,迅猛发展的广东省遇到了电力紧缺这一瓶颈,每周只能“停三开四”,因此对建核电站寄以厚望。
彭士禄感叹,当时凡是需要广东方面配合的,广东都做得非常齐全周到。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任仲夷在病中送了彭士禄四个“千万”(千言万语、千难万险、千辛万苦、千方百计)的殷殷嘱托,主管副省长叶选平全力配合。筹建指挥部从广州迁至深圳的蛇口工业区后,袁庚将自己的办公室让出来给彭士禄使用。
广东电力局经过初步选址,勘察了4个地点,彭士禄考察权衡后,敲定了大亚湾。深圳市用最便宜的价格,划了一大片地给大亚湾核电站作为建设用地。
彭士禄等去法国考察后,因法国与中国关系较为友好、堆型丰富、运行也比较稳定,决定采用法国的M310堆型。
一位美国友人不解地问彭士禄,全世界能搞核潜艇的国家都能搞核电站,你们为什么还引进法国的核电站呢?彭士禄打了个比喻说,中国的乒乓球打得好,但足球就是踢不出去。核电厂的科研和设计中国都能做,就是大设备国内造不出来。
彭士禄攻读了国际原子能机构出版的《核电站投标经济评价》等文献。他不仅从书本中学,还在宴会、闲聊等各种场合向外国人学。很快他就入了经济学的门,提出了投资、进度、质量三大控制,并为投资和进度控制建立了数学模型。
一位经济学家说,彭士禄有一招,让学经济的人感到惊讶。他坚信宇宙是和谐的,凡成系统的,各部分之间必有比例关系。他从与各国投资者的交谈中,东一句西一句地问到了核电站各系统的价格比例,再参考一些资料,把比例关系的数学模型建立起来了。这样,只要算出一个子系统的基础价格,其他系统的基础价就估算出来了,大大简化了计算量。
经过自己的计算,彭士禄告诉大家,大亚湾耽误一天工期,会损失100万美元。他说,过去我们搞核潜艇是国家拨款,不用还债,利率等于零,“大锅饭工程的定义就是利率等于零的工程”。现在建商业性核电站,筹建工作不能等、不能慢,要快马加鞭。这个“时间等于金钱”的概念提出后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人给他贴上搞资本主义的标签,但他还是力排众议,说干就干。
广东方面提出,与香港合作建设核电站。1984年初,时任水电部核电局局长潘燕生南下深圳,参与谈判。
彭士禄主持了与香港中华电力公司的谈判,确定双方合资成立合营公司,其中内地控股75%,港方持股25%。
1984年5月前后,经与广东省协商,通过高层决策,水电部内部发文,推荐彭士禄担任合营公司董事长,广东电力局局长陈港担任副董事长,潘燕生担任总经理。
为了不延误工期,彭士禄在此前的3月15日就宣布核电站开工。潘燕生去现场宣布时,连记者都没有,开工仪式也没有邀请任何领导,也没有报告水电部部长钱正英,事后在报纸发了一个很小的消息。
潘燕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各方关系复杂,建设大亚湾核电站存在很多干扰,但彭士禄非常自信,也很坚定,压力再大也胸有成竹。“他是一位敢定事的领导,能排除外部干扰,真正按市场经济和技术根据来做定夺,我这个总经理当得很舒畅。”
昝云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按惯例一般都主张大*说了算,但彭士禄坚持重大问题决策必须取得双方一致意见。很多人对此不解,彭士禄说,香港方面尽管是小*,但它提供了市场,并且有丰富的经验。改革开放初期内地对国际市场了解不够,如果是一方说了算,那就很可能出问题。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是非常明智的。
谈判还在进行期间,彭士禄就“先入为主”。在决定征地后,还没有批准现场准备,他就通过招标,搞了“四通一平”工程。
彭士禄对移民工作没有经验,但他坚持两条:一是按政策办事,二是该给移民的一点不能少。拆迁中,由村民们自己选择搬迁地点,为每户盖两层楼,连带坟墓一起迁移,树木赔偿之类都在一年内完成。征地没有遗留任何问题。
昝云龙说,除了“四通一平”,彭士禄主张与法国电力公司签工程前期服务合同、用不到100万美元与三个顾问公司签订顾问服务合同、对大项目的招评定标进行评估等做法也都曾被诟病,但也都被后来的事实证明为正确的。
潘燕生说,彭士禄按市场经济思维办事,并不事事向上汇报。谈判期间,由于彭士禄人脉较广,香港方面也了解他的身份,对他很买账,很多人都希望能参与这个项目。
一次,经人介绍,约旦一家公司表示愿意为中方购买设备提供7.5亿美元贷款,贷款条件也很优惠。由于当时核电站建设资金还未落实,彭士禄在全聚德的饭桌上当场签了第一笔3亿美元的协议。
然而,这一过程是不符合程序规定的。协议签署后,约旦代表立刻飞到北京准备谈进一步合作,此时彭士禄尚未来得及上报。协议要求中国银行担保,中行毫不知情,向上汇报。国务院领导召集钱正英、潘燕生等人去中南海开会,叫停了这一项目。彭士禄没有参加这次会议。
会后,潘燕生去香港销号,叫停了这笔贷款,并通过新华社香港分社做了澄清。这次风波没有影响项目的进展,但彭士禄的工作受到了影响。
1984年10月前后,广东当地一位记者写了一份材料,列出了彭士禄在广核筹建办工作中的一些失误,陈述他不适合担任合营公司董事长,不具备领导核电的能力。这封信以中方五名负责人联名的名义送到潘燕生手上,潘燕生不认可信中内容,没有在信上签字,但信还是送了上去。
此后,中央领导找潘燕生谈话,明确彭士禄不在时由潘燕生全面负责广核筹建办工作。不久,彭士禄被调离广东第一线,回水电部主持核电工作。
1985年1月18日合营合同签订,原湖北省委副*王全国出任合营公司董事长,潘燕生任总经理,昝云龙任总经理助理。
昝云龙说,一开始整个大亚湾核电站工程都是一片“沼泽地”,由于彭士禄在初期的探索中趟了很多“浑水”,等于为后来的工程排了雷,为大亚湾的后续发展构筑了很好的基础。
彭士禄依然一心牵挂着大亚湾。1986年,受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件影响,香港百万人签名并游行,反对建核电站。彭士禄因公赴港时,大批记者包围他提问:“核电站会不会爆炸?”彭士禄说:“原子弹里的铀含量高达90%以上,好比酒精;核电站里的铀含量约为3%,好比啤酒。酒精用火一点就燃,而啤酒是点不燃的。”
这个经典比喻是彭士禄的杰作。1970年陆上模式堆启堆前,他被军管会从试验场紧急召回,回答人们“模式堆出事的话会不会爆炸”的质疑。好酒的他突然福至心灵,想出了这个妙喻。
这个比喻在不同场合中被多次引用,此后香港媒体的报道倾向开始转变,反核风波最终平息。这场普核活动成为教科书级别的危机公关案例。
“我们是真投标”
1986年,核电主管部门从水电部转移到核工业部,彭士禄也从水电部副部长改任核工业部总工程师,担任秦山二期核电站董事长,负责筹建工作,潘燕生担任副董事长。
秦山二期核电站最初决定引进,但与日本、德国谈了一年多仍没有结果。彭士禄给国务院领导写信,提出“以我为主、中外合作”的方针,被中央采纳,成为以后指导中国核电发展的主导方针。秦山核电站也成为了中国自行设计、建造和运营管理的第一座压水堆核电站。
潘燕生说,秦山二期核电站主要是技术人员当家,建设工作比大亚湾核电站要顺利得多。
秦山二期两台60万千瓦机组要148亿元人民币投资。当时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刚刚军转民,经济实力很薄弱,要投资就得靠国家支持。而国家明确告知,没那么多钱,需要自筹资金。
当时部分国有企业已经开始搞集资和股份制,彭士禄也想用这种形式募集资金。他把有意投资核电的省市及国家有关部门领导都请到秦山来座谈,并承诺:大家只要来投资,将来核电厂发电了,一定以最优惠的价格卖电,同时每年还能分得股份红利。大家都表示感兴趣,但却都说有困难,拿不出那么多钱。
彭士禄提出了一对一说服的“单兵教练法”,领着一班人一个星期内马不停蹄地跑了安徽省、浙江省、江苏省和上海市,一一说服了这三省一市投资。
安徽省在三省一市中最穷,但冲着彭士禄最后也同意参股1%。近30年过去后,安徽省哀叹:“我们吃了大亏了!如果早知道核电发展这么好,当初我们再穷也要投资到5%以上啊!”
那时《公司法》还没出台,但彭士禄率先引入工程“三制”,即业主负责制、招投标制和工程监理制,得到了中央的认可和支持。结果,秦山二期概算资金没有超,工程建设进度提前,特别是秦山二期3号机组,提前了5个月发电。

彭士禄(中)在秦山二期工地现场。图/受访者提供
引入招投标制在当时遇到很大阻力。按计划经济时期的通行做法,很多人主张设备应定点生产,争论得很厉害。最后,彭士禄坚持设计和设备全都要实行招投标制。时任国家计委主任黄毅诚也很支持,并且强调要公开投标,而不是假投标。
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原院办秘书科科长郭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1970年中国第一艘攻击型核潜艇下水后,由于缺乏业务,该院(由909基地迁入成都,1991年改名为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以下简称核动力院)经历了将近二十年的低谷期,因此上上下下对这次招标十分重视。他们当时投的是三标段,也就是核心部分的反应堆及一回路主系统。大家夜以继日地做方案,还派出了20多人的队伍去北京。
可是招标会前,核动力院听到风声:即使核动力院中了标,也不会真的获得这个项目。
据说,有上级单位希望由上海一家核电设计院来承担这个任务。因为当时普遍认为,核动力院是做核潜艇的,就做好你的核潜艇就行了,别到核电这个市场来。
得知消息的彭士禄向核动力院保证:“我们是真投标,希望你们回去认真准备。”核动力院参与投标的专家曾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本来没有什么信心了,如果没有彭士禄那一句话,可能相当一部分人就要打退堂鼓了。
最后投标的结果,核动力院分数大幅领先。即便彭士禄自己手中的5分投给其他单位,也依然是第一。由此,核动力院踏上了军民结合、高速发展的道路。
“酒圣”
第一艘核潜艇下水后,深山中的909基地又运行了十年。郭勇说,他是1975年来到909基地,成为中央控制室一名操纵员的。基地有很多彭士禄的崇拜者,按现在的话讲就是“铁杆粉丝”。每当他凌晨值班犯困时,他们就会给他讲“彭拍板”的各种逸闻趣事。
有一次,彭士禄请了裘怿春等几位单身在基地的小伙子来家吃饺子。吃饭前,夫人马淑英手抓一把筷子摆上桌,裘怿春就在这一瞬间受到启发,有了解决反应堆控制问题的灵感,后来这个发明就叫“束棒控制”。
由于爱好文学,郭勇被模式堆室推荐去参加国防科工委神剑学会组织的“两弹一艇”报告文学项目。当时,彭士禄已从核工业部调到水利电力部,担任副部长兼总工程师。在时任核工业部办公厅主任李鹰翔的帮助下,1982年元旦的第二天,郭勇早早赶到北广路1号水电部大楼,见到了彭士禄。
他记得,彭士禄个子不高,穿着一身西服,满脸笑容地接待了他,并向自己的秘书介绍:“这位是模式堆的战友!是四川老家来的人!我习惯把待了几年的909基地称为老家。有朋自老家来,不亦乐乎!”
郭勇递上了准备好的30多条提纲,彭士禄笑呵呵地接过去,说老家人布置作业了,自己要好好准备一下,4号早上来接他。
4号早晨,彭士禄亲自坐着车来,把郭勇接到家中,操着广味普通话,跟他谈了6个小时,还留他“喝点小酒,摆摆龙门阵”。
这次采访的第二天,彭士禄就南下广东大亚湾了。
郭勇再次见到彭士禄,是1989年夏天参加编写《中国核军事工业历史丛书:潜艇核动力装置卷》,去北京密云水库水电部招待所请彭士禄审稿时。该卷审了3天,那次的交流更多。
他记得,一起散步时,赵仁恺笑着对彭士禄说:“满功率运行没有你顶天立地的拍板,还不知要拖到何时。”彭士禄也笑着说:“现在想起还真有点后怕!”赵仁恺说:“彭总敢于拍板,也是当时环境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但拍板成绩按三七开的话,彭总应该是成功的!”
退休后很多年里,彭士禄仍然以顾问身份在中核集团自己的办公室里演算画图,直到身体情况再也不允许。
在北京海淀区甘家口的家中,彭士禄要靠老伴的搀扶在屋内走动。他喜欢在午后沏一壶普洱茶,点一支烟。每当家中来客,他总是以酒代茶。因为喜欢喝酒,他获得了酒友们颁发的“酒圣”荣誉证书。住院时,为了不被查房的护士发现,他还把啤酒藏在被窝里。
2018年7月24日下午,原首艇主机兵程文兆、反应堆一回路操纵员李善昌和辐射剂量监测员刘洁清代表第一代核潜艇艇员,前往北京协和医院探望彭士禄,赠送了他一艘首艇的模型。彭士禄戴着吸氧面罩,和三位老兵一同对着镜头敬了个军礼。
60多年前在909基地时,这几位老兵每天在工地都可以看到彭士禄。彭士禄给他们上课,讲授核物理、热工水力、高等数学、化学、电子学、辐射防护等几十门学科,课后再实操、模拟演练。
女儿常来医院看彭士禄,有时还带客人来,每次探视完了,他总是坐着轮椅坚持送客人到电梯口,等客人上了电梯后,他冲着人们挥手, 有时还调皮地跟女儿说“See you tomorrow”, 最后还来一个飞吻。这是他跟女儿之间特有的互动。
他在医院里获得了许多新的绰号:彭老乖、彭老赖、彭老帅、彭老六、老顽童……他告诉来访的《彭士禄传》作者杨新英,自己最不喜欢别人称他“中国核潜艇之父”,最喜欢别人称呼他“彭大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