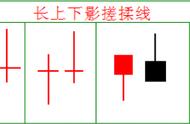下班回到家里,刚想做晚饭,忽然空气中飘来一股浓浓的香气,略带一些咸,不由得深深地吸了两口气,这味道好熟悉啊!对了,谁家在烀咸菜!

思绪一下子回到了我的童年——上世纪70年代。
那时候,大家都很穷,供下饭的菜很少很少,菜倒是自己还可以种上一些,尴尬的是没油!每年生产队在冬天都会榨油,在新年来临之前每家每户按人口分发。按当时我们的六口之家,大概能分到十斤左右的花生油,这便是全家全年能吃到的油了。也正因为吃油受限,很少能去炒菜,咸菜便成了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下饭菜。

每年我妈都会做三次“咸菜”——春天烀一大锅黑黑的咸菜,夏天晒一盆酱,秋后再烀一锅盐豆子。
每年小雪节气到来时,妈妈就会开始腌咸菜,用料就是自家种的辣疙瘩或萝卜,也有上面的辣疙瘩缨子或萝卜缨子,没卷好的白菜都可以,没什么讲究。妈妈把要腌的菜洗净,放进一口大瓷缸里,按菜的多少再放盐放水,就这样腌一个冬天。
来年惊蛰过后清明之前,妈妈选择在好的天气里,把腌好的咸菜捞出晾晒,晒到八成干就收起来,接下来就可以烀咸菜了。

记得妈妈总是在锅底先摆上几根香椿树的枝条,一为增香,二为咸菜不会直接接触到锅底而造成糊锅。香椿棒的上面摆上晒好捆扎成把的辣疙瘩缨子或萝卜缨子,上面用辣疙瘩或萝卜压着,免得它们浮起,倒入腌菜的卤汁,就开始烀了。
妈妈是个烀咸菜的能手,不知什么原因,别人烀的咸菜容易发霉变质,她烀的咸菜放三年都没事。起始大火烧开,改小火慢煨,发现锅里的卤汁变少了,要继续添加卤汁,也可以把反复烧开的卤汁舀出一些,再添加生的卤汁,就这样慢慢烧,慢慢烀。烧了一天一夜,咸菜由原来的颜色变成酱红,深酱红,最后变得乌黑,第二天的上午咸菜就可以出锅了。
刚出锅的咸菜,那叫一个香,附近的邻居都闻得到,还没来得及烀的人家可能会拿着碗过来要一点,主家也不会吝啬,装上满满一大碗新咸菜,让来人满意而归。他们之间就这样往来着。

煎饼卷大葱都知道吧?这是我们苏北鲁南地区独有的一种吃法,新烙的玉米煎饼或山芋干煎饼(那时候是不敢奢望吃小麦煎饼的),卷上新咸菜,再配一棵洗净的大葱,就是我们这里的人间美味,无需其它任何菜品,都能让人吃到撑。
随着生活品质的提高,黑咸菜慢慢淡出人们的餐桌,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使命,妈妈也早已离我而去。“爸爸,我饿了,我要吃饭”,孩子的一声叫唤,立马把我拉回现实,“噢,这就做”,我回应着。
难忘那时邻里间的你来我往,难忘妈妈的那锅咸菜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