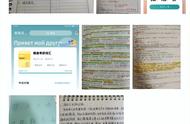近期读了一些外国名著,如利哈乔夫的《论教养》,梭罗的《瓦尔登湖》......常有一种不舒服感觉。那就是:很多外国作品的语言晦涩难懂,句子与句子间往往思维跳跃性很大,甚至常有前言不搭后语的现象。真有点像和一个略懂汉语的老外艰难地沟通。硬着头皮读着这些所谓的外国名著,实在有如梗在喉,味同嚼蜡之感!
当然,我也意识到,我们所读到的都是译本,是译者再创作的结果。我们所品尝的已不是作者原汁原味的私房菜,而是一个悟性不高的二流厨师,按着作者的菜谱,依葫芦画瓢的即兴发挥。至于加多、加少、加错了佐料应该是常有的事,做出来的是一道道有违初衷的冒牌菜。当我们品尝着它们时似乎觉得被下了迷药,似醒而醉,似断还续,似是而非,如在云里雾中。而这些定然是原创者所不乐见的。
坦率地说,活了半辈子,读过的外国名著并不多。真是没资格对这些“山珍海味”指手画脚、品头论足。仅仅是因为对近期的一些外国作品的确有些失望。怀疑自己以后到底应不应该多读点外国作品。
但印象中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古希腊的《伊索寓言》,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语言却极其朴实、生动、流畅。大量精妙入微,精雕细刻、不厌其烦的细节描写,气势恢弘、排山倒海、一气呵成,让人心悦诚服。
而这样的作品似乎少之又少。总体感觉:西方文化底蕴与我们五千年的积淀不可同日而语。
于是我便暗自思忖:语言是思维的外壳。“语言的舒展即是思想的流畅,语言的优美源于思想的精致;相反,语言的苍白即是思想的苍白。表达的词不达意、语无伦次,只因为思想的贫乏和浮浅,只因为缺乏精深之思,却又要‘为赋新词强说愁’”。
这也许恰恰反映了西方文明程度的确不高的现实。 相比流畅、厚重、博大、严密华夏文明,西方文化难免显得稚嫩、肤浅、笨拙和粗疏!
这应该是我们文化自信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