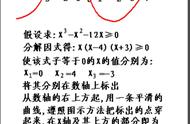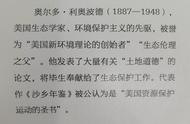七月,在寂静的清晨,在人类社会醒来之前,农场早就开始了一天的喧嚣。田雀鵐用男高音般的歌声宣告了自己对北美短夜松树林的占有,旅鸫声明了对树杈的权利;莺鹪鹩,玫胸白斑翅雀,黄林莺,主红雀,莺雀……组成了大合唱的团队。
在遥远的过去,整片田野都曾经是罗盘花的领地,可是现在它们只能在墓地的角落里苟延残喘,人们不知道,他们正在以刈割杂草的名义,焚烧着历史书。
这是一种天意,它没让那在彼此灭绝中建立起现今世界的成千上万的动物和植物物种具备一种历史意识。现在,同样的天意也使我们与这种意识无缘。当最后一头美洲野牛离开威斯康星时,几乎没人悲伤,因此,当最后一棵罗盘花跟随着它到那人烟稀少的茂盛的草原去的时候,也几乎无人悲伤。

八月,有一幅画,正是欣赏的好时候。这幅画,是这样易于消失,以至于除了某些长阳四处的鹿意外,几乎无人得见。绘制这幅艺术品的作家,是一条河,作品是以一条宽阔的泥带开始的,它淡淡地涂在向后退去的河岸的沙子上。
但是,当我看见这条泥带因为荸荠草而变成绿色时,我便特别小心地注视着,因为它是这条河拥有了绘画灵感的信号。几乎过了一夜,这些荸荠草才变成了厚厚的草甸,那样葱翠,那样稠密,连那些从邻近高地上下来的草原田鼠也经不起诱惑了。它们倾巢出动,来到这绿色的牧场,而且显然是要整夜整夜地在天鹅绒般光滑的厚毯子上摩擦它们的肋骨。一条整洁漂亮的曲曲弯弯的田鼠足迹证实着它们的热情。鹿在绿毯上走来走去,显然只是为了使脚下感到舒适。

九月,我们可以欣赏到丛林中的合唱。山齿鹑,隐夜鸫,草原松鸡,旅鸫……都是这支合唱队的成员。
我们为这支几乎就在我们的门口台阶上唱出的清晨赞歌而骄傲。而且,不知怎么地,在秋色中,那些松树上的发蓝的针叶,从那时起,就变得更蓝了;甚至那些松树下由悬钩子铺成的红地毯,也变得更红了。

十月,当落叶松变成烟样的金色的时候,是狩猎披肩榛鸡的季节。
狗对什么是榛鸡栖息之处,要比你知道得更清楚。你要认真地、紧紧地跟着它,从它竖起的耳朵上读出微风正在讲述的故事。
十一月,是相对比较安静的季节,急匆匆的风从玉米地里掠过,从沼泽地里吹过,从沙洲上吹过,带来了雁群归去的叫声。
当雁队在天边成了模糊的黑点时,我听到最后一声雁叫,听起来像是在企求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