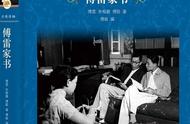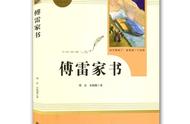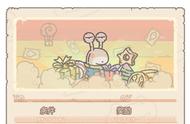傅聪

2012年傅聪(左)与傅敏在北京合照

傅雷书信手稿

20世纪70年代,傅聪在肖邦故居

当地时间12月28日,著名华人钢琴家傅聪因感染新冠肺炎在英国逝世,享年86岁。傅聪被誉为“中国的肖邦”,也被誉为“中国的钢琴诗人”。昨天,本报全媒体记者采访了傅聪先生的家人和生前相关好友,对于傅聪的猝然离去,弟弟傅敏悲伤难抑。他表示,哥哥的音乐里始终贯穿着一种浓烈的“家国情怀”;译林出版社出版顾问、《傅雷文集》的出版人江奇勇也表示,傅聪之所以染疫,与之前手术后抵抗力下降有关系。“他的世界离不开钢琴。所以哪怕手术后,他依然每天坚持练琴。”而国际钢琴大师郎朗也在微博中表达了自己的哀悼:“傅聪大师,我十分敬重的伟大的艺术家,愿天堂没有病痛。”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肖欢欢
图/译林出版社提供
傅聪弟弟傅敏:“钢琴就像他的生命”
傅聪的弟弟傅敏28日知道傅聪染疫,起初只知道哥哥住院,但没想到哥哥的病情进展这么快。当妻子陈哲明告诉他哥哥去世的消息后,傅敏心里十分难过,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傅敏告诉记者,父亲傅雷对兄弟俩的教育不是口号式的,而是通过行动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父亲从小就教育他们,一个艺术家永远要保持赤子之心,这一点对哥哥傅聪影响尤其深远。傅聪的演奏富有中国韵味,他的音乐里始终贯穿着一种浓烈的“家国情怀”。“傅聪在国外的日子并不好过,他一直以为当年是他出走波兰而连累了父母,所以心中一直很难过。”傅敏说。
让傅敏印象深刻的是哥哥的谦逊。傅敏说,傅聪从来不妄称自己是大师,他不止一次表示,自己只是对音乐保持着最初的纯真和饥渴。而傅聪对钢琴的痴迷让傅敏印象深刻,他说,哥哥是不折不扣的“琴痴”。早在几年前,傅聪做过两次手术,医生建议他手术后静养,不要弹钢琴,妻子卓一龙苦劝不下,打电话让傅敏相劝。但对于傅聪来说,要离开钢琴太难了。“钢琴就像他的生命一样。”在傅敏印象中,哪怕到了80岁,傅聪依然保持着每天练琴的习惯,每天练8小时也不觉得累,即便后来身体不好时,每天也要练5小时。
说起傅聪去世的消息,傅敏的妻子陈哲明昨天在电话中也十分悲伤。“我们全家人都沉浸在悲痛之中,哥哥去世的消息是我告诉傅敏的,他现在听力不是很好,心情也很糟糕,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接受哥哥离开的消息。”陈哲明告诉记者,因为现在英国的疫情十分严重,并且中英之间的航班也处于停航状态,所以一家人暂时还没有去英国处理后事的计划。“我们需要平静一下,然后再商量下一步。”
陈哲明表示,他和傅敏见到傅聪已经是4年前了。最近几年,傅聪做了几次手术,身体不是很好。但没想到,4年前的那次见面竟然是最后一次。
“父亲并没有偏心”
如今大家看到的《傅雷家书》多数是傅雷写给傅聪的,而傅雷和傅敏之间的书信来往却很少。不少读者误认为这是傅雷“偏心”。对此,傅敏告诉记者,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我在国内,与父母接触的机会更多,父亲对我可以说是耳提面命,言传身教,这种教育远比家书要深刻得多。”傅敏说,当时父亲也给他写了很多信,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他看不到前途,非常苦闷。很多书信都被他烧了。“哥哥在国外,所以他的书信能完整地保存下来。但父亲对我的爱和关心丝毫不比哥哥少。”并且,之前傅聪一直反对将自己的回信收录在书中公开,他认为自己没有父亲那样行云流水的文笔,也没有父亲那样学贯中西的学养,实难与父亲相提并论。
傅敏回忆,哥哥傅聪是音乐天才。“他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傅敏说,在傅聪三四岁时,父亲发现他对古典音乐有股狂热劲,百听不厌,觉得他是学音乐的料,于是开发其潜能,让傅聪在8岁半时跟着当时最优秀的钢琴老师学习,并扩展其视野,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其实当时父亲也曾尝试让我学习音乐和美术,但最终发现我实在没有这方面的特长,最后只好作罢。所以,说我父亲偏心的,那是不了解情况。” 傅敏说。
傅敏坦言,父母从小就教育他们要热爱祖国。当时哥哥到国外去,其实父亲心里很矛盾,但他也知道,如果当时儿子在身边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所以尽管他非常热爱自己的祖国,还是将儿子送到了国外。
出版人江奇勇:“他一直有个心结”
得知傅聪去世的消息,《傅雷文集》的出版人江奇勇感到既震惊又难过。此前,江奇勇曾和傅聪、傅敏兄弟有着不错的交情。“我前天从媒体得知傅聪染疫住院的消息,即与傅敏妻子联系确认,傅敏妻子告知,的确住院,是肺炎,没有让傅敏知道。我要求一旦有好消息一定立即告知。不幸今天上午得到大师离世噩耗,痛哭一场。一位杰出的钢琴家、艺术家走了。”江奇勇说。
江奇勇告诉记者,他是1981年编辑《傅雷译文集》时与傅家兄弟相识的。在江奇勇的记忆中,因为工作的原因他曾多次和傅聪接触。1998年《傅雷文集》出版,江奇勇所在的安徽文艺出版社在上海举行签售,傅聪、傅敏都参加,都住在东湖宾馆。恰逢江奇勇当年编辑出版了李泽厚《论语今读》,他送了傅聪一本,没想到傅聪对这本书非常感兴趣,竟然很快翻完。“他真的是天资聪颖,读书之快令人惊讶。显然他不仅琴弹得好,书也读得广。”
江奇勇回忆,2003年《傅雷家书》(三联书店版增补本)发售,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为了与三联书店版区分开来,他做了几个封面设计,最后选择了一个比较接近普通百姓的封面,里面还附录了大量照片。傅聪在给读者签名时看到这个版本,就给傅敏打电话质问,傅敏向他解释,是为了贴近市场才需要这样做的。傅聪说:“我宁愿不这样广泛传播,也不愿意这样出版。”江奇勇说,傅聪、傅敏兄弟俩关系非常好,但傅聪非常较真,为了这事,兄弟俩大吵一架。这是极为罕见的。后来,他专门到北京傅聪住地,当面向他道歉,傅聪的情绪这才稍微缓和一些。傅聪表示:“傅家总还要留点隐私,不能什么都透露给读者。”
2012年,傅敏夫妇准备傅雷夫妇骨灰安葬仪式墓碑,原来有个设计,是有傅雷夫妇画像的,但傅聪不同意。后来傅敏夫妇用了傅雷家书中一段话,“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他这才同意。原来安葬仪式安排在2013年清明,但傅聪希望推迟时间,等他回来再安葬,于是仪式就安排在了2013年10月。父母安葬前的日子里,傅聪拒绝接受任何采访。“傅聪当时的心情很复杂,他心中一直有一个心结,觉得当年自己出国,可能连累了父母。” 江奇勇说。
每天只吃两顿饭的“巨匠”
江奇勇记得,最后一次听傅聪弹琴是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大约是2014年。“当时他弹莫扎特、海顿曲目,完全是人琴合一,这种境界恐怕很难有人企及。有人评价,傅聪晚年的琴艺达到巨匠水平,此言不虚。”
江奇勇介绍,小时候因为顽皮,傅雷罚傅聪不吃午饭。后来他长大了满世界巡演,也是饿一顿饱一顿,傅聪却从来没嗔怪过父亲,他说,得益于父亲的惩罚,他从来不吃午饭,一天只吃两顿饭,这对于弹钢琴很有帮助,因为吃午饭容易瞌睡。哪怕后来成为举世闻名的钢琴家,傅聪多年来始终保持着这样的习惯。
江奇勇说,这两年傅聪进行过两次手术,术后医生都要求静养,可是他不听医嘱,还是坚持弹琴,以致再度住院。傅聪之所以染疫,与之前手术后抵抗力下降有关系。“他的世界离不开钢琴,所以手术后依然每天坚持练琴。”
郎朗追思傅聪:
“他是我们精神的灯塔”
傅聪去世的消息也引起了音乐界的关注。国际钢琴家郎朗在微博中表达了自己的哀悼:“傅聪大师,我十分敬重的伟大的艺术家,愿天堂没有病痛。” 郎朗表示,傅聪对他的激励非常大,他至今仍清楚地记得,2001年自己在伦敦首演拉赫玛尼诺夫第三钢琴协奏曲,音乐会结束后傅聪跟他拥抱的动情场景。郎朗说自己永远忘不了傅聪大师对他的叮咛——要永葆赤子之心。“他是真正伟大的钢琴诗人,也是古典音乐里的一股清流,是我们精神的灯塔。”
此外,国家大剧院也发文悼念。而阿格里奇基金会在官网上留言:我们将永远记住他,他是一位具有伟大人格的伟大音乐家。
记者手记:
有趣的灵魂 真正的绅士
傅聪与广州一直非常有缘,他曾数次来广州进行钢琴独奏演出。在2013年夏天,经过和傅聪经纪团队的提前预约,笔者曾在广州观看过一次傅聪的演出,并和傅聪有过一次会面。当晚,虽然已经将近80岁,但一身黑色演出服的他看起来风度翩翩,美妙的琴声从他修长的手指上滑过,妙不可言。贝多芬、舒伯特、彪德西等名家的作品经过他的演绎,作为钢琴“门外汉”的我听起来也别有一番味道。
在当天演出结束后,我和另外一位记者一起和傅聪先生进行了对话。因为演出结束后要稍作休整,所以傅聪到达预定的见面地点略晚了几分钟,见面后他接连致歉。傅聪说,自己从小家教极严,吃饭不能出声音,言必信、信必果,答应别人的事情一定要做到,和人约定时间不能迟到,这都是父亲从小就一直强调的。“我小时候和父亲约定时间出去,我们都要提前10分钟到,否则迟到了就要罚站。”他笑着说。
其实我对于傅聪的了解,更多是来自于那部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傅雷家书》。但让我颇感意外的是,傅聪告诉我,《傅雷家书》他自己都没有看全。“我每次看《傅雷家书》的时候都心潮澎湃,没办法冷静下来,我都会想起很多和父母在一起的故事,我一整天都没法做事情。”他说。
傅聪早于上个世纪60年代已被《时代杂志》赞誉为“中国当今最伟大的音乐家之一”,但他却表示从来没觉得自己是音乐大师。“我觉得自己是一个钢琴匠,是音乐的囚徒。”傅聪与肖邦有着不解的缘分。他也是公认的演奏肖邦的权威,被称为“中国的肖邦”,但傅聪却告诉我,他只是肖邦忠实的追随者而已,也并不喜欢“中国的肖邦”这个称呼。
和父亲不同的是,傅聪对子女的教育比较宽松。“我知道被逼着做事情的感受,所以我不会要求我的子女一定要做这做那,所以你看到,我的孩子没有一个是弹钢琴的。”他笑着说。和傅聪聊完天,我不由想起一句话:这是一个有趣的灵魂,真正的绅士。
没有“傅聪”,只有音乐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肖欢欢
2009年5月13日,在傅聪莅临广州星海音乐厅之前,当时的广州日报记者龙迎春曾独家专访傅聪先生,听他自己如何谈音乐,论人生。而今,得知傅聪先生逝去的消息,龙迎春也回忆起11年前专访傅聪先生的点滴往事。
文/广州日报特约记者 龙迎春
今天早上看到了傅聪先生在英国去世的报道。我在广州日报工作期间,曾经有幸在几年中,连续听了他的几场音乐会。印象最深的一次,他穿着深蓝的对襟衫从星海音乐厅的侧台出来,全场掌声雷动,而他在钢琴前坐下来之后,观众席立时鸦雀无声。
一个外行,很难形容他的琴声。他的双手在琴键之上,编织出了一个曲折往复的世界,层层叠叠,精巧回环。作为听众,唯有屏息静气,才能感受到他的魅力。更有幸的是,我连续几年一直磨着左岸文化的创始人方洁,也是傅聪先生音乐会的主办者,希望能够采访他。连续磨了三年,2009年,他在广州星海音乐厅举办海顿音乐会之前,终于得到他的应允,给了我五十分钟的电话采访时间。
一旦接受采访,傅聪是随和而绅士的,除了我问到的婚姻问题被他毅然打断,他对于我提及的其他问题,包括他受伤的手(腱鞘炎)、他对音乐的理解、他对技巧和投入的诠释,都毫无保留地与我分享。他反对钢琴家标榜自我风格,在他看来,没有“傅聪”,只有音乐;作为诠释者,只有肖邦,或者只有海顿;在他看来,钢琴家犹如布道者,整个一生都是对艺术的“殉道”,根本没有正常的生活,但对于这一点,他甚至连遗憾的时间都没有,因为他所有的时间,甚至灵魂都投入了其中。
那一年的演出结束后,我被邀请跟傅聪先生一起晚餐。听他讲黄宾虹和父亲傅雷的交往。他还说起自己除了练琴,一切从简,尤其是住酒店,只要一张干净的床就够了。
总以为等自己空一点了,还会有机会听他的音乐会,还能再见到他。但他今天走了,他是一个时代的绝响,而他的好友之一、天才大提琴家杜普蕾早已夭逝。这些伟大的灵魂和智者,是隐藏在我们生命中的密码和开关,不知道哪一天,会以什么样的因缘被碰触到,打开来,我们被琐碎淹没的日常生活,便在那一瞬间被点亮和照耀,人间杂碎、车马喧嚣皆可暂置一旁,做一回纯粹的人。
仅以此送别傅聪先生,他其实并不需要,是我们,想念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