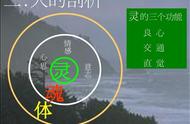《世说新语》以“简约玄澹”(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十三)的风格著称,并成为对应于晋人精神风度的史料而为世所重,但此书究竟是脱逸还是融入了中古骈文衍进的历程?学界似乎未予深究,即使是欣赏其修辞,也正如明代学者王世贞《世说新语补序》所言:“至于《世说》之所长,或造微于单辞,或征巧于只行,或因美以见风,或因刺以通赞,往往使人短咏而跃然,长思而未罄。”[1]人们的审美惯性往往被其意味盎然的“单辞”、“只行”之美所吸引和强化。其实,《世说新语》中分布的偶辞、双行之美亦值得关注。从本文形态上看,《世说新语》是一部衍生性文本,编述者是刘宋宗室刘义庆,他本人爱好文义,喜招聚文学之士,《世说新语》应是他和宾客文人采缉旧文编述而成。无论是编述者于“采掇综叙”之际附加了审美用心[2],还是“采缉旧文”的始源性材料中自然葆有审美的时代印痕,总之,《世说新语》中存在的对句之美,既体现汉末至晋宋文学修辞琢炼雕饰的演进方向,也折射对偶形式的思辩法则与认识功能,因而是中国骈文发展史上需要深化研讨的一环。
一、《世说新语》与语言生态
诚如刘应登所论:“晋人乐旷多奇情,故其言语文章别是一色,《世说》可睹已。《说》为晋作,及于汉、魏者,其余耳。虽典雅不如左氏国语,驰骛不如诸国策,而清微简远,居然玄胜。”[3]《世说新语》所载述的主体多为晋人,也上涉至汉末,其“言语文章”自成特色,尤以“清微简远,居然玄胜”为风格标志。所谓清简,也可以说是不求繁复,作为其极致性的表达,有时是不言之妙,有时是一言半句。举两例:
阮宣子有令闻,太尉王夷甫见而问曰:老、庄与圣教同异?对曰:将无同?太尉善其言,辟之为掾。世谓三语掾。卫玠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于三?宣子曰:苟是天下人望,亦可无言而辟,复何假一?遂相与为友。(文学18)
符宏叛来归国,谢太傅每加接引,宏自以有才,多好上人,坐上无折之者。适王子猷來,太傅使共语。子猷直孰视良久,回语太傅云:亦复竟不异人!宏大惭而退。(轻诋29)[4]
阮宣子“将无同”三字句关涉清谈中名教与自然关系的重大命题,王子猷的“亦复竟不异人”六字句让自负的叛人感到无地自容,且具显口语风。自矜于“无言而辟”或“一言可辟”,是晋朝清谈之士敢于傲人之处,但如果将这种简约语风看得笼罩一切,也是有失客观的。这就要从语言生态上估量晋人“言语文章别是一色”的内涵与条件。
在名士的清谈玄辩中,甚至脱口而出訾骂之意时,可以观察到巧妙的骈语对句。如《世说新语·轻诋》的如下一则:
庾元规语周伯仁:诸人皆以君方乐。周曰:何乐?谓乐毅邪?庾曰:不尔。乐令耳!周曰:何乃刻画无盐,以唐突西子也。(轻诋2)
周顗不喜舆论把他与名士乐广相比拟,这里的“刻画无盐”与“唐突西子”,组词搭配上是平行匀称的,两句的形态在对句平行之外,还能做到没有平板感,“刻画无盐”是因,“唐突西子”是果,句意上下纵贯。这种句意表达的方法更早出现于东汉之末,孔融《汝颍优劣论》引“陈群曰:颇有芜菁,唐突人参”。到了骈文更为成熟的齐梁之时,任昉写《到大司马记室笺》有曰:“惟此鱼目,唐突玙璠。”[5]三例比较而言,《世说新语》所载周伯仁语,对句既富有横向的动宾搭配上的平行感,又有纵向的上下因果意的贯穿,所以其遣言达意是相当富于修辞功力的。
魏晋时期以来,汉语词汇史正发生着较为强烈的变化,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指出:“复词的逐渐增多是近代汉语的一贯趋势。”[6]吉川幸次郎注意到《世说新语》中助字增加的新现象,甚至说它“是助字过剩的文章”,其中也有“复合助字”,这与“二音复合语的流行”的中国语发展大方向相吻合。又精辟地指出“《世说》的文章中四字句、以及作为其延长的六字句极多,以四音与六音为表现观念,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语的自然要求”。[7]志村良治从更具体的角度,认为这一时期语言现象的新变中,就体现为“复音节词的增加”,以及“以复音节词为单位,确立了四六的基调”,他在归纳分析这一现象时,特别提到了《世说新语》:
骈文就建立在四字、六字的基调之上。舍去骈文绮丽的外观不谈,把它底层潜在的四六基调作为问题提出很有必要。因为连乍一看似乎正相反的《世说新语》中,已经可以看出同样的以四六为基调调整文句的倾向。[8]
关于骈文的四六基调,刘勰《文心雕龙·章句》所说“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节也”[9],就是指四六基调的稳定的表现力,决定了六朝骈文的盛行[10]。通常骈文是少不了整饬绮丽的外观的,以至于使人觉得是远离现实语言的修辞性的文体。在这个标准的作用之下,《世说新语》“乍一看似乎正相反”,书中呈现的简澹鲜活的语体语风,很容易误将它脱逸于中古骈文发展进程之外,多数骈文史论著对于《世说新语》在骈文进程史中的意义还评价得不够充分。吉川幸次郎举出了堪为《世说新语》文章理想的一例:“道壹道人好整饰音辞,从都下还东山,经吴中,已而会雪下,未甚寒,诸道人问在道所经,壹公曰:风霜固所不论,乃先集其惨淡,郊邑正自飘瞥,林岫便已皓然。”(言语93)[11]“整饰音辞”具有时尚之力。志村良治提醒说《世说新语》中四六句调随处可找。
《世说新语》不仅可以看出以四六为基调组织文句的倾向,而且句意表达中的对偶现象也反映了语言生态的丰富性。由于《世说新语》既具有保存口语的文献属性,又体现知识群体的雅趣,所以通览其中的对句表现,有助于理解骈文在中古时期开花结果的生活土壤。这里还想指出,骈文固然是向着美文的方向发展,但也不应忘记,俪语偶句也与语言生态相胶着,在某种意义上也能约略反映口语化的底蕴。王锳《韩愈散文中的一些口语成分》一文作出了有趣的考察,他认为韩愈古文追求的是一种仿效秦汉、脱离当时口语的“超语体”,但他的书面语不可能完全摆脱口语的影响,典型的例子是他一方面写了刻意仿古求雅的《平淮西碑》,一方面又写了解决现实问题的《论淮西事状》,如文中论从外乡调集兵员不如本乡之便:“所在将帅,以其客兵难处使,先不存优恤。待之既薄,使之又苦,或被分割队伍,隶属诸头。士卒本将,一朝相失,心孤意怯,难以有功。又其本军各须资遣,道路辽远,劳费倍多,士卒有征行之艰,闾里怀离别之思。”此文就属于口语成分较多的代表,文中使用了大量双音词,客观上反映了中世汉语生态的一种趋势,“道路辽远,劳费倍多,士卒有征行之艰,闾里怀离别之思”这类的四六基调与语体感的结合,应是我们考量文体和修辞时所应顾及的。[12]
二、对句生成与清谈时代
刘勰《文心雕龙·丽辞》总结骈俪文体的生成原理时指出:“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13]论证骈文的理法意义,以自然法则作为文辞偶对的终极依据,带有玄学本体论的色彩,并由此而赞赏偶对技巧的顺势而成,不落于过度雕琢。
所谓“造化”,意指大自然,也意味着孕育化生之道,这是由道家哲学强化起来的概念,《庄子·大宗师》即谓“今一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14]。刘勰从自然之道所得到的启示表明,无论是道的形质外化,还是道内在于万物的法则,现象或事物间的关系是根源性的。人们或许会质疑刘勰,毕竟“支体必双”也存在反证,刘勰在这里对师法自然所作的“支体必双”的举证,似乎陷于偏颇。诚然,这确实涉及师法自然的哪些特征和理法,其实刘勰的深意在于看重万物或自然事件之间的关系,可以是彼此感应、共鸣,抑或对比、转化,所以,神理所关,没有孤立存在的事相,即刘勰所谓“事不孤立”。早期儒家哲学也强调关系,但它的关系较重于或限于人事与社会层面。而道家哲学则更为宽泛,涵盖了所有事物,即万物之间的关系。经历了魏晋玄学的熏染,道家哲学以及《易》学所主导的这种思维框架更为深入人心,延展到人格层面与文学层面。不难想到,老子《道德经》列举过一长串对反概念,如高下、有无、善恶、重轻、静躁、雄雌、白黑、弱强、巧拙等,这些矛盾对子不仅带来对照效果,而且对反双方也是相互依存的,这种矛盾相济的关系在“高下相须”一语中可加体会。所以,刘勰有理由认为,作为偶辞俪句的存在依据,是“高下相须”这样的万事万物之间既相互对比对反、又相互依存转化的关系所支撑的。
《世说新语》中分布的对句,颇多“自然成对”之妙。这首先表现在扩大了对万物与人世间“事不孤立”的观察范围。《老子》提到“万物负阴而抱阳”[15],如果说超越的“道”是无形无名的,那么通过认识蕴含在万物中的二元对反之理,应该有助于体悟所谓道真。可以理解,《老子》为什么津津乐道各种矛盾相济的对子,老子甚至说:“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16]这种观察视野和思想方法,对于惯常的善恶或邪正的界限就有所打破,并推动认识视野的多元,以及认知局限的突破。《世说新语·德行》篇中的如下五条可资举证:
陈仲举言为士则,行为世范……(德行1)
陈元方子长文有英才,与季方子孝先,各论其父功德,争之不能决,咨于太丘。太丘曰:元方难为兄,季方难为弟。(德行8)
王戎、和峤同时遭大丧,俱以孝称。王鸡骨支床,和哭泣备礼。武帝谓刘仲雄曰:卿数省王、和不?闻和哀苦过礼,使人忧之。仲雄曰:和峤虽备礼,神气不损;王戎虽不备礼,而哀毁骨立。臣以和峤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应忧峤,而应忧戎。(德行17)
王平子、胡毋彦国诸人,皆以任放为达,或有裸体者。乐广笑曰:名教中自有乐地,何为乃尔也!(德行23)
晋简文为抚军时,所坐床上,尘不听拂,见鼠行迹,视以为佳。有参军见鼠白日行,以手板批*之,抚军意色不说。门下起弹,教曰:鼠被害,尚不能忘怀;今复以鼠损人,无乃不可乎?(德行37)
陈仲举能在言行合一上彰显德性,叙述者正是有见于“言”与“行”其实是有张力的一个对子。有时一个人的仪态与内心也有反差,《谗险》篇就称:“王平子形甚散朗,内实劲侠。”“散朗”是玄学时代所孕育和崇尚的一种风度,在《世说新语》中就有以“林下风气”著称的贤媛谢道蕴获得过此誉。这里王平子外表的“散朗”,因与内在的“劲侠”素质构成了太大的反差,使人观察到一种伪饰感。当然,像“散朗”这样的风度表现,也应显示为一定的立体内涵,个性的复杂性可以提供各种形态的剖面。《言语》篇中如下的例子,又利用形表与内心的反差关系的多元,以及兄弟二人应变的言语机智,相映成趣:
钟毓、钟会少有令誉。年十三,魏文帝闻之,语其父钟繇曰:可令二子来!于是敕见。毓面有汗,帝曰:卿面何以汗?毓对曰:战战惶惶,汗出如浆。复问会:卿何以不汗?对曰:战战栗栗,汗不敢出。(言语11)
“汗出如浆”与“汗不敢出”,是两种相反的身体状态,却可以同样指向惶恐紧张的精神状态。两位少年的答语本身也构成了对句,前半的“战战惶惶”与“战战栗栗”可谓“言对”或“正对”,后半的“汗出如浆”与“汗不敢出”可谓“反对”,完成了共同的指向,消解了来自最高权威者的问难。在这段叙事中,二钟言语之机敏,调动出多重的对比关系,形成对句修辞,为开脱情境服务。写骈文或文中寓骈,通常都是一人撰作。像这样的机智应答,由两人或三人之间的对话而形成对句修辞,是《世说新语》所载“言语”之所擅。再如:
顾悦与简文同年,而发早白。简文曰:卿何以先白?对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质,经霜弥茂。(言语57)
顾悦借用自然界植物的质性之异来解释人与人的体质表现上的差异,可谓善用生活智慧,且字句对偶的凝练本身也自具理趣与美感。《论语·子罕》载孔子的名言:“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不过,这是散语单句,到了清谈时代的人们就更善于融炼对句了。
《世说新语》中分布的对句背后的认知反思,还与魏晋玄学时代价值多元化的思想激荡有关。例如,名教中的“孝”历来受到提倡,到了玄学时代,却出现了“生孝”与“死孝”的对比考量,关键在于形式上的“备礼”或“不备礼”,刘仲雄的观察是具有玄学洞鉴力的:“和峤虽备礼,神气不损;王戎虽不备礼,而哀毁骨立。”这一观察涉及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形态,打开了种种对比视野。“鼠被害,尚不能忘怀;今复以鼠损人,无乃不可乎?”字句虽不十分工整,却足称妙对,将“人害鼠”与“鼠损人”加以比对,即鼠从遭害对象到害人主体的转化,刺激原有心态立场而达成省悟,也以特殊方式呼应了孔子关怀“伤人乎,不问马”的人道情怀。
汉代儒术独尊局面打破后,名教的价值标准不是唯一的,而且往往需要重新审视和解释,尤其在乱世,仕隐的价值观必然产生碰撞,《世说新语》所载下例实是仕隐价值观的一种论战:
南郡庞士元闻司马德操在颖川,故二千里候之。至,过德操采桑,士元从车中谓曰:吾闻丈夫处世,当带金佩紫,焉有屈洪流之量,而执丝妇之事。德操曰:子且下车,子适知邪径之速,不虑失道之迷。昔伯成耦耕,不慕诸侯之荣;原宪桑枢,不易有官之宅。何有坐则华屋,行则肥马,侍女数十,然后为奇?此乃许、父所以慷慨,夷、齐所以长叹。虽有窃秦之爵,千驷之富,不足贵也!士元曰:仆生出边垂,寡见大义。若不一叩洪钟,伐雷鼓,则不识其音响也。(言语9)
这是书中字句偶对偏于全体工整的段落[17]。所拟庞士元以“屈洪流之量,执丝妇之事”来唐突司马德操的丈夫情怀,但对方却以高隐的价值观为更值得坚守,从“邪径之速”与“失道之迷”的重重判断,到古代高隐之士的人事验证,令发难者服理认输。
《世说新语》有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之宣言,据冯友兰《论风流》一文概括,真风流的构成条件是必有玄心、洞见、妙赏和深情。[18]兹从对句生成的角度稍加举证引申:
庾公造周伯仁。伯仁曰:君子何欣说而忽肥?庾曰:君复何所忧惨而忽瘦?伯仁曰:吾无所忧,直是清虚日来,滓秽日去耳。(言语30)
张玄之、顾敷是顾和中外孙,皆少而聪惠。和并知之,而常谓顾胜,亲重偏至,张颇不恹。于时,张年九岁,顾年七岁,和与俱至寺中。见佛般泥洹像,弟子有泣者,有不泣者。和以问二孙。玄谓:被亲故泣,不被亲故不泣。敷曰:不然,当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言语51)
孝武将讲《孝经》,谢公兄弟与诸人私庭讲习。车武子难苦问谢,谓袁羊曰:不问则德音有遗,多问则重劳二谢。袁曰:必无此嫌。车曰:何以知尔?袁曰:何尝见明镜疲于屡照,清流惮于惠风!(言语90)
孙子荆年少时欲隐,语王武子当枕石漱流,误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孙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砺其齿。(排调6)
王司州至吴兴印渚中看。叹曰:非唯使人情开涤,亦觉日月清朗。(言语81)
王恭始与王建武甚有情,后遇袁悦之间,遂致疑隙。然每至兴会,故有相思时。恭尝行散至京口谢堂,于时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恭目之曰:王大故自濯濯。(赏誉153)
以体道之心自处的周伯仁,自释瘦是因为“清虚日来,滓秽日去”,表明了一种玄心,代表对道家生存典范的倾心,因为道家认为“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19],“虚”也是道的品格,老子称:“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王弼注谓:“橐籥之中空洞,无情无为,故虚而不得穷屈,动而不可竭尽也。”[20]顾和给孙辈的一道设问,外孙张玄之与孙子顾敷的回答构成了语句与意思上的对应,当然顾敷能归因于“忘情”,富有玄心,不意小小年纪谈吐,与当时清谈中讨论圣人是否有情的玄学议题也起了关涉[21]。
袁羊对于执掌清谈牛耳的二谢心生钦佩,他对车武子烦劳二谢的担心加以慰释时,用了一组巧妙的对句:“何尝见明镜疲于屡照,清流惮于惠风!”既符合事理,同时也寓有对谢氏如“明镜”与“清流”般识度魅力的暗誉。
晋宋之时士人形成了以玄心赏咏山水的爱好,孙子荆对“枕石漱流”口误为“漱石枕流”的解释,虽属谐谑之言,可表对自然山水的亲近。而王胡之沉浸于吴兴印渚风景的审美感受,更表现出受到玄风洗礼后的妙赏。
在“王恭始與王建武甚有情”这一段记事中,“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既是王恭所寓目的风景,又引发了他内心情感的“开涤”,使他豁然化解了对故人的嫌隙。正是在破除了私愤之后,相思情深,心平如镜,他由衷地给予王建武一个品题:“王大故自濯濯。”“濯濯”是一种清朗如洗的风神,是魏晋风流之所尚,这一品题的呼之而出,不得不说是对应于大自然“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所带来的某种觉醒作用,使人荡涤情感障碍,拥抱超迈境界。这么说来,“清露晨流,新桐初引”两个工整的四言正对之句,好像“道生一,一生二”的孕生过程,带来充沛的原动力,引动了高朗超迈的“濯濯”之思。
刘勰注意到魏晋玄风影响于文学演进的事实,称“因谈余气,流成文体”[22]。以《世说新语》来考察,清谈的眼界、旨趣与方法等方面,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于文章对句表达的时代特色和修辞内涵,就此而言,可以看出刘勰的这个判断也是适用的。
三、“事对”与“反对”
《文心雕龙·丽辞》将对偶的类型总结为四种:“故丽辞之体,凡有四对: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23]对应于骈文创作上的举证,是相当有合理性的。兹从《世说新语》的对句表现,也可看出“事对”因难见巧、“反对”合力显优,从而印证刘勰的对偶理论。
“事对”意味着对历史典故或古人成语的随意驾驭,来为当下的语境服务,既需意思贴合,还求字句清丽。后来的文体理论家也有一些表述可资参照,如元代祝尧《古赋辩体》卷六《三国六朝体下》提到“用事”之忌是“为事所用”[24],清代程杲《四六丛话序》认为“以事对者尚典切,忌冗杂;尚清新,忌陈腐”[25]。从这些崇忌通则中也可感事对的难度。
邓艾口吃,语称艾艾。晋文王戏之曰:卿云艾艾,定是几艾?对曰:凤兮凤兮,故是一凤。(言语17)
蔡洪赴洛,洛中人问曰:幕府初开,群公辟命,求英奇于仄陋,采贤俊于岩穴。君吴楚之士,亡国之余,有何异才,而应斯举?蔡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于孟津之河;盈握之璧,不必采于昆仑之山。大禹生于东夷,文王生于西羌,圣贤所出,何必常处。昔武王伐纣,迁顽民于洛邑,得无诸君是其苗裔乎?(言语22)
邓艾与晋文王司马昭之间的对答,虽语出两人之间,但在字句上近于对句结构,“凤兮凤兮”是利用了楚狂接舆在孔子面前歌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云云,大约有以灵鸟拟人之意。邓艾并不是简单地推拒嘲讽之言,而是利用古事古语作算法,且不意间又隐将自己所落地步与圣贤孔子相联类,非常巧妙。吴楚之人蔡洪入洛后的地域人才论辩,其中引到了“大禹生于东夷,文王生于西羌”的古例,也增加了雄辩性。
刘琨虽隔阂寇戎,志存本朝,谓温峤曰:班彪识刘氏之复兴,马援知汉光之可辅。今晋阼虽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于河北,使卿延誉于江南。子其行乎?温曰:峤虽不敏,才非昔人,明公以桓、文之姿,建匡立之功,岂敢辞命!(言语35)
挚瞻曾作四郡太守、大将军户曹参军,复出作内史,年始二十九。尝别王敦,敦谓瞻曰:卿年未三十,已为万石,亦太早。瞻曰:方于将军,少为太早;比之甘罗,已为太老。(言语42)
殷仲堪当之荆州,王东亭问曰:德以居全为称,仁以不害物为名。方今宰牧华夏,处*戮之职,与本操将不乖乎?殷答曰:皋陶造刑辟之制,不为不贤;孔丘居司寇之任,未为不仁。(政事26)
苏峻时,孔群在横塘为匡术所逼。王丞相保存术,因众坐戏语,令术劝酒,以释横塘之憾,群答曰:德非孔子,厄同匡人……(方正36)
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言语70)
从三代贤圣到秦汉人物故事,都可以入对句用事。一般而言,用典隶事可以使言约意丰,意思婉转,有时也适当掩抑锋芒。刘琨以东汉班彪、马援明辨天命的事迹自励,引古自证,增强个人意志的合理性。摯瞻如此回复王敦,刘孝标引《挚氏世本》曰:“瞻高亮有气节,故以此答敦。”[26]甘罗为少年时,就在秦朝建功受封,载于《史记》,摯瞻用来抵驳刚愎自用的王敦,用古却不掩锋芒,尽显个性。魏晋名士喜以孔子的某些境遇自比,前举邓艾化解“艾艾几艾”的尴尬时,用到孔子生平中被质问“凤兮凤兮”的一幕;殷仲堪本具玄学素养(“本操”),但他在政事中未忘孔子为大司寇诛乱法大臣少正卯的故事;孔群在王导的酒席上,碰到从前使自己难堪的敌手匡术,恨心再燃,便说“德非孔子,厄同匡人”,用孔子在宋国厄于匡简子,来类比自己“厄”于匡术。两人恰好同姓,匡人之可鄙,尽在言中,而圣人有时也受制于小人,故其困厄遭遇也可聊慰常人。
所谓“反对为优”,往往更见缀言敷意的熔裁之功。刘勰为什么会提出“正对为劣,反对为优”的理论?或许应该与他担心“骈赘”之弊相关。相对来说,“正对”滥用就较易表现为“一意两出,义之骈枝也;同辞重出,文之肬赘也”[27]。而“反对”则通过对反概念或视野的矛盾统合,得到文义丰足无滥之境。这种对句的奇妙,有时巧夺天工,有如神来之语:
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言语55)
羊秉为抚军参军,少亡,有令誉。夏候孝若为之叙,极相赞悼。羊权为黄门侍郎,侍简文坐。帝问曰:夏候湛作《羊秉叙》,绝可想。是卿何物?有后不?权潸然对曰:亡伯令问夙彰,而无有继嗣。虽名播天听,然胤绝圣世。帝嗟慨久之。(言语65)
桓温感动千古的名句“木犹如此,人何以堪”,句构中的实词主体“木”与“人”,一为无情物,一为有情者,再加上助词对应,对比写来,富有抒情的魔力。后一例的“名播天听,胤绝圣世”强化出一种对比,名望无非身外虚誉,胤嗣却属血脉实传,羊秉如此表述,“善敷者辞殊而意显”(借用《文心雕龙·镕裁》语),将幸与不幸各表到极至而相映,产生了令人“嗟慨久之”的情感效果。
不可否认,“反对为优”的眼光历练,存在于清谈风气曼衍之中。名士社会在对人物或学风文格加以品鉴之际,往往通过有差异度的两人或两事合论,字句形成“反对”,在意味揭示上“情周而不繁,辞运而不滥”(借用《文心雕龙·镕裁》语)[28]。
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固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文学25)
孙兴公云:潘文烂若披锦,无处不善;陆文若排沙简金,往往见宝。(文学84)
孙兴公云:潘文浅而净,陆文深而芜。(文学89)
或问顾长康:君《筝赋》何如嵇康《琴赋》?顾曰:不赏者,作后出相遗;深识者,亦以高奇见贵。(文学98)
世称庾文康为丰年玉,穉恭为荒年谷。庾家论云是文康称“恭为康称恭为荒年谷,庾长仁为丰年玉”。(赏誉69)
时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怀,李安国颓唐如玉山之将崩。(容止4)
戴安道既厉操东山,而其兄欲建式遏之功。谢太傅曰:卿兄弟志业。何其太殊?曰:下官不堪其忧,家弟不改其乐。(栖逸12)
谢遏绝重其姊,张玄常称其妹,欲以敌之。有济尼者,并游张,谢二家。人问其优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风气。顾家妇清心玉映,自是闺房之秀。(贤媛30)
《世说新语》立有“品藻”篇,似专着意于作对比性的评鉴,如:
汝南陈仲举,颍川李元礼二人,共论其功德,不能定先后。蔡伯喈评之曰:陈仲举强于犯上,李元礼严于摄下。犯下难,摄下易。仲举遂在三君之下,元礼居八俊之上。(品藻1)
明帝问周伯仁:卿自谓何如庾元规?对曰:萧条方外,亮不如臣;从容廊庙,臣不如亮。(品藻22)
简文云:何平叔巧累于理,稽叔夜俊伤其道。(品藻31)
刘尹至王长史许清言,时苟子年十三,倚床边听。既去,问父曰:刘尹语何如尊?长吏曰:韶音令辞,不如我;往辄破的,胜我。(品藻48)
简文问孙兴公:袁羊何似?答曰:不知者不负其才;知之者无取其体。(品藻65)
有人问袁侍中曰:殷仲堪何如韩康伯?答曰:理义所得,优劣乃复未辨;然门庭萧寂,居然有名士风流,殷不及韩。故殷作诔云:荆门昼掩,闲庭晏然。(品藻81)
桓玄为太傅,太会,朝臣毕集。坐裁竟,问王桢之曰:我何如卿第七叔?于时宾客为之咽气。王徐徐答曰:亡叔是一时之标,公是千载之英。(品藻86)
多例可见,人物品评之风炽盛,当时在名士间喜欢发出的问题是,某甲何如某乙?这样的两厢评鉴比照而出,怎样才能语简意丰?怎样才能警悟动人?在此调动“反对”的修辞力量,正是耐人寻味的。《世说新语·品藻》中还有一条:“王夷甫以王东海比乐令,故王中郎作碑云:‘当时标榜,为乐广之俪。’”两名士组成了俪偶之目,载入碑文,刻石长存。另外,《贤媛》篇载:“王浑妻钟氏生女令淑,武子为妹求简美对而未得。”佳耦美对存在于生活与人们的向往中,在清谈时代有其富有内涵的时代自觉。总之,《世说新语》中丰富的对句之美,有其哲学与时风底蕴,有其语言修辞上的天成与琢炼。
文/曹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