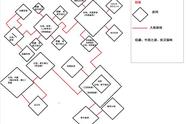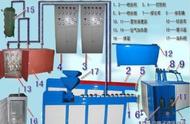《钦天之剑》——京味儿民国风科幻小说
这是一个在并未存在过的年代中,一群从来没出现过的人的故事。
初升的朝阳,把阳光揉进茂密的白桦林里,让树皮上的“眼睛”更加醒目,晨鸟的叫声给这片缈无人迹的广袤树林更添了几分幽静。趟过树林间马腿高的野草,在远东西伯利亚树林里的这个五人小队已经前行了一整夜,幸好队伍里大都是生龙活虎的年轻人,此时尚未露出疲态。
唯一的一位中年人在队伍的最前面带路,他骑在马上,腰杆挺直,手里握着一个半块砖头大的黑色仪表,每前进十来分钟,就看一下仪表盘上指针的读数,再对照指南针,用手势示意,调整整个队伍的前进方向。
在队伍最后压阵的一个队员,双腿一拱,驱马向前赶了几步,在越过驮马的时候顺手拿了一皮袋酸马奶子,赶到队伍前和中年人并驾齐驱。
“歇一会儿吧,队长。”
“不行!”中年人摇摇头,双眼通红,就像是烧着一团火,“要快,再快点。已经太迟了……”
在日俄战争获胜之后,日本的国势一日千里,老对手阴阳寮的气焰也开始嚣张起来。而内忧外患的中国,却像一辆破旧的大车,在历史的轨迹上吱吱嘎嘎地缓慢前行。
这个行动小队所属的那个神秘组织,即便拥有远超各国同类的底蕴,此时也只能坐在这辆破车上干着急。
这个时候不能休息,也不敢休息。
“马快吃不消了。”年轻人把手里的皮袋递给队长,另一只手握拳,用大拇指向身后指了指。
队长侧头看了看身后的马队,队员们的身体状况还能硬撑,但马匹的疲态却无论如何也掩盖不住。在这样荒凉空旷的荒原和密林里,失去马匹只会更慢,总不能真的靠肩扛手提来赶路。
他无奈地掏出怀表看了一下时间,举起手指着前面不远处一块林间空地,示意大家去那边下马暂歇。然后接过皮袋皱着眉头灌了一大口,递还给那个年轻人。年轻人松了口气,拨转马头去照顾后面的兄弟们。
这片空地中间有块半人高的巨石,所有人跳下马,十分熟练地从马鞍后面摘下料袋,挂在马耳朵上。
队长爱怜地拍了拍马头,回身吩咐:“不摘行李,检查一下装备,我们只歇一刻钟,吃点东西继续前进。”
队员们有条不紊地忙碌起来,有的检查驮马身上的装备,有的拿下毯子铺在石头边上,抓紧时间休息,有人取出干粮分发放给众人。队长接过干粮,叼在嘴里,拿着仪器爬上巨石顶部,在随身的笔记本上记录着数据。
年轻人背靠着大石头坐下,眯着眼睛养神。这时候队伍里年纪最小的栓子凑过来小声说道:“我出来之前,听司里的人说,在所有外勤队伍里,咱们队长本事最大。大帅你跟队长的时间最长,你给说说?”
“说说?”外号叫大帅的年轻人半眯着眼睛,声音懒散,仿佛马上就要瞌睡过去,“队长是留过洋,喝过洋墨水的。年前我们俩去上海租界,那里面大鼻子蓝眼睛的洋人都服他,那洋文说的,连个磕巴都不打。”
“那咱们队长的本事不能只是会说洋文吧?还有没有别的?听说俩月前汉口那档子事儿,都是咱们队长力挽狂澜?”
大帅一撇嘴,得意劲儿几乎满溢出来:“要不是咱们队长处置及时,半个汉口都得完蛋!”
栓子挠挠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大帅你是知道的,俺跟你们不一样。你们都是打小儿学本事,喝了好几年墨水才出来历练差事。俺是半途被队长捡进司里来的……所以之前上课的时候,教员讲的东西好多搞不懂,他们说的那个‘平行世界’还什么‘空间’到底是怎么个来路?遇到事儿具体该怎么办,那俺是懂的,但就那啥啥理论的,俺实在是闹不明白。”
大帅直起身,看了看在巨石顶部忙碌的队长,一时半会还没有结束的意思,想了一下说道:“我记得栓子你挺喜欢去咱们分部边上那个茶馆里听评书,出来前说书的讲《封神榜》,里面有一段说‘三千世界’的你还记得吧?司里教员说的平行空间,就是指这个三千世界,也就是说,除了咱们自己待着的这个以外,还有很多世界。”
“你这么一说俺就明白了!”栓子咂了咂舌,“那其他空间里面,还不得住的都是神仙老佛爷?就凭咱们,把他们下凡过来的大门给堵上,行吗?干得过吗?”
大帅给气乐了:“我说你小子,平时教员给你上课的时候全都睡过去了吧?哪有什么神仙老佛爷。我跟着队长闯过这么多事儿,平行空间也见识过不少,连根神仙毛都没遇到过!”
“那……”栓子带着几分羡慕地指了指大帅的衣兜,“没老神仙的话,你那个宝贝怎么回事儿?”
大帅得意地拍了拍衣兜:“这叫科学物品!什么宝贝,别露怯啦,你小子进司里那会儿,看见电灯泡子的时候还奇怪为什么吹不灭呢,那不也是‘宝贝’?”
大帅的话引得其他两个队员低声笑了起来,栓子也闹了个大红脸:“俺那不是不懂吗?不懂俺这不是来问了吗?”
大帅听到这话,脸一沉正色道:“是,你说得对,是我不好,不该笑你。”
栓子倒是被他这个态度搞得有点慌:“别……俺不是那个意思……”
大帅笑了,拍了拍栓子的肩膀:“等回头咱们这趟差事做完,你也算见识过平行世界的人了。等你见识过就知道,在那些世界里面,没人烟的蛮荒占了绝大多数,就算是有文明世界,活在里面的也是和咱们差不多的人,饿了要吃,枪打了会死,科学比咱们昌明的世界有,不如咱们的也多的是。但无论咋样,只要俩世界连接上,基本就能肯定要有大灾大难了。所以我们要做的事儿,就是断绝这种连接!生死不计,百折不悔!”
“生死不计,百折不悔!”听到最后八个字的司训,其他三个人都跟着低沉地复述了一遍。想起自己曾经亲历过的异象惨景,和曾经的战友们为维护太平,前仆后继的牺牲,脸上不禁显露出坚毅的神色。
“休息够了吧?继续出发!目标离着不远了。”石头上传来队长的声音。
众人迅速起身,收拾好东西继续前进。
在西伯利亚的荒原上,俄罗斯人用唾手可得的原木建造了绵延数里的木栅,把三座高耸的铁塔仔细地保护在营地当中。木栅上安装了不计其数的电灯,木栅上每隔一段就有个高高的木制望楼,下边还有牵狗带枪的守卫不停巡逻。
在高纬度夏季短如昙花的黑夜中,一片雪亮灯光将木栅周围照得亮如白昼,几乎可以媲美几年前的巴黎世界博览会。巡逻队和望楼守卫的口令对答声不绝于耳。从这一切布置中可以看出,即便几年前战争的失败大大伤了俄国人的元气,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这些俄国熊的行动力仍然十分可观。
木栅不远处,夜色掩映的密林里,队长把手中的怀表扔给大帅:“抓紧时间休息,早7时发起突袭。”
“要不要改个日子,等过几天夜长一点再动手?”大帅问,队长刀锋一样的目光马上扫了过来。
“不行,侵蚀读数一直在上升,而且阴阳寮的家伙就跟在咱们后面。要是被他们得了手,那就一步迟步步迟了!”看着队员们疲累的神色,队长叹了一口气,“不能等了,那三座高塔明显已经快要发动,计量器显示有强大的能量正在聚集,之前咱们得到消息的时候就已经晚了,不能再等下去,真要是被俄国人鲁莽地击穿空间屏障……”
“队长,快看!”大帅突然指着队长身后的高塔喊道。
三道白亮的闪电正徐徐从高塔上升起。
“突击!”队长反应过来,大喝一声,拔出毛瑟手枪,扑向木栅。
栓子举起麦德森机步枪,紧跟大帅,打出一个又一个短促而准确的点射,把试图阻拦众人的俄罗斯守卫一个又一个扫倒在地。在他身后,其他人背负炸药沿着刚刚打开的血路冲向高塔。
1908年6月30日晨,西伯利亚通古斯地区发生不明原因的大爆炸。亮度与太阳相当的巨大火球划过天空,冲击波将2000多平方公里内的8000万棵树木焚化殆尽,直到爆炸发生的几天后,亚洲与欧洲的夜空依然呈现诡异的暗红色。
全世界只有很少的人,才知道那天发生过什么事情。
………………………………
时间到了公元1928年的年底。
自打八国联军闹了北京城,造下好大*孽之后,已经过了快三十年。
可北京城元气一直没彻底恢复过来。再等到宣统皇帝逊位,在四九城里张扬了两百多年的旗人们倒了铁杆庄稼,北京更是显出几分破败萧瑟之意。现如今不再是首都,连名字都改叫了北平,越发地一天不如一天了。
但对于坐地虎魏七爷来说,这二十多年可是遇上了好时候。
他是打庚子年之前就跟着师父学艺。等拳民们闹起来的时候,师父热血上头带着几个师哥跟着拳民们去围东交民巷。仗着会几手功夫冲在最前面,结果几个师兄全都死了,只有师父带伤逃得了性命。
把师父的伤伺候好之后,魏七爷就从一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小徒弟,升格成了最得宠的大弟子,因此,师父叫上几个有字号的长辈,给他贺了个号叫坐地虎。
等到师父归天,这一门上下,连房子带人就都归了魏七。镇九城那不敢说,起码在东城这一片儿,提起坐地虎魏七爷来,也算是个响当当的人物。鼎盛时期,就连官面儿上想要平事儿,也得拎一匣子正明斋的点心上门来打个招呼。
这几年虽说世道不好,但总算祖师爷赏饭,日子还过得下去。魏七爷也没什么雄心壮志,只图不招灾不惹祸,把日子过好就行。因此上甚是知足。
一早上起来,练过了功夫——这是吃饭的能耐,不能丢——就有身边伺候的徒弟给端来温度正好的三窨茉莉花茶,魏七爷大马金刀威风凛凛地坐在堂屋的太师椅上,手里搓着两颗铁胆,看那日影慢慢爬上窗户纸,把窗棂的影子投在堂屋的地上。
喝着茶,跟着唱片机里折子戏的板眼摇头晃脑,好一副悠闲自得的做派。
后院里妻妾儿女们的鸡飞狗跳,或者前院里徒弟练功挨打的鬼哭狼嚎,他浑然不放在心上。人过四十,魏七爷是愈发的洗练火气,雍容自在起来。
眼看日影渐高,到了该听话匣子的时候,前院里忽然乱了起来。有人高声喝问,紧接着是哄然一片的嘈杂,似乎是来了什么不该来的人。没等魏七爷发话,只听腾腾腾脚步声响,有人快步走到堂屋门口,站在门外语气里带着七分火气和三分不屑道:“师父,管片儿姓宋的那小子来了,指名道姓要见您。”
还行,知道站门外头说话,没慌慌张张往屋里闯,还算懂规矩。说话的是大弟子杨歪脖儿,自打出手失风被人打歪了脖子,就一直替魏七爷管着前院。
能这么懂礼数,魏七爷非常欣慰,但说的事儿让魏七爷感到迷惑,扭头瞅了瞅墙上挂的黄历,今天既不是初一也不是十五,还没到交例钱的时候。
姓宋那小子大名儿单一个斌字,是警局老石手底下顶顶机灵的一个,左邻右舍都知道,老石是拿他当亲儿子看的。没到日子口儿上门,这叫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现在不比头两年,要小心应付。
俗话说虎死不倒威,魏七爷自是不能怕了个小毛孩子,但不知为什么就觉得有点心慌。他把歪脖儿叫进屋来,再把家里能顶事的弟子们都叫齐,拿出精气神儿分列左右。
有徒弟们站脚助威,魏七爷心里踏实了不少,理了理身上的大褂,调整了一下表情,这才开口道:“传进来!”
话音刚落,就听外头脚步声响,一个身材高挑的年轻人一挑棉布门帘,走进堂屋。
此人身高在五尺六寸上下,穿青挂皂,一身黑色警服浆得笔挺,头上戴着大檐帽,黑漆帽檐光可照人,帽圈儿刷得雪白,里面衬了竹篾浑圆绷紧,不像一般巡警那样又皱又塌。腰上扎着牛皮带三指多宽,铜带扣擦得锃光瓦亮。往脸上看,双眉斜挑,眼角微扬,唇边仿佛总是带着一丝笑意。
魏七爷一眼瞥到来人之后,迅速耷拉下眼皮盖住自己的神色,拉长了腔儿慢声问道:“我说宋巡长,不年不节,又没赶上初一十五,你上我这儿来难道是拿人的吗?”
宋斌见他一不见礼二不看座,也不以为忤,向着魏七爷一抱拳,自己施施然走过去往下手椅子上一坐,腰杆儿挺得笔直:“街里街坊的,我就非得有公事才能上您这儿来?就不能是找您办私事?”
听说是私事,魏七爷假装没注意到宋斌不请自坐,破了自己的下马威,一挑眉毛道:“哦?你宋巡长能找我有私事?说来听听。”
宋斌环顾左右,道:“敢请七爷屏退左右,我才好说这个私事。”他把“私事”俩字咬得很重。
魏七爷却不吃他这一套,摆一摆手道:“这儿没外人。”这话,既是跟弟子们显示亲近,又是在向宋斌示威。
宋斌淡然一笑:“那成,这是您自己说的。”
这话让魏七爷一个激灵,觉得自己可能掉进宋斌挖的坑里了。可话已出口,再想改也来不及了,只能硬着头皮道:“不错!”
“您把欠我的钱还了吧。二十块大洋,镚子儿不能少。”宋斌往太师椅背上一靠,翘起二郎腿。
魏七爷气得笑了出来,道:“我说斌子,七爷我好歹也是眼瞅着你长大的,叫你一声侄儿,不算占你便宜。马叔的家教真没得说,你们这帮孩子连撒谎都不会,瞎编都不知道编点儿别人能信的事儿……”说到这儿,魏七爷对着宋斌倾过身子,左手握拳伸出大拇指一指自己鼻子,“我欠你的钱?这话说出来你自己信吗?还二十块大洋,你小子长这么大,见过那么多钱放一块儿吗?”
人群后排,刚还在前院里开水盆中用食中二指夹肥皂片儿的小徒弟,拿毛巾擦着手问身边的师兄:“来的这位谁啊?这么大口气也不怕闪了自己舌头?”
师兄用嘴角嘘了一声,小声给这个新来没几天的同门解释——
魏七爷提起的马叔,大号叫马叔牟,头几年人还在的时候,跟北新桥附近的方家胡同里开了个“孩儿店”,带着一帮捡来的孤儿讨生活。当时的北京城里,类似的“孩儿店”很是有几处,多数是由一两个地痞控制起来盘剥孤儿的地方,可马叔牟开的这家孩儿店跟其他的又有不同。
1900年庚子国变之后,八国联军在北京城滥*无辜,好多孩子成了孤儿。马叔牟从那时候起就开始收养孤儿,一直干了十几年。立店之时就有五十开外的年纪,孩子们当面管他叫马爷爷,背后都管他叫马老头儿。
马老爷子年轻时干过什么,孤儿们不知道。只知道他手头没多有少趁几个闲钱,够盘下一个院子给孩子们住,给孩子们饭吃的。赶着每月初一十五,还能请先生来教孩子们认几个字。每到开课这天,老爷子就在院子里枣树下的青石条前,摆个小桌子,笑呵呵地听着孩子念书的声音喝茶。
等这些小胡同串子们长大了,马老爷子还会给其中聪明机灵的张罗个差事。虽说平时也会让孩子们些干杂活儿来贴补店里的开销,但跟其他孩儿店相比,已经算是极其厚道的地方了。
等大清国亡了之后,跟这世道一样,马老爷子的日子也是一天不如一天,青石条前小桌子上茶壶里的茶,从双窨的茉莉花儿变成了高碎。最后请不起先生,马老爷子就挽起袖子自己教,在越来越纷攘的乱世中,努力地让孩子们别冻着饿着,再多学会几个字,好歹懂点这世间的道理。
宋斌差不多就是在那个时候被马老爷子收养的。
宋斌的爹娘都是北京人,老爹来往于京城和口外之间做买卖,手底下很是趁几把骆驼(注:骆驼专用的量词,一把为七只),年轻时去张家口置了家业,所以宋斌小时候是在张家口长大的。6岁那年,他爹外出行商一去不归,渺无音讯。他娘苦苦等了两年,把家当变卖光之后只好带着孩子回了娘家。结果次年,也就是辛亥革命那年也病死了。9岁的宋斌受不了舅妈在家摔盆打碗指桑骂槐,一怒之下离家出走,饿倒在北新桥十字路口旱桥的桥头,亏的是马爷爷捡回他的一条小命。
因此上,宋斌把马老爷子当成是自己的亲爷爷。
可这好日子也没过多久,1917年,张勋复辟,北京城闹辫子兵。赶上马老爷子上街给店里一个生病的女孩子——小名儿叫做大妞儿的——抓药,躲慢了,被辫子兵照后背上一枪托砸吐了血。回到家里没熬几天就撒手人寰。人临走的时候,拉着宋斌的手,哆里哆嗦指着屋里屋外的孩子们,一句话没说出来就过去了。
宋斌坚信,老爷子临死想说的是——让自己把孩子们照顾好。那年十五岁的他,从此就背起了这一大“家”的重担。
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宋斌十五岁,按说不算小。可他这个穷人家跟别人还不一样,他再能干,也没能耐养活这么一院子比他还小的孩子啊。
没熬几天,就逼得他把主意打到歪道儿上去了。结果上街第一次伸手掏包,就让苦主摁了个正着。那人是个报社记者,姓何,看着是个白白净净的读书人,可手底下竟然有两下子功夫。拧着宋斌的膀子就交给了正在街上当班的石巡长。
可等石巡长问清楚宋斌是为养活一帮孤儿才做的贼,就不想难为他了。再知道这小崽子还识几个字,更是动了怜才的心。干脆带着他去何记者的宅门口跪了一天一夜,求着何记者撤了案,最后还收宋斌做了徒弟。靠着师父的接济,靠着自己每个月的月饷,靠着当年才六岁的大妞儿,背着她亲弟弟小青子,带着一众大小崽子们糊洋火盒,这个家硬是撑了下来。
这么多年下来,石巡长升了石警长,管着一个巡警局。宋斌自己也成了巡长。当年的孩子里,有孩子长成了人,离开他们自己出去讨生活,也有倒霉没养住的,还有从外边捡回来的新人。总算没有辜负马老头儿当年的托付。
到现在,马老头在世时收养的那些孩子,还住在一块儿的,除了宋斌之外就只剩下了姐弟俩。姐姐大妞今年18,弟弟小青子今年13。
大妞没离开那是为了宋斌,这事儿宋斌心里明镜儿似的。可就算穷人家结婚,起码也得请上一棚执事,开几桌流水席叫上左邻右舍热闹一番吧。但有这一大家子拖累,怎么也攒不下钱来,所以俩人的感情那是两情相悦,心照不宣,但最后那一步始终没敢往前走。
如今听魏七爷提起马老爷子,宋斌眼睛里的光芒暗了一霎,随即脸一扬道:“你提起我们家的事,那还真就提对了。我且问你一句,我想娶大妞儿,一直攒不出请执事的钱来。这个事儿你知道吧?”
这话说的没头没尾,定然有圈套,魏七爷心思电转,表面上丁点儿看不出来,只是点头:“这个街里街坊的谁不知道?”
宋斌放下二郎腿,双手一拍:“着啊。所以七爷您欠着我钱。”
魏七爷是真有点上火了,手里一直转的铁胆都停了下来,声音里也带上了怒气:“斌子,刚才我说的明白,指着马叔那边儿论,我魏七当你是个晚辈。当年要不是机缘巧合,让你师父石警长先捡到你,没准你就要投在我的门下。既然没有这个师徒的缘分,今天七爷也不想拿大辈儿压你,可这人说话做事得讲道理。你自己做梦想娶媳妇儿,凭什么是我欠你的钱?”
这一片儿的人都知道,魏七爷这对铁胆十步之内百发百中,跟手里一直转着也就罢了,一旦不转就是起了动手的心。站在左右两排的徒弟之中,有跟宋斌相熟的,这会儿都替他捏了把汗。
宋斌却毫不在乎,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个黑皮小本本:“前些天,酱坊东夹道胡大老爷坐洋车回家,半路上让人摸走了皮包。做贼偷钱,在北平城里每天没有一百也有五十,本来不算个事儿,但胡大老爷包里还有重要文件,结果这个包让贼扔到了厕所里头,钱丢了也就算了,文件全毁这是哪家的规矩?
“胡大老爷急火攻心回家就躺下了,转天儿悬赏二十大洋要抓这个贼。我已经查问清楚,做下这缺德事儿的人,就是你徒弟鸡屎。这赏钱要拿人去换,七爷您今天要是交人也就罢了,要是不交,那不就是欠了我二十块大洋吗?”
这话当众往外这么一说,把魏七爷一口气憋在胸口,上也上不去是下也下不来。
没错,东城的坐地虎魏七爷*就是做贼的买卖。
宋斌是如假包换的警察,虽说警匪一家是满天下都认可的规矩,可只要理由充分,警察上贼窝里要贼,魏七爷没有发作的道理。但被个小毛孩子三言两语就这么把人交出去,魏七爷颜面何存?坐地虎的名号要是栽了,以后七爷在地面儿上可就不好混了。
想到此处,他扫了一眼戳在墙角、跟个盆景似的三道弯、没一点儿正形、不到三十岁就有点谢顶的鸡屎,心里暗骂这小子没事给自己找事。然后眼珠一转咳嗽一声:“话不是这么说的。凭什么那二十块大洋就是你的呀?要是我自家把鸡屎捆上送到胡老爷家去,那这钱他是不是该给我呀?”
七爷这叫以进为退,想着拿话把宋斌套住,起码眼前不能就这么让宋斌把鸡屎带走,先把自己的面子保住。至于出了这个门宋斌还抓不抓鸡屎,那倒与他坐地虎的面子就没多大关系了。
却不料宋斌微微一笑:“对。我知道你魏七爷干得出捆自己徒弟换赏钱的事来,你们家没规矩,不讲究。要不然我也不能堵门口儿跟你要这个钱。”
这话可戳到了七爷的肺管子,把他气得将铁胆交到左手上,右手抡圆巴掌重重一拍桌案,把茶碗都震躺下了,喷香的茉莉花茶流了一桌子,看得旁边的小徒弟直心疼。
其实魏七爷也心疼,这一巴掌把茶叶都洒出来不少,下午想喝还得重新泡。这可是好茶,一撮茶叶要一毛多钱,都够手下的记名徒弟一两天嚼谷了。但宋斌话头儿顶在那边,他这会儿没工夫在意这个,怒气冲冲地回手冲堂上挂的东方朔画像一抱拳:“祖师爷在上,我坐地虎是做贼的不假,可我魏七这一门是有传授的,三百六十行之一!不是野路子,不是下三滥!你个小毛孩子别血口喷人!谁没规矩了?谁不讲究了?”
宋斌见他发怒,也不慌张,反问道:“那请问魏七爷,照道上的规矩,得了胡大老爷皮包应该只取钱财,外面的包要扔回原处,对吧?给人家扔到茅房粪坑里,算是谁传授的哪门子规矩?!”说到最后一句,宋斌也运上了气,几个字声振屋瓦,气势一点也不比魏七爷差。
这话问得魏七爷一愣,刚想开口反驳,宋斌又道:“据我所知,您这个行当讲究三不偷五不取。内中有一条是不能偷人家救命钱。是也不是?”
“那又如何?”
宋斌道:“那你问问鸡屎,三天前协和医院门口有个当妈的,抱着得急病的孩子上医院看病。就在医院门口,钱包让人给摸走了。这事又是谁*?”
偷了包裹取完钱财要扔回原处,那是怕包里有要紧的东西,避免事主为找回东西下死力抓贼。是规矩,但不是什么禁忌,做贼的自保之术罢了。可偷人救命钱那就大不一样了,这叫有伤天和,是行里的大忌讳!出来混江湖的人谁不迷信?得罪上天那是要遗害同门的!
一般来说,谁身上的哪笔钱是救命使的,做贼的自己也搞不清,师父教手艺的时候是有察言观色这一科,但应景儿也可以推说不知道,不知者不怪嘛。
可选在医院的门口下手,对方还带着个得病的孩子,就没法拿这话搪塞了。要是传扬出去,别说鸡屎,连坐地虎魏老七在内,整整一个门派都得脸上无光。要是野路子的贼窝真就罢了,可七爷这一门在江湖上也是有名号的,道上的大佬三节两寿有他一张帖子。要是因为这事儿被人指脊梁骨,成了不懂规矩的下三滥,那他在北平城的江湖道上,就再也抬不起头来了。
宋斌这话一出,整个堂屋里所有人都转头盯着鸡屎,看他如何作答。
鸡屎从宋斌进屋的时候,就把自己往墙角里塞,这会儿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哆哆嗦嗦往前一步,那手抖得跟弹弦子似的,点指宋斌道:“你……”
屋内众人还以为他要为自己分辨,都等着听。不想他这一下是虚晃一招,一个字说完,横肩撞开身边两个师兄弟,撒腿就要往院子里逃。
众人没料到他闹这出,连一直紧绷着弦儿的宋斌在内都是一愣。眼看鸡屎趁众人愣神的功夫已经冲到门口,弯腰伸头去顶门帘。却见魏七爷手一抬,白光闪过,一颗铁胆正中鸡屎的脚踝。鸡屎吃痛,“哎呀”了一声栽倒在当地。杨歪脖和另外两个师兄弟扑上前去,将他按住。魏七爷做个手势,就有人递过去绳索,杨歪脖儿手底下利索,扭肩头拢二臂将鸡屎捆了,又拿麻核把嘴也塞上——这是规矩,防着他在去警局的路上胡说让街坊听到——交给宋斌。
宋斌蹭楞一下站起来,冲屋里人团团一抱拳,不等一屋子大小贼还礼,接过绳头,拉着鸡屎转身出门。
魏七爷却又开口道:“斌子,咱可把话说明白了。一来,鸡屎是坏了门中的规矩才交给你,回头医院那边的事儿你给个人名地址,该多少是多少,那钱七爷我还给她。二来,胡大老爷那边的赏钱,算你娶大妞儿七爷我给你随的份子。除此二事之外,你可不能往鸡屎身上再安别的罪过!”
这是场面话,宋斌当然明白。人家把人交给自己了,自己自然也得给人家留面子,点头道:“你放心魏七爷。所谓冤有头债有主,我宋斌做警察也是有师父的,规矩就是规矩,不乱给人栽南瓜秧子。”说罢带着鸡屎出门,留下魏七爷坐屋里运气。
院门外不远处一辆马车里,有人目送宋斌押着鸡屎离开,轻声道:“孤身闯贼窝,能平平安安拿了人离开。这小子有点儿门道啊。”
旁边有人问:“孙哥,那咱们要不要……”
先前说话那人摇头道:“再等等,咱们刚安顿下来,这几天琐碎事多,过些日子再说。”
两人正说话间,几个老太太从车边经过,每人手里都拿着瓷碗,拎着布口袋。前边走的两位是天足,健步如飞。后边还有几位裹着小脚的,气喘吁吁地跟着:“塔大姐,您别走那么快,我们老姐儿几个跟不上。”
前头一个老太太连头都没回:“快着点儿吧,老姐姐。马坛主传下的法帖儿,今儿个无生老母显圣,去的人除了给符水,一人还赐半斤杂合面儿,去得早还有鸡蛋哪。眼瞅着午时三刻就要开坛,去晚了鸡蛋可就没啦。”
后头一个老太太道:“我都不盼着鸡蛋了,杂合面儿真给吗?这做完晌午饭都没顾上吃一口就跑出来了,要是空手回去,我们当家的又得数落我。”
“给,人家真给,上次我就拿着啦。马坛主说啦,无生老母可是白莲正神,关外那帮人信的歪脖老母都是骗人的。无生老母不一样,只要是怹老人家许下的东西那就真有。您快着点儿吧。”
几个老太太前呼后拥地去了。
车中的两人听得直皱眉。年轻无须的那人就问:“孙队长。北面的白莲教好像很活跃啊,南边被咱们给剿得就剩半口气了。这都已经公然施符水、散好处招揽外围信众了。咱们要不要查一查?”
孙队长摇头道:“明面上的这些白莲都是招些愚夫愚妇下钩骗钱的外围,跟咱们剿的那些不是一回事。”顿了顿,又道,“不过,你说得对,南北方形势不一样,也不能完全放着他们不管。但这事现在不急,等把眼前的坎儿过了,再下功夫查一查。”
说着伸手拍拍车把式肩膀,示意他驾车离开。车把式抖了抖缰绳,轻轻抖了个鞭花,两匹健马打了个响鼻,喷出一尺多长的白气,大车起步混入人流。
马车在人流中缓慢前进,那个孙队长刚说要眯起眼睛歇一会儿,就听见有个报童远远地喊:“卖报卖报。四个大子儿一份,七个大子儿两份。《燕京时报》:傅斯年发掘安阳殷墟,得有字甲骨八佰片。《京津泰晤士报》:北平再现猿人遗迹,瑞丁大儒安特生回到他心爱的鸡骨山。”
孙队长听到最后一句,似有所感,道:“小刘,你去买份报纸。”
小刘奇道:“队长,您还有心思看这些小报?”
孙队长道:“你没听见‘鸡骨山’这几个字么?回去让小胡查查档案,看是不是明字壬戌二百七十六号档里记的那个地方。”
小刘一脸惊讶和钦佩:“您听个地名就能记起档案编号来?太厉害啦。”
孙队长一笑:“马屁差不多就得了啊。前些年司里让我查过这个档案,跟一件要紧的东西有关。那是我入职的第一个差事,所以有印象,年头多了也不知道记差没有。马上就是侵蚀高峰期,这会儿是牵一发动全身的时候,可不敢漏掉相关的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