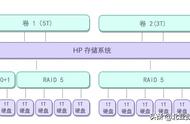既不俯视也不仰视,既不冷漠也不过分热情。《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的书写者姿态更像是借住在某个大杂院里的单身青年又或者是胡同口摆摊的大爷,默默观察着蓑衣胡同13号里发生的一切。他们的苦乐哀愁似乎和我们毫无关系,却又真实地像发生在自己身上一样。
文|李初晴编辑|糖槭
「当时我就笑疯了」
2000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剧版(以下简称《张大民》)初登荧屏时,仅比影版《没事偷着乐》晚上映一年,二者都改编自刘恒的原著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按现在的IP改编规律而言,两部作品时间上连接太过紧密,珠玉在前,难免会让人做比较,而后者总归吃亏一些。
剧版开播不久,就有声音认为,电视剧改成了「又臭又长的裹脚布」,「津味儿贫」变成了「京味儿贫」从而失了原著的精髓,甚至开始「就贫说贫」,将主人公塑造成了一位「城市流氓无产者」。
20年过去,这种说法已基本偃旗息鼓。作为新千年的开篇之作,其在北京电视台的收视率一路攀升至70%,几乎拿完了当年所有能拿的电视剧奖项,同名原著小说由于电视剧的热播再次卖到脱销。
当年有记者走访花市、王府井、西四的几家新华书店,却仅在西单图书大厦找到了几本被紧急调运来售卖、身披「1999兔年贺岁」宣传标志的单行本。由于原著小说仅7万字,出版商不得不放大字体和行距,才勉强符合发行售卖的需求。
导演沈好放同样沉迷于原著笔锋锐利而不失诙谐的对白。1998年,他收到老友的推荐,一口气在招待所的厕所里读完了整篇小说,「当时我就笑疯了。」更没想到的是,就在这天下午,北京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的主任再次向他推荐了同本书。一拍即合,沈爽利表示,「这戏我来拍吧。谁来改本?」得到答复是刘恒亲自操刀。只花了不到一天时间,这部戏就被快速敲定下来——这种情况放到今天来似乎不能想象。
尽管如此,在本剧的「灵魂人物」张大民的角色问题上,导演与资方仍产生过较大的分歧。1997年,沈好放与梁冠华刚合作完由老舍小说改编的家庭言情剧《二马》,两人对彼此印象都还不错。开拍前,沈向资方力荐梁担纲新剧主演,不料却在半夜两点,接到资方打来的电话 ——「沈导,换人吧,太胖了。」在导演的坚持下,「只适合演地主」的梁冠华一个月内成功减肥30斤——尽管依旧与冯巩先行带来的公众形象相差甚远,仍算是坎坷着争取到了人生中第一个荧幕主角。
后来的观众感叹剧中的角色「无论主配演,都像沿着演员模子刻出来的一样严丝合缝」。一级表演艺术家徐秀林饰演操劳一生后患阿尔兹海默症的母亲;后被称作「娶妻当娶李云芳」的老大媳妇由朱媛媛饰演;话剧经验丰富的赵倩和鲍大志则分别扮演伶牙利嘴的「北京大妞」大雨和窝囊没出息的三弟大军的角色;1998年开拍当时,刚满18岁「嫩得可以掐出水」的霍思燕则饰演命运凄惨的老四大雪;家中唯一的大学生大国的饰演者王同辉当年也在备考北电的表演系硕士。
回过头来看,《张大民》的成功几乎是注定的。刘恒精准老练的平民派语言功底,早年留学东京深受小津安二郎生活叙事影响的沈好放,以及大量采用「人艺班底」的演员阵容——剧中动辄十几分钟,大段的长镜头段落都对演员的台词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共同决定了最终呈现的品质。2020年,没有人再质疑这部剧的表达水平及其本身的艺术价值,豆瓣讨论区涌现出坐等该剧涨到9.0的声音。
平民式的英雄就此胜利了?被公认的是,此后再难在荧屏上看到如此动人温情的生活剧了。张大民一家像是刚迎着新千年的钟声走近我们,又立马淹没进时代的洪流里日行渐远了。或许诚如沈好放所言,「张大民是时代的产物,放在今天来个第二季也没有办法超越。」
既不俯视也不仰视,既不冷漠也不过分热情。《张大民》的书写者姿态更像是借住在某个大杂院里的单身青年又或者是胡同口摆摊的大爷,默默观察着蓑衣胡同13号里发生的一切。他们的苦乐哀愁似乎和我们毫无关系,却又真实地像发生在自己身上一样。
当我们站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回望它,仍能发现其中难能可贵的人性的、爱的光芒。那是关于「贫」的艺术,生活的艺术。

世俗的力量
张大民的「贫」得到过人民群众的「盖章」。在b站上重温该剧,会发现凡是大民说话的片段上,总能飘过一片「他是真贫啊」的弹幕。
第一集结尾,一起长大的李云芳被甩后闹到都寻死觅活了,大民非扯到小时候看的《地道战》,还要抓着人家一块挖地雷。住房问题反映到厂里无望,当面揭穿师傅私吞了一居室,岂料对方借口「我是正科级呀」反驳,他气急之下又开始「贫」,「唉呀师傅呀,瞧把您给逼的,这么寒碜的话都说出来了!您再占着茅坑不拉屎,我就直接把马桶挪到您椅子下边!」
张大民属于典型的贫民加贫嘴,遇上谁都能逗上两句。可另一方面,这种「贫」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好处。调侃完师傅,他回到家里蹲在屋檐下继续惆怅。
大民被困在生活的高墙中无处翻身,只能用安贫乐道,小富即安的思想聊以自慰。这种人物形象在当时引发了文学界和剧作界的争议。
2000年,文化批评家解玺璋抨击《张大民》是「对现实的妥协和投机」。
「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在不幸中寻找幸福。忽略幸福的物质性而把精神绝对化。」对于观众津津乐道的「知足常乐」,他反问「正义和人的尊严是不是早就被我们抛到爪哇国去了?」
面对上世纪末社会急速世俗化的过程,解玺璋在其间看到的,是1990年代以来整个社会群体精神的「犬儒化」、「平庸化」,以及「市侩主义」和「阿Q主义」在民众中的流行。但张大民是「阿Q」吗?今天的观众又应该如何看待他?
2019年,刘恒接受采访,并对此作出回应,「我觉得世俗的力量值得尊重」,「当普通人的能力天然地有限,自我拯救的方法也许就是自己的乐观主义,它未必不是一种精神财富。」
于张大民而言,「没事偷着乐」是面对巨大的生活漩涡时最有效的抵抗方式。比「贫」更值得深究的是无力摆脱的「贫困」。
张大民一家几个都是工人阶层出身。大民最开始是暖瓶厂工人,后转去做喷漆工。妻子李云芳是毛巾厂工人。二姐大雨是肉联厂的猪大肠清洗工。平民出身,无所依靠,遇到问题怎么办?
张大民曾试图向社会呐喊,质疑师傅私吞房屋;住的胡同要拆迁了,结果拿到合同才发现,原定补偿的三间房变两间了,大民气急,一向好脾气的他,拿着扫帚就要把拆迁公司往外赶。可是,这种挣扎终归太微弱了。没辙了,就只能发动他的民间智慧,精打细算着房屋的每方尺寸,恨不得把一套几平方米的房间各个角落都占上东西;砍不了树就圈到房子里面,一家人围着棵大树睡,还借此灵感给儿子取名「张树」。
《张大民》之后的十多年里,愈多的研究者将目光聚焦到作品背后的社会转型及其对人们精神生活的冲击上。一个如此老实巴交、憨厚乐观的好人怎么沦落到掏光屁兜也不能满足媳妇想吃一个炸鸡腿的心愿呢?
如今当我们回顾1990年代后期的中国社会,会发现其中「呈现出了非常复杂的局面」。「原有的经济体制的价值观念已经解体,人们普遍地失去了原有的心理平衡。」「空前的活跃」、「空前的紊乱」让整个中国社会「笼罩在一种困惑迷惘中」,「历史的发展似乎越来越超出了普通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和想象能力。」(张德祥,《90年代的社会转型与现实主义衍变》,1997)
剧中,李云芳和张大民接连下岗,拆迁公司修改合同,似乎种种都昭示着老百姓在已经到来的社会变革面前的手足无措。面对这些社会抛出的问题,编剧和导演没有回避,也没有试图激烈地拉扯,它被含蓄而揶揄地展示给观众。
一个矛盾的命题在于——张大民是个好人,丈母娘夸大民「除了胖和挣得少点,就没别的挑的了」。可这么一个乐观向上积极生活的好人为什么没有得到他应有的待遇?分不到房子有他,下岗失业有他。送走儿子上学后,张大民百无聊赖地游走在商场、街道中。想着做水泥搬运工却因不合格被辞退,推销暖壶却到处碰壁。他迫切地想重新支撑起这个家庭,通过劳动获得认可,却一次次被社会放逐。
由此,张大民所有的「贫」都显得真实而鲜活起来。他不再是「为贫而贫」。在痛苦与困顿重重交织的个人生活面前,小人物的求之不得、爱而不能都被这种「乐天知命」层层纾解。「贫嘴」成为了消解生活局促与不安的手段。
「比如写下岗工人,却回避他们在生活中的困苦和艰辛,只是写他们如何锐意进取,找到了更好的出路云云,让人感到似乎下岗对他们大有裨益。那不是现实主义,那是粉饰现实主义。」2000年,剧作家李跃森在《张大民》的读片随笔中如是评价。
不言而喻,《张大民》的现实性是通过喜剧的形式外化出来时,更接近大众艺术,也更具打动人心的深刻力量。

李云芳和张大民
真实生活运行的逻辑
如果按戏剧程度悉数,《张大民》大概凑足了现实题材剧的狗血戏码。不孕不育、出轨、白血病、吸毒……单把这些关键词拎出来或许就能把没看过的观众吓得退避三舍。
但看过的人却不会说一句不真实。沈好放和刘恒曾公开表示,《张大民》是一部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结合的作品。浪漫主义在于塑造的人物形象带有夸张成分,尤其在于大民身上那种「不打折扣的乐观主义」。而该剧的现实主义更为明显,以老北京胡同生活为蓝本书写平民的生存处境。之所以让人感到平实而不狗血,在于每一个戏剧性冲突被安放在针脚扎实的生活细节中,尽量让人物的性格发展遵循真实生活的逻辑,不对每一个角色进行道德判断。在拍戏过程中,即便是面对出轨的莎莎和古三儿,沈好放也不断跟演员们强调,「你们演的不是一个坏人。要站在角色位置替他想想,他内心追求善良的愿望未必比你们差。」
相比之下,如今的「现实题材剧不现实」却已经成为反复被诟病的说法。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当下都市剧中的角色们「穷不下来了」。说着草根奋斗却可能住在繁华的市中心,享受豪华的家装待遇;从普通家庭进入社会打拼的女主角却能做到每天更换大牌服装。
近两年,随着经典情景剧再次翻红,考古党们热衷在知乎上提问「《家有儿女》里刘梅一家月收入到底有多少?」
而这一问题,放在《贫嘴张大民》里似乎很好解答。
为了每个月38块钱和4块肥皂的补贴,张大民可以自愿转到污染严重的喷漆车间;给媳妇下奶滋补买的鱼被猫叼走了,他就跑到房顶上追着打。
「贫穷得扎实」的身后是深刻的社会现实。1998年,《张大民》开拍时,全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425元,月均可支配收入不足500元(据国家统计局1998年中国人口综述数据)。可以想见,在双双下岗和养活一家子的现实压力面前,张大民在金钱状况上的困窘有多么真实。
及至2005年(《家有儿女》播出前后),全年数据涨至10493元,基本翻了一翻。再到2019年,较14年前的数据又翻了4倍。但荒诞的是,影视角色里的消费水平却似乎早早领先于现实生活里的普通人,以至于愈发令人难以产生共情。
不仅是制作方感受生活的能力变了,市场口味也在随时发生调整。
人们更期待看到男女主角在性格和命运上的反转,往往是将一个人逼到绝境时,幡然醒悟或调转性情,响亮地扇回生活一个耳光,最后乘胜追击势如破竹,赢得爱情和事业的双重眷顾。
可二十年过去,纵观当下的剧集市场,我没有看到一个「张大民」式的人物。他去哪了?我不知道。但很难有一个电视剧让我看到笑着笑着就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