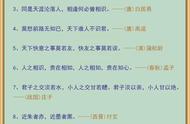2012.12.04草 2019.1.19修改
天气愈冷,便愈让人感到阳光的可爱。尽管电的热量,煤的热量,以及柴的热量,皆足以使冰霜遁形,但纵使每每徜徉于温室的暖融之下,却还是不能抑制住心中那种到田垄之上走一走的“奢念”。
空气里会密布着泥土的味道,且时时焕发出粗犷的野性,尤其大雪之后,阳光飘飘忽忽,稍稍凝视,晕眩感油然而生,继而莫名地生发出一点小迷茫和小欢喜。一想到这儿呵,仿佛已瞬间穿越了漫长的时空隧道,回到无比青涩又跃跃欲试的孩提时代。
当与玩伴们强壮到足以和一条“二细子”赛一场跑的年纪,最大的乐趣莫过于在雪地里跟随那位全村最有名的猎手,带上他的“二细子”,到一望无垠的大平原上猎一回兔。有的地方雪厚,小孩子们一脚踏下去便覆没了靴子,可打猎的诱惑使他们的两颊染上绯红。忽然,猎手在前面扬一扬左手,孩子们的喧哗一下子沉寂,猎狗小小翼翼地收敛了气势,哈腰潜踪,大家的脚下偶尔响起轻微的“吱吱”。一些散碎的爪痕蜿蜒过某一截田垄,恰好有几丛刺儿蓬挡住视线,在进入射程的一刹那,猎手的枪“砰”地炸响。而后余烟尚袅,“二细子”早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扑了上去。未几,它摇头晃尾地叨着一只硕大的野兔回来讨赏了。
是了,雪地寻踪,也许不过是与“枪”结一个宿缘的导引而已,尽管这个开端动魄惊心。最近一直在阅读两部小说,一部是美国作家梭罗的《凡尔登湖》,一部是沧州籍作家夜子的中篇《田园将芜》。两位不同历史背景不同语言环境下的作家皆在作品中不约而同地写到了“枪”。梭罗感慨,“我们不能不替一个没有放过一枪的孩子可怜,可怜他的教育被忽视,他不再是有人情的了”、“到后来,如果他身体里已播有更善良生命的种子,他就会发现他的正当目标也许是变成诗人,也许成为自然科学家,猎枪和钓竿就抛诸脑后了”。夜子则干脆把“枪”上升为男人们藉之互道衷肠把酒言欢的一个符号,一声号角——晚风阵阵,在果园里一个男人的一两声枪响之后,另外两个男人心照不宣地悄然而至,两碟小菜,两瓶烈酒,他们摇曳的一生,恍惚有了着落……
哪个男孩子的心里没有一丝丝关于“枪”的情愫与幻梦呢,这不关乎*戮或血腥。回梦前尘,爱枪之始是在一个幼小的清晨或者黄昏吧。外公祖上传下一条丈二扎枪,“盘”得光溜溜的腊条杆子上镶着一只扁长的枪头。岁月抹去了它的锋芒与*气,甚至红缨都散落不见。即便如此,它会消减一个男孩狂热的向往么?舞之抖之,他仿佛顺理成章地化身武林高手,颇有一点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的气度。扎枪可谓生不逢时,冷兵器时代烟飞灰灭,它哪比得上《南征北战》、《上甘岭》里遇神*神遇佛*佛的飞机大炮的纵横睥睨?于是小小瓜娃,遂有了民兵打靶屡驱不退的坚持,有了雪地猎手身后的狐假虎威,也有了再大一点的光景,自造火药枪的孤胆经历。
那种对于一条真正意义上的“枪”的渴念,灼热又苦恼,“求之不得,寤寐思服”,而终于在十三岁那一年,“美”梦成真。三叔去唐山卖梨,被嘱咐与他的合伙人在园子里“看家护院”。深秋的夜晚潮湿清凉,每夜提心吊胆地于黑漆漆的小径间穿行,梨树无风自动,叶子沙沙地响个不停,兼之会听到鼠兔的轻咀以及刺猬的慢跑。这些又怎么会让一个男孩望而却步呢,园子底处正有一杆鸟铳等待他去擦拭和搓摩。那是一段何其幸福美好的光阴哟,尽管那杆鸟铳不过咆哮过三两次,而对于一个男孩来说,一生可无憾。
此后不久,禁枪了。一个村子一个村子的男人们,沉默地把枪交了上去,恋恋不舍,又满怀惆怅。他们是否晓得,再有雪后,再有“二细子”撒欢的田垄,他们依旧可以跟那些身后逡巡不去的小家伙讲一讲往事,吹一吹牛。
时光不老,马放南山。在办公桌前间或失神,三十载的生旦净末,终于活成一个胡茬硬硬的狼狈大叔。再多的铁血相思,也不过似一声雪野上的鹰唳,直上云霄,后会无期……散了,都散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