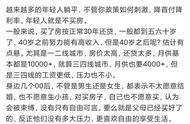前天,一篇名为《注意!这些字词的拼音都被改了!》的文章在社交媒体引起热议。“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shuāi)。” “远上寒山石径斜(xié),白云生处有人家。”“一骑(qí)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等经典古诗文的一些字的读音改动让大家惊呼不已,曾经错误的读音似乎变成正确的。关于读音的争议这篇文章已经说的非常清楚了,新版《审音表》公布后: 我们如何读古诗文,今天这篇文章更多的是想分享如何科学的读古诗?
诗歌应该怎么读才科学?伴随着近年来的“国学热”,本已沉寂许久的吟诵又进入了人们的视线。据吟诵的传承者们说,他们吟诵的调子反映的是唐朝乃至更早的古人是如何读诗的,属于文化活化石。吟诵更成为了各路“国学大师”的基本功,无论文怀沙、叶嘉莹还是周有光,皆被许为“吟诵大家”。
官方的文化机构显然也对他们提供了强大而有力的支持 — 中国多种地方吟诵已经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佼佼者如常州吟诵更是荣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重点保护对象。但是,神秘的诗词吟诵在古代是否真有如此高的地位?吟诵的历史究竟有多长呢?
辅助记忆的手段
但凡背诵过课文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 — 散文不如诗词容易记住,而诗词又远不如流行歌曲容易记住。
人类对声音的记忆受声音本身特性的影响,作为声音的一种表现形式,语言也不例外。相对于漫无规律的声音,人类大脑更容易记住有规律的声音,因此规律的韵文,如诗词歌赋更容易被人记住,反之,背诵散文的难度则要大得多。
在人类社会发展早期,书写的重要性相对较弱,文学作品的传播更加依赖口语,所以传承下来的口头文学往往是韵文。为了方便记忆,不同文化会根据语言自身特点,增强声音的规律性。
如英语是分轻读重读的语言,所以英诗讲究音步(foot),靠重读音节和非重读音节的排列组合实现轻重抑扬变化。同时,英语词尾音节结构复杂,故而传统的英国诗歌也讲究押尾韵。而英国的邻居法国的诗歌则大不一样,法语音节轻重之分并不明显,因此法语诗歌并不讲究音步,而是只重视押韵。法语的祖宗拉丁语则词尾变化很少,押尾韵意义不大,所以只靠音步;又由于拉丁语词较长,音节数量多,如英语般的强弱交替很难做到,因此拉丁语的音步节奏更加复杂多变。
柯尔克孜族的长篇史诗《玛纳斯》中则有所谓押头韵的做法,即上下两句用同一辅音开头,此种手段在古英语诗歌《贝奥武甫》中也有应用。壮诗的有些句子则在句中押韵,以利演唱山歌时停顿。

《贝奥武甫》(公元八世纪左右)讲述了斯堪的纳维亚的英雄贝奥武甫的英勇事迹,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英国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最古老、最长的一部较完整的文学作品,也是欧洲最早的方言史诗。
用较为单调重复的音乐加以伴奏也是辅助记忆的常用手法。语言与音乐配合能极大地提高记忆效率,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引发“耳虫效应”,让人不得不记住。前面已经提到壮诗有山歌调伴随,而在如《玛纳斯》之类的超长篇史诗的传承过程中,音乐的功用更不可忽视。

流行的神曲基本都会产生”耳虫效应“,旋律简单,不断重复,在大脑中形成长期记忆。
韵乐同存
中国传统的韵文则因为汉语的特点而有很大不同。
汉语是单音节语言,同汉藏语系其他语种相比,汉语较早地丢失了复辅音,形成了特有的声母 - 韵母体系,一个字占一个音节,各音节长度除入声外大致相等。这一特点使汉语音节较其他语言更整齐划一。而中古以后的汉语一直是有声调的语言,至迟自中古时代始,中国人就开始自觉挖掘汉语声调因素的审美价值。近体诗、长短句、南北曲甚至小说、弹词、地方戏曲中的韵文,无不受四声体系的制约。
因此,汉语韵文除了讲究押韵、平仄外,也素有文乐一体的传统,文学除了书于竹帛,还要被之歌咏。

工尺谱是近古以来,汉语音乐文学常用的记谱形式。
五胡乱华,中原大乱,南渡士族中流行的“洛生咏”,就是洛下书生的吟诵声调。谢安面对要*他的桓温作洛生咏,吟诵嵇康“浩浩洪流”诗句,桓温被其旷远的气度折服,于是放弃了*他的念头。顾恺之却把洛生咏说成“老婢声”,觉得其音色低沉重浊,像老太太说话。
明初死于朱元璋屠刀下的诗人高启曾写过一首诗,叫《夜闻谢太史诵李杜诗》:“前歌《蜀道难》,后歌《逼仄行》。商声激烈出破屋,林乌夜起邻人惊。我愁寂寞正欲眠,听此起坐心茫然。高歌隔舍如相和,双泪迸落青灯前。……”把一位谢太史深更半夜吟诗的意象,写得很惊人。
这样的歌唱传统就是所谓的吟诵,简而言之就是拉起嗓子来把古代诗文的字句都唱出来,而不用日常说话的语调。五四时期,旧式文人反对白话诗的一个理由就是白话诗不能吟,所以不能叫诗。
不难看出,吟诵本是辅助记忆的手段,没什么神秘可言,不是用来表演的艺术形式,更不应该是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质上甚至可以说,吟诵的作用机理和近年在以 Bilibili 为代表的网站上流行的“鬼畜”视频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通过不断重复的语音和乐段配合,达到让人印象深刻的目的。
不古的古风
虽然吟诵发端于保存记忆之用,但毕竟古已有之,它是否保存了古人的读音,也保存了古代的音乐?遗憾的是,现今各路吟诵的调子和古代音乐几乎都毫无关系。
中国最早的韵文合集是《诗经》,《诗经》305 篇,按道理是篇篇有乐曲与之配套的,但今天可以追溯到最早的《诗经》乐谱是南宋人“复原”的。在朱熹的《仪礼经传通解》中,载有南宋赵彦肃所传的《风雅十二诗谱》,音乐史家杨荫浏译过这个谱子,译完不忘加一句:“这是不折不扣的假古董。”

《风雅十二诗谱》中的《关雎》曲
《楚辞》和《诗经》一样,原本也是可以和乐歌唱的,可惜曲调早佚。史书里记载过两位会唱楚辞的人,汉宣帝时候有个“九江被公”,隋文帝时有个“释道骞”,看起来都是神秘人物,与今天装神弄鬼神神秘秘的“国学大师”应属同道中人。
莫说《诗》《*》,其实甚至连中古时代的谱子也几乎没有传世的 。中古中国受到波斯、中亚音乐的影响形成的燕乐,成为当时的流行音乐。唐代律诗、绝句都可入乐,但其乐谱均已失传了,词谱也几乎全部失传,唯一存世的就是一本《白石道人歌曲》。
既然如此,现今各种吟诵调又是从何而来呢?
当词乐失传后,明清时代的人们喜欢用其他音乐形式的曲调(主要是南北曲)来唱词。昆曲在明清盛行二百年,被公认为正声雅音,受到知识阶层的普遍青睐,古诗词吟诵调受到昆曲的影响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编撰于清朝乾隆年间的《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和编撰于道光年间的《碎金词谱》,收录了大量明清人用昆曲重新谱写的唐宋词。*晚年专门录制了一批,每首曲子都反复听,有时兴之所至,还要改动几句词,让录制组重录。

*听《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时,曾将末句”举大白,听《金缕》“改为”君且去,休回顾“。
除了昆曲,佛教音乐也进入到各种吟诵调中,胡适曾说过:“大概诵经之法,要念出音调节奏来,是中国古代所没有的。这法子自西域传进来,后来传遍中国,不但和尚念经有调子,小孩念书,秀才读八股文章,都哼出调子来,都是印度的影响。”和尚念经叫“呗”,即梵文 Pathaka,就是赞颂、歌咏的意思,诵读佛经其实采用的也是歌唱的方式,并往往用乐器伴奏。
甚至民间流行的某种曲调,也会成为该地区流行的吟诵调子。杨荫浏采集了苏南地区对于同一句《千家诗》几种不同的吟诵法,认为其中一种就是无锡旧时民间流行的宣卷声调。家庭妇女们晚间聚在灯下诵读唱本小说的时候,用的也是这种音调,后来由滩簧而来的沪剧中“过关调”也用这个调子。
当然,作为辅助记忆的手段,吟诵的调子讲究程度其实相当低。不用说因地方的不同而曲调不同,就是同一个人念两次,旋律也可能不一样。至于吟诵调旋律是否好听,因为和辅助记忆并无关系,也就不需要吟者关心,但为了追求规律,吟诵调的单调性是确定的。学会用一种腔调吟诗其实并不是件难事,只要学会了一首平起式的和一首仄起式的,其余的不学自会,因为同一格式的诗用同一种调子吟起来是差不多的。
精于常州吟诵的赵元任就说过:“无论是‘满插瓶花’,或是‘折戟沉沙’,或是‘少小离家’,或是‘月落乌啼’,只要是‘仄仄平平仄仄平’,就总是那么吟法,就是音高略有上下,总是大同小异,在音乐上看起来,可以算是同一个调的各种花样(variations)。”
而用方言吟诵更是清朝以来才形成的“传统”,根据明朝在中国的传教士的记载,明朝上流社会的读书人都是说官话的,只有不识字的贩夫走卒才使用方言。
但是今天各地的吟诵却普遍使用当地方言。仍以赵元任为例,他的回忆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种情况:“我出生在天津,说的是官话,但不会用官话读文言文。我的家乡在吴方言区西部边界的常州,它靠近官话方言区的南界。以前我会说常州话,但不会用常州话读文言文。9、10 岁上回到家乡,开始读书、念文言文。我的老师是常州人,他怎样教,我就怎样读。所以,我虽然会说官话,却只会用常州话读文言文和吟诗。”
但即便是这样的吟诵,在当下也已属难能可贵。由于吟诵被神秘化和高雅化,不少本不会吟诵的“大师”对其趋之若鹜,于是各种新创吟诵层出不穷:如文怀沙的“啸叫式吟诵”竟被不少人追捧,公开宣称不会常州话的周有光也成了常州吟诵的代表人物,甚至有“文化学者”以子虚乌有的“国子监官韵”吟诗。
然而吟诵诗词毕竟是“国学大师”的事,而对绝大多数新一代中国年轻人来说,每天登录 Bilibili,观看各式各样的“鬼畜”视频才是他们觉得更加重要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