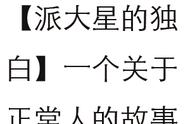来源:经济参考报

在中核集团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媒体记者参观中国实验快堆。记者 才扬 摄

我国第一台回旋加速器。记者 王璐 摄
北京西南郊的房山区,有一座因核而建的小镇——新镇,被誉为我国核工业“摇篮”和“老母鸡”的中核集团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下称“原子能院”)就坐落于此。
87岁的苏兴普经常在原子能院生活区里散步。62年前,当他“一头雾水”地从东北连夜调往北京时,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乃至后辈的命运会与中国的核事业紧密相连。
彼时,这里还是荒郊野岭,1958年第一座重水反应堆和第一台回旋加速器的建成,开启了中国的原子能时代,于敏、王淦昌、邓稼先、朱光亚、陈芳允、钱三强、彭桓武这些后来闻名中国、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科学家在此“以身许国”。
如今,“一堆一器”都已安全停闭或退役。原子能院已拥有自主研发的“多堆多器”,实现多元化应用,还先后派生或援建了14个核科技骨干单位,上万名科技人才从这里奔向全国,中国核工业走出了一条真正属于自己的创新之路。
“一堆一器” 开启中国原子能时代
走进原子能院科研生产区中心位置,在一座红色的厂房前,一块三米多长、两米多高的蓝绿色“大块头”十分显眼,这便是我国第一台回旋加速器的主磁铁。穿过钱三强、王淦昌两位科学家雕像所在的花园,与之东西遥遥相望的是我国第一座重水反应堆。
核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大型基础性核设施,中国的原子能时代,正是从这“一堆一器”开启。
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的核工业可谓是“一穷二白”。时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的钱三强认为,要迎头赶上,应从基础研究抓起。但当时不仅科研人员极少,而且连回旋加速器、核反应堆等必要的设备也没有。
1955年,党中央作出了创建中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并决定从苏联引进一座热功率7000千瓦的重水反应堆和一台磁极直径1.2米的回旋加速器,在它们“安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原子能科学研究新基地,也就是今天的原子能院。
现年85岁的曾凤英曾担任专家翻译,她清晰地记得基地选址时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情形。“什么都没有,只能看到野草、泥土,还有很光滑的石头,就像过去河水从这里流过似的。”当时下起了大雨,车一下子陷到土路旁的玉米地里。
从1956年破土动工,仅仅两年多的时间,荒郊野岭间一座原子能科学城就拔地而起。“当时大家都很兴奋,很多人吃住都在工地上,入迷了。”中核集团首席专家、原子能院回旋加速器研究设计中心主任张天爵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回忆道。
这其中就包括苏兴普。此前在辽宁鞍山一家国企做技术安全科负责人的他,突然被领导找去谈话,“说是明天要调到北京工作,我问干什么工作,领导说到了就知道了。”晚上他坐着卡车到了原子能院,第二天报到时才知道,自己被安排负责我国第一座重水反应堆核辐射防护工作。“当时我对核知识一无所知,只能边干边学。”苏兴普说。
1958年6月,喜报接踵而至:10日,我国第一台回旋加速器第一次得到质子束并且到达内靶;13日18时40分,我国第一座重水反应堆首次达临界。9月27日,我国第一座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第一台回旋加速器正式移交生产。
83岁的原子能院正研级高工张兴治介绍,随着工作的推进,国内专家也有了一定底气,承担“一堆一器”继续运行和维修工作,做了大量的自主技术改进,提高了性能,扩大了用途。
58年前,25岁的他从北京邮电大学毕业来到原子能院,“专业不对口”只能从头开始学习。1969年,为了响应“两弹一星”的研制任务,需要对回旋加速器做改进,张兴治担任运行组长。“现在仍记得,操作台上那密密麻麻的近百个开关,这要求我们三个人必须要做到像一个人一样紧密配合,才能保证数据的精确性。”
比他晚两年到原子能院的张文惠研究员如今已81岁,他回忆称真正“吃透”第一座重水反应堆用了20年,后来该设施因老化面临技术改造,都是他和同事直接上手,其中关键的一环就是“换心”——更换堆芯。
历时一年零六个月,重水反应堆成功“返老还童”,性能得到提高,而经费投入只相当于新建一座反应堆的十分之一。1985年,这项改建工程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重水反应堆还为我国第一个大型核设施出口工程——871工程(即援助阿尔及利亚建造15MW多用途重水研究堆——比林和平堆),成功提供了全套技术和经验,这项工程被誉为“南南合作典范”。
原子能院党委*万钢认为,尽管“一堆一器”是从苏联引进,“但是这个引进不是简单的引进,我们还进行了消化吸收再创新,因此形成了自己的能力。”
1984年,我国第一台回旋加速器退役。2007年,我国第一座重水反应堆安全停闭。它们为中国核科学技术研究奠定了基础,也推动了核工业的建立和发展,是“两弹一艇”研制成功背后的功臣。2018年,“一堆一器”成功入选国家工业遗产和首批中央企业工业文化遗产。
自主创新 实现“多堆多器多元化应用”
“一堆一器”的改建,只是一个开始。回顾历史,年过八旬的原子能院原院长孙祖训总结:第一,不能等靠要,要自己主动出击;第二,一旦有想法,就要赶紧去做。中国必须要建自己的反应堆和加速器。
1964年,原子能院自主设计和建成我国第一座国产反应堆——49-2游泳池式反应堆。该堆安全运行了50多年,承担了我国重大项目燃料元件考验任务,同时还用于同位素生产、材料辐照考验、单晶硅辐照、核电服务和人才培养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即将退出历史舞台时,该堆还在清洁供暖方面焕发了新的生机。原子能院堆工部反应堆运行研究室党支部*韩玉祥指着现场的模型介绍说,一座400MW的“燕龙”泳池式低温供热堆,供暖建筑面积可达约2000万平方米,可温暖20万户三居室,目前已在北方几个城市开始选址。
循着自主化这一道路,原子能院在核技术研究和应用领域大展宏图。1984年,原子能院自主开发和设计建成了我国第一座微型中子源反应堆(简称“微堆”),这是一种小型、安全、低功率的核装置,只有高压锅大小,可应用于中子活化分析、放射性同位素制备、堆物理实验及核仪器考验等。
原子能院堆工部微堆研究室党支部*牛胜利讲述了一段利用微堆破解百年谜案的故事。2008年,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联合多方力量破解清朝光绪皇帝死因,“我们采用微堆中子活化分析技术发现,光绪头发中有高浓度的三氧化二砷,也就是砒霜,比墓穴环境中的砷浓度高得多,而其胸骨、胸腹部衣物等处检验出的残存砷总量达到201毫克,充分证明光绪是被高剂量的砒霜毒死的。”
微堆还是我国反应堆“走出去”的先行者。截至目前,原子能院已为巴基斯坦、加纳、尼日利亚等国建设了微堆;在2016年成功将原型微堆中的核燃料235U富集度从90%降至12.5%,并实现满功率运行;2017年和2018年又先后成功完成加纳微堆和尼日利亚微堆低浓化改造,使中国成为第一个完全掌握微堆设计、建造、运行、退役、低浓化技术的国家。
能代表我国核科学技术研究能力的还有中国先进研究堆,该反应堆于2002年8月正式开工,2010年首次实现临界,2012年3月实现满功率运行。“从堆型选择到反应堆主工艺设计和调试,全部由原子能院承担,它的建设充分体现了立足国内、自主创新的特点。”时任工程部副总工程师张文惠说。
采访时恰逢停堆,《经济参考报》记者身穿防护外套,带上帽子、鞋套、眼罩……“全副武装”进入到反应堆内部。从顶端往下看,只见圆形的水池内充满了蓝色的等离子水,堆芯在金属容器的包裹下静立水底。来到一楼的大厅,反应堆周边布满了国内外多家知名高校、领先研究机构共建的各类先进谱仪。
原子能院反应堆工程技术研究部党委*王谷军介绍说,这座功率60MW的反应堆,主要技术指标位居世界前列,亚洲第一,能为相关领域领先研究提供不可多得的理想实验环境。例如,谱仪利用反应堆产生的粒子对测试样品进行深度扫描“体检”,可以分析其元素种类、含量、内部结构等,还能发现一些精密零部件的内部是否有裂痕。
未来核科技的探索并不止于此。2010年,原子能院研发、设计、建成中国实验快堆,2011年并网发电。作为第四代先进核能系统主力堆型,相对于压水堆,快堆不仅可以将铀资源利用率从1%左右提高到60%至70%,还可使乏燃料的放射性毒性影响和废物量降低数个量级,促进核能绿色可持续发展。“目前我国600MW示范快堆的建设正在推进中。”原子能院快堆运行室主任刘尚波称。
在加速器方面,自主创新也在加速。从1996年的30MeV强流质子回旋加速器,到2014年的100MeV强流质子回旋加速器,一批批中高能加速器的逐步产业化,正为或将为医疗、工业等领域的高精尖课题提供全新的解决方案。
目前正在调试的230MeV超导质子回旋加速器,代表着国际先进水平的质子治疗方向,适用于黑色素瘤、颅内肿瘤、眼癌、前列腺癌、肺癌、肝癌等癌症的治疗,但目前同类设备基本被国外产品垄断。“很多人问,国产的行不行?我想对他们说,在加速器部分,我们不比任何一个国家差。”张天爵直言。
人才为本 从“以身许国”到“人才特区”
孙祖训总结的第三条经验则是要重视发掘人才,培养人才,“我们几届领导班子都是这么做的。”
1955年,在建设新基地的同时,原子能科学技术人才的选拔与培养也在紧锣密鼓进行。钱三强担任团长,率领39名科技人员组成考察学习团,分两批赴苏联理论与实验物理研究所(当时称“热工研究所”)等单位实习,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在回旋加速器和实验性重水反应堆上实习,以便回国后参加苏联援建设备的安装、调试、运行和利用。
20世纪60年代,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的王淦昌回国,接到研制原子弹任务时,留下了那句时至今日仍是原子能院精神的名言:“我愿以身许国!”
不同时代的核科技工作者,用艰苦奋斗、埋头做事来践行着共同的责任担当。张兴治回忆刚进入原子能院时,脑子里除了工作就是学习,娱乐和享受安排在日常计划的最末位。“有时候下班很晚了出门,回头一看,各个大楼房间都是灯火通明,大家都在熬夜学习。”“当时每周末都有辆解放牌大卡车进城,但是大家一般不会每周都出去,一个月进城一次就不错了。”
4月17日22点42分,张天爵在微信朋友圈分享其团队的工作状态,“刚处理完实验数据回家吃饭。昨天夜里和大前天夜里,两个通宵的实验数据看起来比较符合预期,想做一次大胆的尝试。”再往前翻,是一条发于3月23日23点12分的动态:“今夜,小伙子们还在实验室熬夜,从现场传回消息判断,小线圈测磁综合精度有可能达到我们自己的一个新纪录。”
当苏兴普的核辐射防护队伍在不断壮大时,他的儿子苏胜勇从部队转业,回到原子能院,做了一名钳工,如今已是全国技术能手、中核集团首席技师,并在2017年有了自己名字命名的工作室。
比苏胜勇更年轻一辈的“80后”魏国海也受到了“以身许国”精神的感召。2005年在吉林大学读大四的他,对这个承载着王淦昌、邓稼先等科学家精神的核科技单位心生向往,努力争取到了在原子能院读研究生的机会,毕业后如愿留了下来。“我们年轻一代要以老一辈科学家为榜样,投身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实践中。”
去年以来,中核集团和原子能院还开始加快薪酬制度改革和“人才特区”建设试点,拓展事业空间,提高待遇水平,改善生活配套设施,为科技创新提供强大动力源泉。“不是小打小闹,而是要大力推。”中核集团人力资源部党支部*赵积柱称。
中核集团人力资源部薪酬处处长晁站勇解释说,现在要做的是各个岗级对标市场,进行动态调整,把待遇低的提上来,把待遇高的做存量改革。
据介绍,原子能院设立“人才特区”,立足科技人才成长的全职业周期,细化完善人才发展通道,实施科技人才专项工程“龙马计划”、海外引才专项工程“凤凰计划”、技能人才专项工程“蓝翎计划”、管理人才专项工程“百灵计划”四项人才计划。
其中,苏胜勇最关注的是“蓝翎计划”,他计划着今年再去技校里招一批学员,通过工作室的一整套安排,把自己的技术传承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