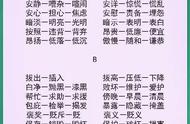斯民小学的上课时间到了。
去看桃花,看看一场春雨后桃花的花苞怎样绽开,争论压弯的桃枝更像一把剑还是三角龙的犄角。去种地,观察一场春雨后西瓜苗的长势,实验羊粪和剩菜哪个更适合用来堆肥。感受春天,去涨水的小溪抓螃蟹、逮鱼,再摸两块石头做美术课的画板。
传统公立教育的语境里,时间被精确到分秒,准确得像一个节拍器。但在斯民小学——一所浙江山里的公立小学,孩子们却可以用一整个下午剥开一朵花瓣,在教室里静静画一幅画。

斯民小学的孩子们正在野外上课。受访者供图
这并不是一个与世隔绝的教育乌托邦,也和自然教育圈曾流行的“在家上学”潮流有着完全不同的理念,一切改变发生在一所曾面临生存危机的公立乡村小学,这是一次体制内部生发出来的尝试。
改变的初衷有些迫于无奈:学生减少,撤校在即,校长斯剑光想用特色的教育留住孩子。改变的效果却出乎意料,有大城市的家长带孩子来到这里“逃避内卷”,也有推崇自然教育的家长带孩子来到这里找寻理想的教育理念,也有人看到媒体报道后慕名而来,想给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
在这个被反复讲述的结果背后,斯剑光知道这场改变有多艰难,他把这概括为“一连串的偶然”:改革的决心、理想者的加入、政策的倾斜、一步步传递的接力棒。他曾经觉得城市的、精英的教育才是不可避免的潮流,而现在,他想带着斯民小学,在乡村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逆流”的家长
从诸暨市区到斯宅村,汽车要驶过一段盘旋而上的山路,离斯宅村越近,路变得越窄,层层叠叠的林木挡住视线。绕过大坝,驶过浩渺的东白湖,听见溪流声时,就到了这个沿溪而建的古朴村落。
走过这里的老街巷,听不见人声喧闹,雨天人们躲进屋子,看山间云雾缭绕。到了晴天,水面泛着波光,村里的老人把新采的野菜晾晒在路旁,搬出椅子在老街上晒太阳。
这是一个逐渐变得空心化的村庄,因为地处水源保护地的上游,这里工业、旅游业受政策限制难以发展,村民多种植香榧、茶叶等经济作物,靠一间间土特产店撑起生活。过去的三十年里,“走出去”是这里的主题,学生去外面村子读书,考出镇子,在更大的城市落地生根,壮年则想尽办法去到附近城市打工,带着子女去城区学校接受更好的教育。

傍晚的斯宅村。新京报记者 史航 摄
在来势汹涌的“走出去”浪潮里,任溪是第一批从大城市“逆行”到斯宅村的家长。她在一所美术学院毕业,热爱自然,喜欢植物,她说:“我想在这里让孩子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
任溪的孩子齐元曾在杭州的一所公立学校读书,在老师口中是个“慢吞吞”的孩子。说是“慢吞吞”,其实齐元成绩并不差,只不过是一张卷子会比别的孩子多做十几分钟,考虑问题的时候会比别的孩子慢半拍。“但是学校不会去等他这半拍”,任溪说,后来她才知道,齐元曾多次因为卷子写得慢被老师要求重写一份,期末时整理一学期的卷子,任溪数了数,发现一共有四十多张。
那段时间每次放学,任溪在家长群里总要被老师点名,每次看到群里出现孩子的学号,她都觉得头疼,时间久了,她开始焦虑,孩子也产生了厌学情绪,变得不爱说话,丧失信心,任溪决定让齐元在家休学一年。这一年里,她去考察过杭州的私立小学,发现那里的孩子从幼儿园就开始学英语,“比原来的学校还卷”,她也去过一所奉行华德福教育理念的新式学校,却发现那里禁止孩子使用电子产品,“和我的教育理念也不一样。”
认识斯民小学是从一堂特色课开始的,那时任溪的朋友林捷正尝试在斯民小学引入特色课程《认识诗经里的植物》,她带着孩子边读诗经边寻找里面的植物,“让孩子们体会到那些诗歌里的植物可以闻、可以食、可以观赏,从而发现诗歌之美和自然之美。”
诗经讲到“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林捷在秋日的早晨带着孩子们走到上泉溪边,看溪水缓缓流淌,岸边的植物随风飘摇,他们采下河边的禾本植物,分辨芦苇、荻、芒、芦竹和斑茅的区别,摘下细长的叶子,做成一艘绿色的小船沿溪逐流。诗经讲到“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林捷就带着孩子们来到院子里、山野间,寻找诗中所说的“薇”,用看麦娘做口哨,用拉拉藤做勋章,用采集回来的薇等植物制作植物拓印手袋。
任溪确信,这是一个“可以允许孩子慢下来的地方”。
来到斯民小学前,家长刘璐也曾想过把孩子送到国际学校或者私立小学,“更彻底地逃离内卷的环境”,但几番纠结后,她最终还是选择了斯民小学。在她看来,她想给孩子一个更快乐,更适合成长的童年,却不想让孩子在童年就决定了以后要走上一条脱离主流教育的路,“一些私立学校的课程脱离升学体系太远,孩子去了之后很难再回到体系里来,但是在斯民我们可以让孩子在宽松的环境里慢慢成长,给她自己选择的空间。”对于刘璐来说,斯民小学是一条“折中”的道路,它“能让孩子在压力下好好喘口气” 。
从无锡来到斯宅村的家长杨淑选择斯民小学,是想在乡村找到自己理想中教育的样子。她从孩子出生的头两年就有了带孩子尝试新式教育的想法,看到表弟和表妹的孩子在南京读书,“在体制里受到非自然的压迫”,她感觉有点喘不过气,“两个孩子放学后父母都在旁边陪着学习,想到这样的日子可能要持续十几年,我有点害怕,所以决定要让孩子走另外的路。”
她曾追随一家奉行“自然自主教育”理念的学校来到成都,最初,她被那所学校展示的教学场景吸引:学生们三五成群地自由讨论课本,老师在旁边耐心引导,不干涉也不强加,这让她感到了教育对孩子的尊重。她开始一边在那所学校从事宣传、后勤等工作,一边陪伴孩子读书。可过了一段时间她发现,这里的教育“开始偏移,开始有了功利心”,学校为了吸引成都的家长带孩子入学,在宣传上“树标杆”,强调数学,追求超前,杨淑觉得这是对“自然自主”的背叛。
后来她带孩子从成都离开,与合伙人一起在无锡开办学堂,继续践行自己的教育理念。但这一实验也很快遇到了危机,她重视通识教育,花钱请了香港一所大学的哲学讲师给孩子上通识课,合伙人和她发了火,质疑她“花了钱却产生不了任何收益”,这段短暂的尝试最后也不欢而散。
两段城市里并不成功的教育尝试让杨淑反思,“城市里的高压力、快节奏是不是产生不了自然教育的土壤?”她把目光放到乡村里的斯民小学,在她看来,这里远离城市的快节奏,也没有很强的升学压力,她想试一试,看“自然自主”的理念能否在这片土地实现。
“来伴读的家长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任溪说,“有的小孩和我家的一样遇到厌学的问题,有的家长不认同公立学校的教育理念,也有的家长只是喜爱自然,想在这里找到一个舒适的环境。”
这些“不太一样”的家长在斯宅村碰撞出一连串的“化学反应”, 校长斯剑光协调镇政府,利用学校周边的村民空置民宿,经过简单装修改造,配备基本生活设施,出租给伴读家长,建立了一个伴读社区。这个社区本是为了解决伴读家长的住宿问题,却在越来越多的城市家长来到斯宅村后,成了一处校外教育的田地。

斯民小学的孩子们趴在礼堂看书。受访者供图
有家长做过高中老师,每晚在伴读社区带孩子们读书,教孩子英语,有家长对传统文化感兴趣,提议在这个社区里开展“夜读经典”的尝试,还有家长做心理咨询师,周末的时候,她组织伴读家长交流,教他们排解心中的压力。
任溪是美术学院出身,她在学校兼任孩子们的生活老师,也帮美术老师带美术课,她带着住校的孩子们用芦苇玩投壶,砍下竹子做成关节灵活的竹节人,还组织起“溜村”的活动,带着孩子们了解斯宅村和斯宅村外的世界。
最近的日子,斯剑光还惊喜地发现,来伴读的家长与村里的老人格外亲,因为老人的儿孙在城里,一年见不了几次,现在突然从城里来了“儿孙辈”,新的人伦亲情替代,“地白送,菜也白送,他们终于有人陪了。”眼下,斯剑光还想帮忙解决伴读家长的就业问题,他帮家长联系附近的制茶传承人,培训家长制茶的方法,还想着和镇里争取村上店铺租金的优惠,让任溪开一间手工工作室。
城市的家长回流后,斯民小学热闹了起来,有媒体聚焦城市家长的“反内卷”实验,也有其他教育工作者前来借鉴经验,想在自己的学校也开展创新,校长斯剑光被问到最多的一个问题是:斯民小学的改变是怎样发生的?
改变的种子
校长斯剑光今年四十五岁,他身材壮实,爱穿一身运动装,头发两侧推平,中间抓高,“打眼一看像个体育老师。”没有访客的下午,他爱坐在教学楼连廊处的木桌旁喝茶,或者扶着栏杆看操场上的孩子们嬉戏。有孩子倒立,他鼓劲“再坚持一会儿”,孩子爬墙,他远远地打手势,“上去,上去”,孩子从阶梯上跳下他也不拦着,“小心点别把树踩坏。”
熟识的老师都说他像个童心未泯的大男孩,带孩子去博物馆,孩子站着合影,他倒立着照,晚上带孩子玩“顶竹竿”,孩子用头顶,他要拿下巴试试,远看像在表演吞剑。生活老师任溪说,“孩子们倒立,爬墙,跳台阶,全都是他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