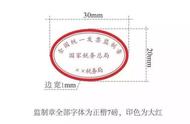内容提要:论及文言小说之功能,学界所论主要集中于资治体、辅名教的实用功能,证经补史的学术功能,以及助谈笑、资闲暇的娱乐功能等几个方面,而对其汇聚知识、博物多识的知识库功能鲜有关注。而这种认识又导致对文言小说文献资源的开发主要囿于文学、史学等人文科学领域。其实,文言小说的“知识库”功能在古代学术史上是名至实归的:在中国目录学史上,自《隋书·经籍志》至《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小说家”著录博物体著作及专业图书是一个通例;古代学界对“小说家类”作品“博识”功能认识的完全自觉与极力张扬发生于中晚明时期,体现于当时学者的论述、小说类书及小说丛书的编纂等多个方面。有鉴于此,我们对古代文言小说文献资源的开发就不能仅囿于人文、社科领域,还应拓展到自然科学研究领域。
论及文言小说或曰旧小说、子部小说之功能,古今学界所论主要集中于资治体、辅名教的实用功能,证经补史的学术功能,以及助谈笑、资闲暇的娱乐功能等几个方面,而对其汇聚知识、博物多识的知识库功能关注甚少。而这种认识又导致对古代小说文献资源的开发主要囿于文学、史学等人文科学领域。其实,文言小说的“知识库”功能在古代学术史上是名至实归的,因此其文献价值不仅体现于人文、社科研究领域,在自然科学领域也有很大的开发利用潜力。以下我们将从古代目录书的著录、古代学者的论述及小说类书、小说丛书的编纂三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一、古代目录书“子部·小说家”对博物体、专业书的著录
历代目录书“子部·小说家”所著录的两类著作与现代小说观念最为乖悖:一是博物体著作,如《博物志》、《酉阳杂俎》等。二是众多专业性书籍,如各种专业图谱、志录等。可以说,自《隋书·经籍志》至《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门户容纳博物体著作、专业著作是一个通例。以下是历代书目著录博物体、专业著作情况一览表:


中国传统博物学①“是儒家‘博物’观念的产物,常用来形容人们所见所闻的各种知识的总汇”。[1]同时传统博物学“有志异的特征,神秘主义的倾向”。[2]就是说,它将“怪力乱神”的内容也纳入其知识体系之中。综而言之,中国传统博物学具有综合性、经验性、志异性等特征,《博物志》、《酉阳杂俎》等书中都有鲜明的体现。
以《博物志》、《酉阳杂俎》等为代表的博物体著作,在中国目录学史上一直游移于“子部”的“杂家”与“小说家”之间。以张华《博物志》为例:《隋书·经籍志》入“杂家类”,《旧唐书·经籍志》与《新唐书·艺文志》改入“小说家类”,《崇文总目》入“小说类”,《通志·艺文略》《中兴馆阁书目》《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并入“杂家类”。明焦竑《国史经籍志》将张华《博物志》、李石《续博物志》及训诂辨订类的《古今注》《事物纪原》等并入“杂家类”。在清代,《明史·艺文志》将博物体著作归入“子部·杂家类”,著录明人所著:赵弼《事物纪原删定》、解延年《物类集说》、戴璟《博物策会》、穆希文《动植纪原》、王三聘《事物考》、闵文震《异物类苑》、朱谋《玄览》、董斯张《广博物志》等书。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则将《博物志》归入“子部·小说家类”。对于《博物志》续书的归类。明清书目也是两柄于“杂家”与“小说家”之间。《博物志补》于《千顷堂书目》入“子部·杂家类”,于《四库总目》隶“子部·小说家类”。《广博物志》于《千顷堂书目》、《四库全书总目》均入“子部·类书类”,但《明史·艺文志》却改隶“子部·杂家类”。而现代纂修《续修四库全书》,又将清代徐寿基《续广博物志》归入“子部·小说家类”。
除了前述“杂家”、“小说家”的归类,有意味的是,明代有些书目及丛书将《博物志》归入“格物家”名下。嘉靖间高儒《百川书志》“子志三·格物家”之下著录了张华《博物志》十卷、李石《续博物志》十卷。[2]万历间杭州出版商胡文焕编辑《格致丛书》,其“经翼”类也收录《博物志》、《续博物志》。其实,“格物家”之归类是对前代“杂家”归类的继承与延伸,反映了中晚明学界对《博物志》“自然研究”特点的新认识。
着眼于《博物志》崇尚博物的知识性以及缀辑旧文的成书方式,将这一系列著作归入“杂家”更为恰当。所谓“杂家”,班固《汉志》说:“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无所归心。”[3](P594)张华《博物志》作为早期博物体著作,其题材来源除个别故事如“八月浮槎”不见他*载,绝大部分是采集旧著而来,清周中孚《郑堂读*》卷六十七“子部小说家类”说:“《博物志》十卷(汉魏丛书本),……是本盖后人未见原书,惟采掇诸书所引,而附益以他小说,分类成编,故证以诸书所引,或有或无,或合或不合也。”[4](P172)鲁迅先生也说其“乃类记异境奇物及古代琐闻杂事,皆刺取故书,殊乏新异”,并怀疑:“(《博物志》)不能副其名,或由后人缀辑复成,非其原本欤?”[5](P31)文献学家吴枫更称《博物志》“仅就搜集选择的材料。分门别类剪裁、排比和编纂”[6](P118)。所以清黄丕烈《刻连江叶氏本〈博物志〉序》说:“茂先此书大略撮取载籍所为,故自来目录皆入之杂家。”
现代的古代小说研究界一般将《博物志》、《酉阳杂俎》等书视为“博物体志怪小说”②,几无异议。这一文体概念的提出,继承了古人对其“杂家”与“小说家”两属性质的认识,并落脚于文学研究这一情境,实际只是立足于此类著作的志异性特征,而忽略了其占主导地位的博物性或知识性。如果按照现代小说的标准,在文言小说诸种类型中,博物体志怪的小说特性是比较薄弱的。实际上,《博物志》并不能算作合格的小说著作,它是地理博物杂说异闻的总汇,地理博物的内容最为突出,此外,“一是记载了许多全无故事性的杂考杂说杂物,二是记载了许多故事性很强的非地理博物性的传说。本来地理博物体志怪的小说特征就不及杂记体来得鲜明,再加上这一点,结果是博则博矣,但却大大削弱了它的小说性,丛脞芜杂,鸡零狗碎,几乎成了一盘大杂烩。”[7](P265)《博物志》与现代小说标准还相去甚远。
由上表还可以看出,清代以前,公私书目“子部·小说家”著录专业著作的体例呈现总体的稳定性。但进入清代,情况发生显著变化。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张廷玉等《明史·艺文志》、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已将专业图书基本上逐出“小说家”门。《千顷堂书目》“小说家”著录了《考槃馀事》、《山林经济籍》等书,其内容呈现一定的专业性,但总起来看,题材庞杂,包罗甚广,如《山林经济籍》内容涉及栖逸、达生、治农、训俗、奉养、寄兴、漫游、玩物等主题,以至今人编《中国丛书广录》等书将其归入“汇编·杂纂类”丛书。《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将动物、植物、器物、食物、杂伎、艺术等专业谱录,统统移出家门,分别归入“子部”的“谱录类”、“农家类”、“艺术类”、“杂家类·杂品之属”等。将上述专业著作清理出“小说家”门,使《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小说家类”著录作品的叙事性、文学性更为突出。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一篇《史家对小说之著录及论述》曾肯定《四库总目》“小说家”分类的进步性:“校以胡应麟之所分,实止两类,前一即‘杂录’,后二即‘志怪’,第析叙事有条贯者为‘异闻’,钞录细碎者为‘琐语’而已。传奇不著录;‘丛谈’‘辩订’‘箴规’三类则多改隶于杂家,小说范围,至是乃稍整洁矣。”[5](P6)这其中也包括专业书籍的移出。
二、中晚明学界对“小说家类”博物功能认识的自觉
中国古人对于“知识”的兴趣与掌握常用“博物”来表达,而博物的书又常被置于“小说”名义之下。这种现象颇值得探讨。
对“小说家类”博物功能认识的觉醒始于元末明初,而知识界的学理自觉与极力张扬则发生于中晚明时期。自宋元以至明代,学界对小说价值的认识,由推崇资治体、裨名教的实用功能及证经补史的学术价值,逐渐转向对其博物洽闻功能的张扬。南宋曾慥《类说序》说:“余侨寓银峰,居多暇日,因集百家之说,采摭事实,编纂成书,分五十卷,名曰《类说》,可以资治体,助名教,供谈笑,广见闻”[8](P6)。曾慥将小说的“资治体”、“助名教”价值排于首位,而将“广见闻”置于末位。元末杨维桢为陶宗仪《说郛》撰序称:“学者得是书(《说郛》),开所闻,扩所见者多矣。要其博古物可为张华、路段;其核古文奇字,可为子云、许慎;其索异事,可为赞皇公;其知天穷数,可为淳风、一行;其搜神怪,可为鬼董狐;其识虫鱼草木,可为《尔雅》;其纪山川风土,可为《九丘》;其订古语,可为钤契;其究谚谈,可为稗官;其资谑浪调笑,可为轩渠子。”[9]杨维桢标举《说郛》十个方面的价值,其中“博古物”、“核古文奇字”、“索异事”、“知天穷数”、“识虫鱼草木”、“纪山川风土”、“订古语”等七个方面,都是关于小说认识功能及学术价值的。与曾慥的小说价值观相比,杨维桢强调的重心已转向“开所闻”、“扩所见”,迁移的痕迹十分明显。明初佚名《群书类编故事序》也宣称,阅此书“足以广闻见、长智识”[10]。
在中晚明学界,论及小说家类的价值,“博物多识、拓展视听”是中心话题。小说的认识功能和学术价值被空前高扬,而传统的辅名教、补史阙、助谈笑等功能被挪移至次要位置。许多从事小说编撰、刊刻、收藏及为小说作序跋的人往往异口同声宣扬小说的博识功能,同时亦为自己的实践活动正名。都穆于弘治十八年(1505)为《续博物志》所作《后记》中说:“小说杂记,饮食之珍错也,有之不为大益,而无之不可,岂非以其能资人之多识,而怪僻不足论邪?”[11](P91)莫是龙《笔麈》云:“经史子集之外,博闻多知,不可无诸杂记录。今人读书,而全不观小说家言,终是寡陋俗说。宇宙之变,名物之烦,多出于此”[12](P15-16)谈恺刊《太平广记》五百卷,卷首附按语云:“庶几博物洽闻之士,得少裨益焉”[13](P2)。刘大昌《刻山海经补注序》称:“世之庸目,妄自菲薄,苦古书难读,乃束而不观,以为是《齐谐》、《夷坚》所志,俶诡幻怪,侈然自附于不语,不知已堕于孤陋矣。夫子尝谓,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计君义不识撑犁孤涂之字,病不博尔。”[11](P91)胡震亨撰《搜神记引》,称赞干宝“爰摭史传杂说,参所知见,冀扩人于耳目之外”[14]的举动。藏书家范钦《烟霞小说题辞》自陈:“余不佞颇好读书,宦游所至,辄购群籍,而尤其稗官小说,窃怪夫弃此而只信正史者,譬如富子惟务玉食,而未尝山殽海错,可乎?”[15](P445)黄吉士《续问奇类林序》自辩:“孔曰博文,孟曰博学,圣贤之学,固如斯矣。”[16]庄汝敬《稗家粹编跋》也伸张此意:“尝观稗官野史与诸家小说之流。非徒好奇语怪者为悦,即博学好古之士往往从而藉记之。”[17](P493)焦竑《国史经籍志》“子部小说家类”按语说:“阴阳相摩,古今相嬗,万变挢起,嵬琐吊诡,不可胜原,欲一格以咫尺之义,如不广何?故古街谈巷议,必有稗官主之,譬之菅蒯丝麻,无悉捐弃,道固然也。余故仍列于篇。盖立百体而马系乎前,尝闻之庄蒙也。”[18](P186)既然儒家的咫尺之义无法尽格古今万物,那么,稗官小说自可发挥独特的功用。
胡应麟对“小说家家类”学术个性的论述始终立足于诸子学术共性的基础之上,所以他的观点更具穿透力。他在《少室山房笔丛·华阳博议》中说:“经之流别,爰有小学;史之流别,爰有诸志;子之流别,爰有众说”。又云:“子之浮夸而难究者莫大于众说,众说之中,又有博于怪者、妖者、神者、鬼者、物者、名者、事者。《齐谐》《夷坚》博于怪,《虞初》《琐语》博于妖,令异、元亮博于神,之推、成式博于鬼,曼倩、茂先博于物,湘东、鲁望博于名,义庆、孝标博于言,梦得、务观博于事,李昉、曾慥、禹锡、宗仪之属,又皆博于众说者也。总之,脞谈隐迹,巨细兼该,广见洽闻,惊心夺目,而淫俳间出,诡诞错陈。张、刘诸子,世推博极,此仅一斑。至郭宪、王嘉全构虚词,亡征实学。斯班氏所以致讥,子玄因之绝倒者也。”[19](P384)这段话把“小说家”务博尚怪个性内涵论述得详尽之极。在《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中他又说:“子之为类,略有十家,昔人所取凡九,而其一小说弗与焉。然古今著述,小说家特盛;而古今书籍,小说家独传。何以故哉?怪、力、乱、神,俗流喜道,而亦博物家所珍也;玄虚、广谟,好事偏攻,而亦洽闻所呢也。”[19](P282)胡应膦从世人接受心理的角度揭示了小说一家之所以古今独盛,就是因为它能迎合、满足人们“博物洽闻”的心理期待。
晚明士人对小说“博识”价值的张扬是以先儒“博学博文”之论为初始依据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博识”可以被纳入由“博”(博学)及“约”(明道)、由知至用的认识论框架,与明代中叶以降兴起的经世实学思潮是相合拍的。
中晚明许多文言小说汇编之书辟有“博物”、“博洽”、“博识”、“该博”、“博学”之类的门目。叶向高《说类》“文事部”下有“好学”、“该博”二子目,“帝王部”下也有“好学”之目。孙能传《益智编》“人事类”下辟有“博物”子目。周履靖《夷门广牍》设有“博雅门”。中晚明士人编撰的专门志人的仿“世说体”小说约有40余种,其中许多设置“博学”之类的门目。何良俊纂《何氏语林》三十卷,体例既仿临川《世说》,但又增“博识”、“言志”二门,在“博识门”小序中,他特别标举孔子“贵博识”之论:“若夫孔子之善诱,与颜子之善学者,唯‘博’、‘约’二语而已,盖二者互相为用,不可废也,……后世舍博而言约,此则入于释氏顿悟之说,道之不明也,夫何尤?”[20](P104)《琅嬛史唾》、《耳新》、《霞外麈谈》、《初潭集》、《廿一史识余》、《问奇类林》、《续问奇类林》等均有此类门目。从中透露出,中晚明士人品评人物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他是否“博物”。
中晚明士人汇编了许多文言小说类书和文言小说丛书,这些汇编之书的题材来源体现出鲜明的张扬知识性的倾向。许多小说类书借“小说”名义以建构新的知识体系。叶向高编《说类》六十二卷,分四十五部,借鉴正宗类书③之体,构建了完备的知识体系。白天文、地理、人事、众物以及灵异,兼容并包。其自序称:“盖上自天文,下及地理,中穷人事。大之而国故朝章,小之而街谈巷说,以至三教九流,百工伎艺,天地间可喜可愕可笑之事,无所不有,虽未足尽说家之大全,然其大端已约略具是矣”。[21](P1-3)其分类情况如下:
天文部 岁时部 地理部 帝王部 后妃部 储戚部 宰相部 官职部 臣道部
政术部 刑法部 礼仪部 歌乐部 凶丧部 文事部 武功部 边塞部 外国部
科名部 世胄部 人伦部 人物部 妇人部 身体部 人事部 释教部 道教部
灵异部 方术部 巧艺部 居处部 货宝部 玺印部 服饰部 饮食部 器用部
杂物部 灾祥部 果部 草部(蔬附) 木部(竹附) 鸟部 兽部 鳞介部 虫豸部其分类体系与《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正宗类书基本一致,但汇辑的全是“小说”资料。
顾起元纂《说略》三十卷,现存万历四十一年(1613)吴德聚刻本,其分类情况如下:
象纬 方舆(上下) 时序 人纪 官仪 史别(上中下) 礼蕞 律支 典述(上中下) 字学 书画 李法 冥契(上下) 居室 服饰 工考(上下) 谐志 食宪
珍珠 卉牋(上下) 虫注(上下)也大致体现天、地、人事、众物之分类格局。顾起元向有阅读说部而又勤做札记的习惯,《说略》即来自其读书札记。他有感于“世之闳览博物君子且囊括昔之为《海》为《郛》者以大其畜”,在友人勉励下,他将这部札记付之剞劂,并自负地宣称:“可藉以备丹阳之钞,补河东之箧。虽六艺键钤,九流津涉,原原本本之论,未极于斯。至于考验是非,综校名实,兼资前识,用广异闻,古今贤哲之用心,往往可以概见。”[22](P344)
穆希文《说原》十六卷,编成于万历丙戌年(1586)。分原天、原地、原人、原物、原道术五部。“杂采事迹,间亦论断,其体例在类书、说部之间。”[23](P1103)其类目如次:
卷一至卷三 原天 卷四至卷六 原地
卷七至卷九 原人 卷十至卷十三原物
卷十四至卷十六 原道术穆希文自序称:“说原者,原天地人物之理而为之说者也。……仍取艺文经籍,志类群书,几易寒暑,四更稿草,研搜诠综,揽撷其玄黄者,附以己见,笔之其诸蠹,谬者悉为剔正,类各有目,目各有说。先之以天地者,人物之祖也;次之以人物者,天地之所生也。而道德艺术,又自人而为之。故以道术终焉。此盖文欲尽博我识,以格物无遗也。奚止尝一鼎脔,啖一鸡蹠已哉!世有博雅君子,更出中密之藏,以续其所未备,只是吾师。”[24]
王圻纂《稗史汇编》一百七十五卷,分二十八门:
天文门 时令门 地理门 人物门 伦叙门 伎术门 方外门 身体门 国宪门
职官门 仕进门 人事门 文史门 诗话门 宫室门 饮食门 衣服门 祀祭门
器用门 珍宝门 音乐门 花木门 禽兽门 鳞介门 征兆门 福祸门 灾祥门
志异门王圻《〈稗史汇编〉引》解释其总体构思:“……总之为纲二十有八,列之为目三百有二十,而命之曰《稗史汇编》。是集也,分门析类,使人易于检索,而记事之次,一以世代先后为序,俾将来作者,得随时随事而附入。此又命名之意也。”[25](P533)先按题材重点对辑录的说部资料进行横向分类,每类之中再依编年之体纵向编排。借鉴典制通史之例,王圻尝试建构稗编通史之体制。
表面看来,中晚明小说类书的分类名目、分类体系与正宗类书并无明显差异,其实,在同样的类目下,它们的选材旨趣却显著有别于正宗类书。其资料很少采自正经正史,而是偏重于经传注疏、杂史杂传、野史笔记、方志风土、诗话词话、神话志怪等,以建构正统学问之外的民间知识体系。
余嘉锡先生云:“汇萃古今小品文字,加以刊削,刻为丛书,自成明人一种风气。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十五‘类书类’,著录陶宗仪《说郛》以下诸书皆是也。其佳者能使古人单篇零种赖以传世,有网罗放失之功。”[26](P940-941)中晚明文言小说丛书所收亦多博物体及专业图书。以《中国丛书综录》[27]“类编·子类·小说”所著录明代文言小说丛书所收录作品为例,窥探其性质之一斑:

沿袭前代体例,清代至近现代的许多书目、文言小说丛书仍然著录、收录博物体、专业著作。如清王文诰辑《唐代丛书》(有清嘉庆十一年(1806)序刊本)、近代国学扶轮社辑《古今说部丛书》(有清宣统至民国间上海国学扶轮社排印本)、王文濡辑《说库》(有民国四年(1915)上海文明书局石印本)、清虫天子辑《香艳丛书》(有清宣统中国学扶轮社排印本),等等,均是如此。今人石昌渝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文言卷)(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其收录范围很注意与“古代目录学传统的接轨”,“采取宁宽勿缺的方针,除了著录文学门类的小说作品之外,还将古代公私书目著录的‘小说家类’作品一概收录”。[28]诸如《采茶录》、《茶谱》、《古今刀剑录》、《花木录》等专业书籍均被著录入内。
三、古代文言小说文献资源的多维开发
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博物体著作及各种专业书籍长期混迹于“小说家”门,是由封建正统学术观念和学术格局所造成的一种畸形现象。众所周知,封建学术的最突出特点是:经学独霸,圣言独断。其余百家群言皆为经学之注脚和附庸。《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叙”称:“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23](P1)既然圣经“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其余学术在其强光照射下只好闭上眼睛、闭上嘴巴了。封建学术格局中居于其次的是与王权统治密切相关的正史书写与研究,《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正史类序”云:“正史体尊,义与经配。”[23](P397)《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总叙”又云:“夫学者研理于经,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征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败。余皆杂学也。”[23](P769)明代可一居士为《醒世恒言》撰序也曾称:“六经、国史而外,凡著述皆小说也。”[29]这里“小说”即是小道、杂学、末学的同义语。而在某些理念极端的正统学者视野中,连史学研究也被视为“玩物丧志”之举。④在这种舍六经国史、余皆为土苴的学术观念、学术格局主导下,各种自然科学领域的专业研究遂成为“君子不齿”的“杂学小道”、“小说末学”,其在目录学上的反映就是“小说家”之归类。
综上所论,中国古代小说的学术内涵远比现代小说宽泛而复杂得多,在更多情境中,它并非归属于文学的域界之内。胡应麟的小说六分法,虽把最具小说性、文学性的志怪、传奇置于小说内涵的核心区域,但其余四种:杂录、丛谈、辨订、箴规,后二种内涵比较清楚,“杂录”、“丛谈”二种则比较笼统含混,二者之间也域界不清,胡氏自己也承认“谈丛、杂录二类最易相紊”。[19](P282)校以《四库总目》“小说家”分类,胡氏的“杂录”应与后者“杂事之属”相近,其《丛谈》当近于后者的“琐语之属”。但他并未把“博物”单独辟为一类,这不能不说是胡氏小说分类的一个缺憾。《四库全书总目》所谓“杂事”类小说如《西京杂记》、《大唐新语》、《唐国史补》、《朝野佥载》之属更贴近于野史杂录,与刘知几《史通·杂述》所称的正史之外的“偏记小说”有很大程度的重合。其界定“琐语之属”的主要依据是此类作品纂辑琐言、不重叙事的文本形态,仅仅限于外在形式层面,并不关涉著作的内涵性质。如博物体著作、专业图书肯定以汇聚知识为重心,本来就不关注叙事。在文言小说诸种类型中,可以说,只有志怪题材的作品才最为接近现代的小说观念,即使那些情节曼妙、文采斐然的传奇小说,在宋元明学界也往往被视为与史部更为亲近的“杂传记”。今人谈论古代“小说”动辄指责此书非小说、彼书非小说,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真正正视古代“小说家”隶属于“子部”的学术背景与传统,从而犯下以今律古、以今绳古的错误。如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类编·子类·小说”著录顾元庆《顾氏文房小说》四十种、《顾氏明朝四十家小说》,并无不妥。但因为以上顾氏二书收录了诸如《鼎录》、《茶谱》、《诗品》之类的专业书及《古今注》、《资暇集》、《瘗鹤铭考》之类的辨订类著作,阳海清编《中国丛书综录补正》就提出“所收诸书并非均属小说,宜分入‘汇编成书·杂纂类’”[30](P219-220),正是陷入了“以今律古”的认识误区。
同时,既然古代文言小说以“博物多识”为己任,承担正统经史以外许多学科领域“知识库”的功能,所以文言小说文献的学术价值就不仅局限于小说研究或文学研究,而应拓展到科学史、科技史及思想史研究的广阔领域,以最大限度发掘古代小说文献的学术价值。值得欣喜的是,古代小说史料的跨学科运用已经引起学界重视,并取得了一些进展。如当代许多科学史论著将《博物志》系列著作视为传统博物学的主要代表形式之一,探究其科学史、思想史价值。如美国学者本杰明·艾尔曼《收集与分类:明代汇编与类书》[31]一文提出,在晚明时期,《博物志》与《续博物志》出现于“格致”主题之下,标志着胡文焕将“博物”看作“格物”的重要组成部分,肯定了其认识论价值。周远方《中国传统博物学的变迁及其特征》[1]一文认为:“从中国传统博物学的演变来看,其学术体系的传承是有规律可循的。它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传承脉络,就是从《山海经》及《尚书·禹贡》到张华的《博物志》,再到此后的两个系列的博物学著作。”其一就是《博物志》及其后世的续补之作,论证了《博物志》在中国古代博物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刘华杰《博物学论纲》[32]一文也将张华《博物志》作为中国古代博物学著作之一种。近年来由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开发制作的《中国基本古籍库》将《博物志》归入“哲科库·综合科技目”⑤,是对《博物志》思想史、科学史价值的认可。再如明初叶子奇(约1327-1390)著《草木子》一书,现代学界一般视之为“笔记小说”,20世纪以来曾被多次收入“笔记小说大观”之类的丛书,⑥但法国学者梅泰理(Georges METAILIE)却运用《草木子》研究中国古代动植物学。[33](P33)他引用《草木子·观物篇》一段论述:“动物本诸天,所以头顺天而呼吸以气;植物本诸地。所以根顺地而升降以津。故动物取气于天,而乘载以地;植物取津于地,而生养以天。善乎《素问》之言曰:‘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废则气立孤危。无不出入,无不升降,器有大小,数有远近。’盖谓此也。动物本诸天而体则温,植物本诸地而体则冷。阴阳之谓也。”[34](P14-15)指出中国古人借用阴阳理论和“格物”方法研究植物生理的特点,并发掘了《草木子》对植物营养、嫁接技术的论述。这些都是今人对文言小说文献认识论及科学史价值重新认识的体现。这种研究可以说具有非常广阔的前景。
注释:
①相对于近现代西方博物学,中国古代传统博物学自有其独特内涵及民族特色。一般认为,其学术体系包括如下分支:《博物志》及其后世续书;以《尔雅》为代表的“雅学”系列著作;以《毛诗草木虫鱼疏》为代表的“诗人多识之学”;《山海经》、《越绝书》以下的地理方志;后汉杨孚《异物志》为代表的“异物志”系列著作;本草与农学著作;动物、植物、器物及艺术谱录;类书系列。(参阅朱渊清《魏晋博物学》,《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周远方《中国传统博物学的变迁及其特征》,《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1年第5期。刘华杰《博物学论纲》,《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②刘叶秋先生将魏晋志怪分为三种类型,其一为“兼叙神仙鬼怪,不专谈某种宗教或方术,夹杂着零星琐碎没有故事性的记载,以《搜神记》为代表”;其第二种为“兼叙山川、地理、异物、奇境、神话、杂事等,而着重宣扬神仙方术,以晋张华的《博物志》为代表,乃《山海经》系统的延续。”实际此类即为地理博物志怪小说;第三种为“专载神仙的传说,以人系事,体同纪传,以晋葛洪的《神仙传》为代表,乃汉刘向《列仙传》的摹仿和扩大”。(刘叶秋《古典小说笔记论丛》,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7页。)侯忠义将汉魏六朝小说分为记怪类、博物类、神仙类。(侯忠义《汉魏六朝小说史》“魏晋小说上”,春风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39-113页。)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将唐前志怪小说分为杂史体、杂传体、杂记体、地理博物体等四类。(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1-22页。)潘建国将汉魏六朝小说按照题材类型分为地理博物、杂史杂传、神仙方术三类。(潘建国:《中国古代小说书目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页。)
③胡道静先生说:“我们现在所说的类书,就是指这种兼‘百科全书’和‘资料汇编’性质的古籍。正宗的类书,也就是这种性质的古籍。”(胡道静:《中国古代的类书》,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1页。)主要指《皇览》、《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书。
④如《四库全书总目》卷六五为宋吕祖谦《十七史详节》所撰提要云:“南宋诸儒,大抵研究性命,而轻视史学。……祖谦虽亦从事于讲学,而淹通典籍,不肯借程子玩物丧志之说,以文饰空疏。故朱子称其史学分外仔细”。(见《四库全书总目》卷六五,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579页。)
⑤《中国基本古籍库》先后列为“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重点项目”和“国家重点电子出版物十五规划项目”,由北京大学刘俊文教授总策划、总编纂、总监制,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开发制作,于2001年3月正式启动,2005年10月全部完成。中国基本古籍库分为4个子库、20个大类、100个细目,精选先秦至民国历代重要典籍,收录范围涵盖全部中国历史与文化,其内容总量相当于3部《四库全书》。
⑥如199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刊《历代笔记小说大观》,其《明代笔记小说大观》部分共收14种,第一种就是叶子奇《草木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