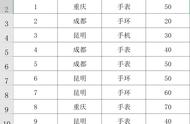◎周崇贤
1
都冬天了,张莲脸上还在长痘痘,据说是因为内分泌失调,这让她很苦恼。为了治好这个痘痘,她真是什么办法都想过了,上正规医院,用民间偏方,听张三李四的建议,忌口。比如说不吃火锅,不吃辣椒,不吃……甚至往衣服包包里揣了个小镜子,随时拿出来,对着镜子动手去掐,去挤,去摁……可是,没有用,那些红红的,硬硬的小肉头,总是隔三岔五地在她脸上开出白色的花蕾。
这两年,张莲干得最多的一件事,不是打怪兽,而是挤痘痘。为这事,她每个月都得跑县城,到美容院去拿药,几百块一个疗程,花得那个肉疼啊!可是,有啥办法呢。她已经被脸上的痘痘搞得筋疲力尽,几近崩溃。有时,张莲挤痘痘被张小梅看见了,就会叫别挤。“你这样挤会留疤痕的。”张小梅说,“要是破相了,小心老公不要你。”
张莲不理她,照挤不误。“哈,不要就不要。一年到头鬼影都看不见。”
张小梅说:“听你这意思,想老公了?”
张莲说:“想你个头”。说话的时候,眼睛还是盯着小镜子,一丝不苟地挤痘痘。
张小梅:“说熬夜最容易上火,我看你还是少刷视频少网聊,每天晚上早点睡觉就不长痘痘了。”
张莲说:“你以为我想熬夜呀,睡不着有啥办法,不网聊,就无聊。”一边说一边继续挤痘痘。
张小梅就有点不耐烦,说:“挤啥呀,长青春痘,说明你还青春。”
张莲当然不会停手,她“嘁”了一声:“站着说话不腰疼,哪天长你脸上,看你挤不挤。”
张小梅摸摸脸,说:“呸呸呸,乌鸦嘴。”
2
张莲跟张小梅是姐妹,张莲是姐,张小梅是妹,两个人出生的时间,也就差个把小时。这倒不是说她们是双胞胎,她们不是一个妈生的,当然,也不是一个爹生的,所以说她们不是双胞胎。她们是堂姐妹。
张莲中等个子,长得有点壮,或者说有点胖。张小梅刚好相反,身段苗条,甚至可以说有点偏瘦。和张小梅的小身板比较,张莲算得上是大块头了,那壮硕的个头,差不多就要比张小梅富裕一倍。只是,这种富裕仅限于身体,如果从家境,从个人经济条件上讲,她与张小梅,刚好成反比。也就是说,张莲家境不好,甚至有点困难,男人常年在外做泥工,很拼,却挣不下几个钱,经常是活干了,却收不到工钱。雪上加霜的是,婆婆还瘫在床上,是个药罐子。
张小梅就不同了,她的那个小蛮腰,用一个茶馆常客的话说,简直就是“广州塔”。
“广州塔晓得不?上一次都得几百块。”茶馆常客如是说。
最重要的是,张小梅嫁了个有钱人家,是的,是有钱人家而不是有钱人,因为他老公何小兵没啥钱,除了打牌,也没啥本事挣钱,这家伙打生下来,就成天跟着他爹上街打牌,耳濡目染,差点就练成了牌桌上的一代宗师,据说他那牌技,打遍周边无敌手,搞得最后都没人愿意跟他玩,除非只是打耍,不赌钱。所以他神话般的牌技,就没了用武之地。也不知这个“据说”是真是假,反正张小梅从跟他耍朋友起,就没见他赢过几回钱。
但何小兵家有钱,除了钱,他们家在老街上,还有一个百多平米的铺面,那家伙,大清王朝时代的房地产,老古董,你说要是转手把它卖出去,得多少钱?不,张小梅不会转手,因为这些年场上的旅游搞得风生水起,来场上花钱的外地人一天比一天多,老街门面,简直就是大银行,她才不会傻得把门面卖掉呢。她要用来开茶馆,赚钞票。
张莲跟张小梅没得比,除了壮或者说胖,其他方面都没得比。好在张家女子质地都不错,和张小梅一样,张莲的皮肤也是白生生的,因为壮或胖,她的白看上去让人蛮有食欲,像“糯米糍粑”。关于这个比喻,也是茶馆常客说的。那个家伙,别看他年纪不大,眉清目秀,还偶尔在鼻梁上架副眼镜,像个斯文哥,却赌性十足。每次到茶馆来,不只是赌得大,还经常带着来路不明的女子,坐在身边跟赌。最让人想不明白的是,这哥们牌技不咋的,经常乱打一通,却又经常胡牌。反正跟着他下注的这女那女,多半都会赢得娇笑连连,脸上开花。
斯文哥爱开张小梅的玩笑,但对张莲兴趣不大。关于这点,张小梅早就发现了,其实也不只是发现他一个,从懂男人开始,张小梅就发现了很多,是的,很多男人都喜欢她的白,喜欢她的小蛮腰,她想这其实是多数男人的毛病,他们好像打娘肚子里生下来,就无师自通地爱好“广州塔”,他们不喜欢“糯米糍粑”。
“广州塔晓得不?上一次都得几百块。”这话就是斯文哥说的,当着她的面说的,说得像一个恶作剧,又像是一次狡黠的试探。
刚听到这比喻,张小梅还有点发懵,一时间竟没反应过来。广州塔她是上过的,记不得要多少钱,反正得买门票,上去之后还得消费,转一圈下来,何小兵按着胸口直喊疼。何小兵就是那个传说中的牌神,她老公,在开茶馆之前,他们一直在广东打工。
张小梅早已经不是懵懂少女了,她早已经成年了,而且早已经嫁为人妇了。用一个流行词来形容,那就是熟妇。对,她是熟妇,熟得就像八九月间的葡萄,要是还没人摘,就自己掉地上烂掉了。她当然知道男人那点小心思,漂亮女人,哪个男人不喜欢?就算他有病,也没理由不喜欢。是的,张小梅知道,很多男人都会喜欢她。她喜欢被很多人喜欢的感觉,特别是被很多男人喜欢,这种感觉,真好。
可是,广州塔?好像还没哪个男人说过她是“广州塔”。男人都习惯赞女人漂亮,像花朵,像明星,像水做的等等;万一不漂亮,就赞你有气质;再万一既不漂亮又没气质,他们就会一脸深沉,说你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反正没谁说女人是广州塔。
广州塔!回过神来的张小梅,禁不住“哈”了一声,这比喻,也……太他妈有才了!
她想这斯文哥不只是好赌,恐怕更好色。
3
自从被比喻成“广州”塔后,张小梅就有了一个顾影自怜的习惯——每次看到镜子,就忍不住要停住脚步,或左或右地摆些姿式,朝着镜中人审视一番。洗澡的时候就更自恋了,经常一洗就是老半天,搞得何小兵好多次便急要用厕所,不得不在外边砰砰拍门,说你到底要洗多久啊,洗到过年啊?
实际上张小梅把自己关在厕所里,并不完全是在洗澡,更多时候,她是在看“广州塔”,或者说在欣赏“广州塔”。左着看,右着看,正着看,反着看,转着圈看,越看越觉得斯文哥眼光有毒,厉害!他那个眼镜,有时戴有时又不戴,说不定就是红外线的,能透视,要不然,他怎么知道她是“广州塔”?都生过两个娃了,按理说这身材得走样,得变形,得中间粗两头细,像个青果。可情况却不是这样子的,她的肌肤不能说弹指可破,但要说腻滑,还真不是夸张。你看那些水珠儿,哪一颗不是刚落在身上,马上就滚到地上去了?为啥,皮肤嫩嘛,光滑嘛!至于身材、小蛮腰,真的是“广州塔”呀!
还在广东打工的某年,她跟何小兵上过广州塔,但她从来就没想过自己会是“广州塔”。可是,镜子里的这小蛮腰呀……不陶醉都不行。又回头想,都是两个娃的妈了,还“广州塔”呢!唉,天增岁月,人增禽兽!这斯文哥呀,真不是啥好人。
其实斯文哥也不是只盯着她,有时候也会开张莲的玩笑,比如有天,刚进茶馆坐下,他就盯着张莲,好一阵看,看得张莲莫名其妙。
张莲一边抹桌子,一边说:“你不认得我?”
斯文哥说:“你脸上长痘痘了,青春痘。”
张莲“嘁”一声,说:“都快成豆腐渣了,还青春痘。”说的时候,下意识地抬起手,摸了一下脸庞上的痘痘。
斯文哥说:“你不要这样自暴自弃嘛。我觉得女人三十不是豆腐渣,而是水豆腐……啧啧!所以,我敢肯定你长的是青春痘。”
张莲说:“青你个头。”
“痘痘长脸上,痛痒为相思,劝你别照镜,此物会思春。”斯文哥即兴赋诗一首,笑嘻嘻地问张莲说不是青春痘那是什么痘,相思痘?
张莲说:“我看不是想(相)撕(思)痘,是想撕烂你的嘴!”
斯文哥哈哈笑,说:“你老公过年回来不?老是这么牛郎织女,阴阳失调,内分泌紊乱,不但会长痘,久了还会得病的。”
真的是呸呸呸,乌鸦嘴。不幸总是被言中。没几天,张莲真的生病了,上火,口腔溃疡,咽喉痒痛,咳咳咳……吃药打针,钱都花了好几百,还是不见好。眼看过年了,打电话问老公几时回来,那边竟给不了准信,说赶工,忙得很,不晓得啥时才放假。
张莲放下电话,有些失落,伸手摸摸脸上的痘痘,那东西硬硬的,热乎乎的,让人摸着摸着就想把它摁平。该不会真是相思痘吧?内分泌紊乱是因为没男人?想想,连自己都禁不住笑了。
4
昨晚下了点雨,天一下子就冷了。早晨到来的时候,张小梅在被子里推了推何小兵,想叫他起床。快过年了,在外边打工的人,有的已经回来了,有的还在回来的路上。只要他们一回来,小梅茶馆的生意,就会猪年狗叫旺旺旺。
张小梅推何小兵的意思,就是叫他快点起来,去茶馆开门迎客。那些回家过年的打工人,在外累了一年,好不容易有个喘气的档期,都喜欢往茶馆里钻,喝茶倒是其次,主要是约几个熟人打牌,不管“斗地主”,还是打麻将,都可以打得昏天黑地,废寝忘食。
每年春节前后,是小梅茶馆最赚钱的黄金季节。当然啦,靠卖茶水是赚不下几个钱的,靠出租牌具,也赚不了几个钱,小梅茶馆的收入,主要是靠“抽水”。上茶馆打牌,没几个不赌钱的,只要你赌钱,就要接受“抽水”这个行规。
何小兵好像还没睡醒,被小梅推了几把,没反应好像也不行,便嘟嚷几句,转过身,又要睡。张小梅有点急,伸手拧了他一把,痛得何小兵“啊”的一声,差点从被窝里蹿起来。“大清早的搞啥子?有病啊!”
张小梅说:“还不快起来开门接客?嫌钱多啊?!”又伸手拧他。何小兵掀开被子跳起来,立即被一股冷风疯狂扑倒,他“啊呀呀”地叫着,转身就往被子里钻。
“太冷了,他妈的。”他说,“叫张莲先过去把门打开。”
何小兵说的张莲,就是张小梅的堂姐,以前跟着老公在广东打工,后来婆婆莫名其妙的就瘫了,没办法再帮他们带娃儿了,加上娃儿也到了上学年纪,总得有人照看,张莲就回来了。从此,家里除了留守儿童,又多了一个留守妇女。张莲回来不久,便到小梅茶馆里打杂了,一个月有千把块钱,算是亲戚间的互相照应。
其实张小梅跟何小兵以前也在广东打工,也是因为娃儿要上学了才回来的。穷乡僻壤,乡亲们除了挖土种地,顶多也就是趁赶场天上街摆个摊子,做点针头麻线的小生意。余下的时光呢,便是游手好闲,吹壳子扯闲事,打牌混时间。张小梅跟何小兵就是看准这点,才夫妻双双把家还的,要不然,他们也会像张莲两口子一样,一个在外打工,一个在家留守。
因为在老街场上有间铺子,所以他们就开了这个小梅茶馆。明里说是茶馆,暗地里是赌档。其实呢,也不能说是暗地里,坐茶馆免不了打牌,打牌免不了赌钱。这都是公开的秘密。坐茶馆打牌,说是娱乐,其实很多人都是寓赌于乐。
何小兵两口子也好这一口,特别是何小兵,据说牌技了得,很多人都不敢跟他玩,怕输个底朝天。关于这个传说,张小梅不以为然,她跟何小兵打过牌,并没发现他有多厉害。但客人只信其有,不信其无,有时遇到三缺一,他们两口子就会看情况及时补上,何小兵上时,客人就小赌怡情,不打大的。张小梅上,那就该打多大就打多大,一直打到新客加入为止。
有意思的是,两口子牌技都不错,运气也好,当了这么多年的候补队员,还真是赢多输少。加上每天的茶钱加“抽水”,算起来比在外边打工好多了。之所以请张莲过来帮忙,倒不是因为生意好得忙不过来,而是张小梅看堂姐一个人带着娃儿,老公在外边又挣不回几个钱,生活有点难,便想帮她一把。本来,这事何小兵是不同意的,一是茶馆那点活他能应付,没必要请人花冤枉钱;二是张莲那个老公跟他关系不好,原因就是他们两口子好打牌,有时赌输了,便会找张莲借钱,而每一次都会被张莲老公——他们的堂姐夫教训一顿。搞得他很没面子。但是,张小梅有点懒,不喜欢成天围着一帮赌客端茶递水,扫地抹桌。她喜欢做候补队员,每天打几圈,轻轻松松就把钱赚了。所以她坚持要请人,何小兵跟她争论过几回,还赌过气,可每次吵嘴,她都会祭出*手锏——晚上不让他得手,搞得何小兵一个人的夜晚索然无味,最后实在是拿她没办法,只得应了。
都说穷人家的孩子能吃苦,从小,张莲的家境就不如张小梅,这就让她养成了手脚勤快的习惯。小梅茶馆那点活,对她来说不在话下。除此之外,她还经常从自己家地里摘了菜来,白送给何小兵他们吃。她的这个性格,让何小兵对她的不满减少了些许。
但何小兵还是习惯性地在任何杂事面前,都条件反射地想到她。拿了我的钱,就得给我干活。他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可张小梅不这样想,堂姐拿那一千块钱,包了茶馆的所有杂务,很够意思了。张小梅觉得不能把啥子事都推在她身上。
“你去不去?不去到时候你别怪我……”
何小兵说:“啥,又跟老子来这套?”一边说一边伸手摸过去。
张小梅推开他的手,说:“别碰我。”
何小兵说:“我不碰你碰哪个?我不碰你难道去碰张莲!”
张小梅愣了一下,心想张莲有啥好碰,除了痘痘就是一身肉。一个“糯米糍粑”能跟我“广州塔”比?嘁!
“吃着碗里的妹妹,还想着锅里的姐姐。不要脸!”她说。何小兵压上去说:“我不要脸,只要你!”两口子就在被子下边滚成一团。
5
小梅茶馆的门板打开了,是张莲伺候婆婆和娃儿吃完早饭后过去打开的。跟以往一样,何小兵两口子来得比较晚,张莲就先把门打开,烧水,抹桌子,准备花生瓜子,等客人上门。在乡场上找个工作不容易,对堂妹一家,她心存感激,具体到行动上,就是尽可能地忙前忙后,把茶馆打扫得干干净净,料理得井井有条。就算生病了,也从不偷懒。比如现在,眼看就过年了,她却得了感冒,成天头重脚轻的,满脑子浆糊。即便这样,她还是坚持着,像往常一样里里外外地忙碌。
张莲咳得厉害,咳得连打牌的客人都说,你都病成这样了还干活?张小梅跟何小兵也让她回去休息,顺便准备年货过年。可张莲不想休息,老公说老板拖着不发工资,要到放假时才结账。她怕这是老板的借口,怕老公收不到工钱,她得坚持赚下这几天工资。
斯文哥又来茶馆了,这回没带女的,罕见的单枪匹马而来。坐了一阵,又打了几个电话,竟没约齐人。见张小梅劝张莲去医院,也没搞清状况,便凑过来表示关切,“老板娘,病了?来来来,把腰给我,让我给你把把脉。”
一边说,一边作势欲搂张小梅的小蛮腰。
张小梅闪身躲开,说:“滚!”
斯文哥打个哈哈,转向张莲说:“原来有病的是你呀,你这个病,其实也没得啥子,找人打一针,打一针就好了。”
“打针,打针不要钱啊?打个屁!”张莲气呼呼的,一阵猛咳。
斯文哥就坏笑:“我说的是找个男人。”
张莲反应过来说:“我呸!你去死啊!”
斯文哥说:“是钱重要还是命重要?没钱早说啊,哥帮你啊!”
张小梅说:“哎哎哎,不要趁人之危哦!”
斯文哥说,“今儿哥身边差了个美女,要不,你陪哥打几圈,输了我的,赢了你的。”
张莲喘着气,努力稳住咳。“你说的?”
斯文哥说:“我说的。”
“说话不算话,猪狗都不如。”张莲说。
张小梅满眼的发现新大陆,她说:“姐,你也会打牌?”
张莲说:“不就是打牌嘛,不是和了就是胡了,猪都会。”
6
张莲头一次当候补队员。麻将她会打。只是这四乡八里的乡亲,逢年过节都闲得蛋疼,没有打牌不讲钱的。就算是小打小闹,三块五块,都得意思意思。如果手气不好,一天坐下来,输个一百两百,也是常事。他们家不宽裕,输不起,干脆就不打。
可是,这回有点奇怪,她的赌性被斯文哥成功地激发出来,反正输了也不是我给钱!她豁出去了。再说了,一般新手上场都会赢钱的,乱棍打死老师傅嘛。要是真能赢点钱过年,想想也蛮不错。关键是,年前她还得去一趟县城,那个美容院老板说了,药必须接着吃,要是中间断了疗程,那前边的药就等于白吃了。她不想前功尽弃。
打的是麻将,一筒两筒三筒四筒五六筒,红中白板东西南北风,别说以前就认得,就说在茶馆里干这一年多,那些绿底白面的方块,看都看熟了,没得啥子。只是,纸上谈兵和刺刀见红是两码事,张莲往牌桌上一坐,突然就紧张得脑子里一片空白,拿一把烂牌自然没得说,偶尔抓一手好牌,最后也让她打得稀巴烂,几盘打下来,输得连斯文哥都没底气了。
“算了算了,你不要打了,再打我都要*了。”他挥着手,就像是在撵一条癞皮狗。“小梅,还是你来打。”
张小梅说我有事,掉头冲外边喊:“何小兵,快来凑数,差你一个。”
何小兵听到张小梅喊,跑进屋来,看见张莲按着胸口,弯着腰猛咳,说:“我那个姨台(连襟)啥时回来,看你这样子,得上医院。”
张莲有些气,说:“不回来了,死在外边了!”
斯文哥笑,说:“怪不得天天长痘痘,打牌又老是输。原来是个寡妇!寡妇门前晦气多!”
张莲生气了,说:“你放屁!你才寡妇,你们全家寡妇!”
斯文哥说:“好好好,不是寡妇不寡妇。只是跟寡妇差不多。”
张莲瞪眼说:“你再说,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
斯文哥说:“刚给你赔了钱,你就这样对我?”
张莲说:“钱是我输的,我赔你。”
斯文哥说:“你陪我?三陪?三陪是犯法的,懂不懂!”
张莲不再理他,气鼓鼓地问张小梅借钱。“再打。”她说,她不甘心。
张小梅有点为难,说:“你别傻帽了,不会打牌就别打,钱又没惹你,别跟它过不去。”
张莲说:“你借不借,怕我还不起你?”
张小梅没办法,说:“行行行,我借给你。要多少?”
张莲想了一下,“借一千。”她说。
可是,打麻将就像变魔术,这刚借的一千块,很快又输得找不到回家的路了。也许,这点钱在斯文哥眼里不值一提,可是,对张莲来说却是一个月的工资,是娃儿的学杂费,是婆婆的药罐子,是她去县城看痘痘的一个多疗程。看着一叠人民币分别揣入牌友的荷包,张莲眼睛都红了,脑子里嗡嗡响,像放飞了一千只苍蝇。她从来就没赌过钱,当然也就没输过钱。可是,这人生的第一次,却输得她抓狂,输得她背心发冷!
何小兵说:“姐,你不要打了,等我来打。”
张莲浑身冒汗,头昏脑胀,站起来的时候碰翻了板凳,差点摔倒。张小梅赶忙扶住她。
张莲艰难地说:“那个钱,等你姐夫回来,再还你。”
斯文哥笑嘻嘻的,“说你阴阳失调你还不信!
张莲气得浑身颤抖,差点就想扑过去和斯文哥动手。
张莲走出小梅茶馆,回场背后的家。沮丧、后悔、心痛,急火攻心,乱七八糟的情绪,把她团团围住,她低着头,边走边咳,喉咙更痒了,想不咳都不行,咳得一身的虚汗,好像肺都要咳出来了。一路咳嗽回到家,不免想起远在外地的老公,便想打个电话给他,可最后还是叹口气,算了,只能一个人扑在床上,大哭一场。
7
张小梅发现钱柜里的钱对不上数,少了。问何小兵。何小兵说借给张莲了。
“她非借不可,你姐要借,我有什么办法!”
张小梅就有点怨斯文哥,要不是他挑逗张莲上桌打牌,她也不会输掉那么多钱,看样子,她是想把本钱捞回来。典型的赌徒心理,都这样。
借了就借了吧。张小梅没在意。反正她在茶馆里打杂,有收入,早晚都会还的。只是,张莲能回本吗,就她那点牌技,最后还不连底裤都输掉了?张小梅想劝张莲别赌了,牌这东西,看起来很亲民,好像是个人就可以玩,事实上天生嫌贫爱富,只亲有钱人,可不是她想玩就能玩的。别说是她,就算是何小兵,玩了几十年的老牌哥,场上响当当的麻将大咖,也不一定就回回赢。回望当年,风风雨雨,输得恨不能一头撞死的时候多了去了。
然而,生活中意外无处不在。不知怎么回事,接下来的那几天,张莲的牌技如有神助,突飞猛进,一日千里。她差不多就把茶馆里的杂活全都扔下了,搞得张小梅又要烧茶又要倒水,一时间竟很不适应。只能一个劲地使唤何小兵,叫他干这又干那,把个男人支使得团团转。
张莲不再等替补,每天直接往牌桌上坐,而且每回都拉上斯文哥。“我得把钱赢回来。”她总是用这个理由。
斯文哥发现张莲有点走火入魔,他反复强调:“早先说好了的,输了算我的,钱你不用还。”
可张莲固执得要命,非还他不可。当然,这得等她赢了钱再说。可她啥时候能赢?
张小梅有何小兵使唤,忙上一阵把活干完,然后她就很不放心地站在张莲身后,给她当军师。
接下来,奇迹就发生了,发生得所有人都措手不及,不肯相信。
8
张莲和张小梅,打这个摸那个。眼看着手上的牌就理顺了——两个三万,一个四万,要是能用三万换个二万回来,就完美了。好,那就打掉三万好进张,果然,没两个回合,上家就把她要的二万扔过来了。我的大姨妈呀,手上很快就是清一色的万子,下轿了,只等七万撞上门来,胡牌。
斯文哥赞叹,说:“厉害哦,时来运转了哦。”
的确转运了,因为后边好戏连台。
张莲手上底牌凑了一筒、二筒、四筒,打哪个?当然是扔掉四筒好进张,让上家见她把四筒打掉了,顺手扔了个三筒给她,气她,哪晓得,张莲要的就是这个。没几个回合,又胡了。
斯文哥有点意外,说“才几天功夫,请问美女,你这是跟哪个学的?张小梅?”然后他就大声叫何小兵:“何小兵,你跟老子出来说清楚。”
何小兵不知发生了啥子事,从外边跑进来。斯文哥说:“要想学得会,就跟师娘睡。这牌是你教的还是小梅教的?”
另二个牌友连输几盘,也有点急了,说小梅你不要在后边瞎指挥,再多嘴赢了都不算哦!
张莲就回头推小梅,说:“你忙你的,今天老娘要赢死他们!”
斯文哥坏笑,说:“赢,哪个赢?”
张莲说:“你去死!”
打牌跟下棋差不多,都有规矩,这个规矩,就是站在旁边观战的人,不要指指点点瞎支招。张小梅见客人不高兴了,就挪腿走开。张莲之所以能接连胡几盘,她也觉得是因为自己在后边指点的缘故。
听说张莲赢了几盘,何小兵的兴趣上来了,他搓着手,站到张莲身后。“我只是看看,我不说话,我保证。”他说。
张小梅走开了,何小兵又不说话,这回张莲得靠自己了。摸这个打那个,几个回合下来,何小兵看见她手上的牌已经形成了一条、一条、三条、四条、五条、六条的组合,新手一般都喜欢对对胡,喜欢成双成对,舍不得拆对打单,张莲也是,两个一条拿在手上,干等。何小兵看在眼里,却不能出声支招,还真的有点着急。
又摸了两圈,张莲还没进张,大家更认为之前的胡牌是张小梅的功劳了,其中一个还提醒何小兵:“不要开腔哦,开枪就会打死人的哦。”
张莲也有点急,她想要一条,可没人打给她,摸也没摸着,怎么办呢,这个一条肯定跟哪个同时捉对了,她咬咬牙,棒打鸳鸯,一拍两散,拆散一条的对子,打出去让人家碰,说不定就能逼出个二条。
“一条!”看张莲用力打出一条,何小兵长长地松了口气。
何小兵站在张莲身后看了几盘,这几盘张莲一回都没胡,气得她起身直往何小兵身上推,“你走开走开,你一来我就倒霉了,快走开。”
何小兵笑,说:“姐你厉害哦,这技术,都比得上老司机了。”
何小兵不是乱说的,他看的最后这盘,虽说也没胡牌,但张莲打得漂亮,开始见她手上拿着一万、二万、二万、三万、三万两组底牌,以为她会奔着小一万去,在那儿死等。没想到为了进张,她直接碰了对家的三万,飞快打出一万,留下一对二万,然后又下轿了,只要另外三家中有人打出二万,她就立马胡牌。可惜了,时机不对,这盘让别人胡走了。
何小兵被撵走后,张小梅有时实在忍不住,还是会跑去张莲身后观战,她可以忍住不说话,却无法不惊叹,原因是,隔不了几盘,就会有奇迹出现。张莲东打西摸,很快就是七个对子在手,只待一个九万撞上门来,就是七对胡牌。清一色素胡!
这手气,不服都不行啊!
听到包间里吵吵嚷嚷,何小兵有时也会跑进来打招呼,说小声点小声点,吵到隔壁人家要投诉你。然后就听说张莲胡牌了,也禁不住好奇,凑过来看一盘。看着看着就傻眼了,张莲手上凑上了龙七对,七个对子,还有两对是一样的牌。差一个五筒就成了极品大对子!
这下何小兵和张小梅都紧张起来,站在张莲身后不肯走,他们的神色让另三家很不安。斯文哥说:“你们不会是在出老千吧?”
张小梅说:“出毛线,你这回死定了!”话音刚落,张莲那只肉嘟嘟的手从桌子中间收回来,五筒,自摸!
当真是运气来了门板都挡不住,张莲这手气,顺起来就收不住,直到其中一家输得精光无奈叫停,这天的牌局才算收工。算一算,还清借的钱,竟还赚了。
斯文哥笑,说:“怎么样,没骗你吧?阴阳失衡,万事不顺;阴阳调和,打牌也胡。你看你,相思痘都不见了。”
张小梅愣了一下,下意识地看张莲,呀,还真是,张莲脸上那些红痘痘,好像比以前少了好多。
张莲也下意识地抬手摸脸,摸到几粒痘痘,眼神就恶起来,对斯文哥说:“你去死!”
9
对张莲神奇的牌技,张小梅百思不得其解,以前没听说她会打牌,而且打得这么好啊!难道真的有高人指点?
张莲笑,说:“有啊,这个高人就是你老公何小兵!”
张小梅心头一震。“要想学得会,就跟师娘睡。”她想起斯文哥这句很不斯文的话。老公何小兵和堂姐张莲……
最令张小梅心堵的是,还清赌债的张莲心情大好,抹桌扫地时,都禁不住要哼上几句,张小梅认真听了,她哼的竟然是“大爷听过我的歌,小何亲过我的脸……”
小何亲过她的脸?
请问是哪个小何?
还能有哪个小何?不要脸的!
张小梅想起来了,张莲平时就管何小兵叫小何。明明比何小兵小了好几岁,偏要叫人家小何!
叫小何不对吗?她是何小兵的大姨姐,叫他小何,没毛病。
张小梅心里堵,就像堵了一块石头,不,简直就是堵了两块石头!她和老公闹别扭了。何小兵问她啥事,她不说,甚至连个温馨提示都没有。
“你自己*好事你不清楚?!”
“我*好事,我*啥好事?”
“是啊,就你,能干啥好事!”
两口子开始冷战,谁也不理谁。晚上躺在床上,也要用被子隔出“三八线”,严肃得像两国边境。谁要是敢越雷池一条腿,或一只手,那就是“侵犯主权”,就是“外交纠纷。”
何小兵没心没肺,能睡,倒床一会就睡得不省人事。张小梅在这边躺着,却没办法不胡思乱想。一想到何小兵教张莲打麻将,张小梅就怒火中烧,无法忍受。谁知道他们是不是在打麻将呢?除了打麻将,就不能做点别的?看张莲那张脸,白里透红,越来越水灵了,连医生都没办法搞定的相思痘,仿佛一觉醒来就少了很多。整个人看起来,就像往糍粑里加了玫瑰糖,那个糯哟,直软到人心尖上去。
越想越气,最后干脆搬到娃儿的房间睡。可是,还是睡不好,每天晚上都翻来复去的,有时连娃儿都被她吵醒了,问她为啥还不睡,问她在想啥子。她能想啥子呢,她想老公何小兵跟堂姐张莲……要是外人就好了,大闹一场,鱼死网破,可是,那是她堂姐,家丑不可外扬……长时间心烦,长时间睡不好,长时间疑神疑鬼,结果就是——张小梅白生生的脸上长痘痘了。
张小梅脸上这个奇异的变化,很快就被斯文哥发现了,他死盯着张小梅的脸,说:“嘿,咋回事,你也长相思痘?还相思谁?莫非相思我?!”
张小梅很气,气得就想吐他一脸口水。
斯文哥不管她,只管满嘴跑火车:“哈哈,这回轮到你阴阳失调了。你看张莲,老公过年回来了,相思痘就好了。”
张小梅气得暴跳如雷,她冲着斯文哥很不淑女地吐了一口:“呸!”
10
对小梅茶馆来说,春节就是一年中的旺季。从四方八面赶回来过年的乡亲,除了走人户胡吃海喝,最大的一件事,就是围一桌打牌,从早上打到深夜,甚至通宵达旦打到天亮。好像大家在外赚了钱回来,就是为了这几天昏天黑地的放纵。不管输了还是赢了,等过完年,都跟接到命令似的,都赶着去坐火车搭飞机,跑到城里去赚钱。周而复始。
就没想到,小梅茶馆会被人举报,或者说,它早就被人举报了。警方对此了如指掌,只不过等到过年这几天再动手。十多个便衣混在人群里,还真跟旅游者差不多,他们兵分两路,散开来堵住小梅茶馆的前后门,然后,突然一声令下,有几个穿警服的人好像从天而降,或者突然从地下冒出来,呼啦一声就冲进了茶馆。
小梅茶馆关门了。何小兵是茶馆的法人,到派出所过年去了。关了十多天,又交了一笔罚款,正月都快过完了,这才放出来。警方放话了,要是再聚赌,就抓他去坐牢。警方怕他不信,专门给他普法,刑法第三百零三条规定: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或者以赌博为业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开设赌场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我去,要个钱都要坐牢?何小兵不想坐牢,他决定外出打工,等躲过了这阵风再说。张小梅呢,不能跟他出去,因为要留在家里,负责管理两个娃儿的吃喝拉撒学。
和张莲一样,张小梅也成了留守妇女。习惯了与何小兵出双入对,突然间身边没了陪伴,这日子真的是过得清汤寡水。
现在,张小梅每天就干一件事,接送娃儿上学放学。然后就没啥可干了。至于张莲跟何小兵到底有没有事,也懒得去猜了。实在是无聊了,就去找人打牌,赢点钱买开心。她相信自己的牌技和手气,跟一帮连广州塔都不知道的乡巴佬打牌,赢点小钱,没问题。
只是没想到,人走倒霉运,喝水都塞牙。何小兵不在家,好像干啥子都不顺,坐上牌桌子,竟然每赌必输,几番挣扎想回本,连打几个通宵,熬夜熬得眼睛都肿了,可是,本没捞回来,反而越输越多,倒欠了一屁股赌债。而且,脸上的相思痘越长越多!
张小梅简直就没法接受这个事实,自己竟和张莲一样长痘痘了。可是,没有办法,她只能和当初的张莲一样,到处求医问药。为了治好这个痘痘,她甚至主动找张莲问她有啥独家秘方。“真的是有男人就不长痘了?”
张莲说:“屁,你信他鬼扯!”
张小梅说:“那你是怎么搞好的?”
张莲摸摸脸,说我也搞不清楚,可能是心情好吧。
张小梅就想起何小兵,心想你们就跟我装吧,你们他妈的都是环保袋,特能装!
有天,张小梅在牌桌上遇到了斯文哥,斯文哥和往常一样,一脸斯文的笑。他微笑着,问她何小兵去哪儿了,问她茶馆啥时开门接客。
接客?换到以前,张小梅一定会像张莲那样,虎着脸着说接你个头!或者说你去死!可是现在,张小梅突然感到心里边动了一下,又动了一下,痒痒的,像有条毛毛虫在爬。斯文哥的眼神,让她下意识地伸手,摸了摸脸上的相思痘。这个相思痘,真是阴阳失调开出来的花朵?
“你上过广州塔吗?”她问,眼神很辣,声音很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