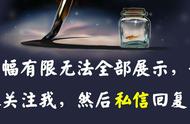作者:赵香玲
说到热炕头,想必北方人马上咂咂嘴:那是真舒服!冬暖夏凉,养腰又养腿。

每到冬天,北方的雪是必不可少的。人们对雪是有恨又有爱。不下雪,大人小孩都会遗憾,感觉不像个冬天。下了雪,路难走,扫雪累,大人又会骂街骂人。下雪的日子,不出门做工的人们三五好友围坐在热炕头,一起喝喝酒,打打扑克,吆三喝四,其乐融融。
今儿来了一群朋友,我多贪了几杯,兴奋的睡不着,躺在阳台前摇椅上看对面的楼。一两家有灯光,很弱。突然就想起老家的热炕头,睡不着的夜,母亲絮絮叨叨讲街坊邻居婚嫁迎娶,谁家儿女出息,婆媳、翁婿和睦。我和她讲讲在北京街头,看花红柳绿,行色匆匆早出晚归被挤进地铁,挤下公交车的日子。那个时候年轻,觉得世界鲜亮,到处都是希望……
北方热炕头有很多个用处,发面,暖菜,睡觉,还有恋爱……
我小时候家里很穷,那个年代物资供应不足,每个孩子只有一双棉鞋,下雪天一不小心就会湿透,冰冷冷的,母亲就会把鞋子架在灶台前烤干,鞋垫放在炕席下烘干,早晨上学的孩子就可以穿一双暖暖的鞋子出门了。
我母亲曾告诉我,对门老太太有5个孩子,没办法买新衣服,棉衣棉裤都是过年头一天拆洗,蒸馒头时用火烤,热炕烘干,老太太一夜不睡,缝好衣服,大年初一给孩子换上,就当作给孩子们换新衣服了。富裕一些的人家,冬天两床被子,两床被子中间都是孩子们的衣服,起床时被子里的棉衣不至于冰冷。早晨母亲都是早早起床烧火做饭,用母亲的话:早晨孩子们睡的最香,早晨的这把火要烧旺一些。
夏天农村都是做两顿饭,中午做好了盖在锅里,晚上直接吃,不烧火的晚上,炕凉凉的,平板躺着,非常舒爽。老人说,这样躺,老了不驼背。我不知道有没有道理,只是,至今我也不喜欢那种软软的床垫子,当年刚兴起席梦思床垫时,人躺上去,会陷进去,我记得我出差天津,住在一家部队招待所,住了一晚上,我第二天落枕去了医院治疗。

我们这一代,改革开放给了大好机会,大部分人成年后都离开老家,或读书或打工,我88年离家去了北京,北京在那个时代,就是我们的梦,我沾了母亲的光,跟了姨家大表哥一家在北京讨生活。大表哥是个军医,很聪明的哥哥是个技术型人才,对我影响很大,终生要学习是他给予我的教育思想。嫂子是留在北京的军人子女,漂亮,一副好嗓子,一双巧手。我跟着嫂子学习城里人的生活方式,努力工作,闲下来去做义工,不容易,却很充实。
我 差不多每年都回老家几天,火车16个小时,加上汽车,回一次家要20小时左右。回家第一件事是爬上家里的土炕,炕头就由父亲的专睡位置换成了我,一整天盘腿坐在土炕上,当然除了下土炕对邻里邻居迎来送往。 北方好多家庭热炕头上睡一家人,父母、哥哥、姐姐。我小时候家里条件不是很艰苦,家里有两铺土炕,姐姐单独住一铺,那时候最盼望着姐姐出嫁,那个土炕可以给我独享,自己的蚊帐,自己叠被子,被子上盖一条彩色的围巾。

记得下乡的知青从青岛来,住在我们家里,留着长长的辫子,穿着很美的衣服和鞋子,皮肤白净,她和姐姐住在一起,我最喜欢的事就是她们收工回家,我爬上她们的炕头,听她们给我讲城里人的生活。所以那个时候我的梦想是离开农村去城里吃白馒头,睡柔软的床。
姐姐出嫁时我才13岁,姐姐的土炕给了哥哥,哥哥去东北打工,土炕给了我。 读初高中都住校,回家少,冬天回家妈妈也不允许我自己住,说是浪费柴火,后来就离开了家,进了城,再回来也只是小住,就和父母一个炕头睡了。
再回头,母亲去世,我从北京回到了老家烟台,因为爱酒,开始做点进口酒的小生意,养家糊口,忙碌也快乐着。姐姐哥哥的孩子们都有出息,去了南方定居,老父亲和兄嫂一起住进了城里,老家的土炕也就成为了我的梦。
我的眼里,城里的房子就是驿站,不断的更换,没有什么温度。我在每一处房子里都做一铺炕,城里人叫榻榻米,加了电,叫电炕。我的办公室也寻一隅做了一铺电炕。电炕周围画上了花鸟,冬天下雪的日子,我会约了三五姊妹,兄弟喝喝茶、品品酒,聊聊天,或者打打扑克。
城里的电炕上屁股热着,茶水氤氲,酒香浓郁,瓜果丰富,环境优雅,往来的都不是饿着的了,心里却时不时觉得少了点啥?
认真想:是少了烟火气!
现在的孩子越来越少睡热炕,北方的农村,家里也一定有个房间做上床,漂亮的床头,幔帐,很厚的被褥给孩子们准备着,因为孩子们从城里回来,怕土炕太硬,睡不惯。 至于吃饭,北方农村大部分家里仍然都在土炕上吃,会准备一些小板凳,小马扎,因为城里回来的孩子盘腿坐着一会儿就会腿麻喊累,万一再找个南方的男女朋友,盘腿坐在土炕上吃饭就成了遭罪了。
大约是年纪长了,我会时不时想念老家的门柱砖瓦,想袅袅炊烟,想热炕头上酒杯里的那些酒,想对面的人。 日子好好过,我想,尘归尘,土归土的,不只是一句话,是真实存在的,活着的全部目标吧。
我们要好好的爱,爱自己,爱家人,还有力所能及的人和事事物物。人生久远,都有尽头,在我、在你,日子不过就是一杯酒,一铺炕而已。世界美丽,都好才好!

壹点号烟台文艺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