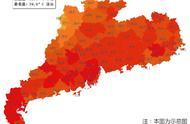认识草药,是因为要认识野菜。
瘦小的我跟在母亲身后,小竹篮里稀稀拉拉几棵野菜。
这是灰灰菜,这是银芡,这是荠荠菜,马齿苋还太小。掐吧,回家给你蒸菜包馍……别掐黄蒿,苦。母亲弯腰从小竹篮里挑出一棵黄蒿扔掉,指着前面一棵匍匐在地上的草,说,那是黄黄苗,是菜,也是药,心凉的药。
我从菜包馍的兴奋里跳出来,跑过去揪那细茎上的黄花儿。哦,茎是空的,轻易就断了,使满劲的我被诓了个趔趄。
小孩子对“药”这个字天生畏惧,看着白汁从断茎处流出来,我不无担忧:药?敢吃吗?会毒死不会?
母亲笑起来:惜命了!当菜吃的药多了,你看,黄黄苗,鬼圪针,小刺蓟,车前草,白蒿,都能吃——有病治病,没病当菜。
我似懂非懂,咬一下黄黄苗的花茎,苦苦的。
无处不在的草药,就这样一一走进了我的世界。

那是八十年代初,农村的医生寥寥无几,像我们这样的小村,即使买几片安乃近土霉素,也要跑到几里之外的邻村。小伤小病,都是自医,用这些长满了房前屋后田间地头的草棵子来治。“药圃无凡草,松窗有素风”。对于老百姓来说,无边无际的土地,就是他们取之不尽的药圃,良药也是凡草,随着季节荣枯,与我们这些凡人同在。
小时候,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知道许多简单又实用的知识:受伤流血,找棵小刺蓟捣碎,绿汁四溢按上,草叶子一裹,草茎一缠,不用再管;流鼻血,自己去地堰上刨白茅根嚼;伙伴害痄腮,去剪人家的仙人掌,和白矾一起捣碎糊腮帮子;家里猪发瘟发烧,遵命去刨苇根蔷薇根地丁黄黄苗;拉肚子了,有马齿苋涩萝秧;咳嗽了柏叶煎鸡蛋、红糖炒姜……
学校里勤工俭学,交过白蒿、酸枣核、红参、蒲公英(等我知道黄黄苗有这样一个美丽的名字之后,就不愿再叫那丑丑的小名了)。我并不知道它们都去了哪里,怎么就变成了片、丸和药水水,但遍地的草药,真的给了我们实实在在的安心。
我们极少生病,泥里土里小伤不断,也不见谁发炎感染生病。这一切,该都是那些锅里碗里绿叶子的功劳吧。
母亲喜欢拿大把的蒲公英叶子煮玉米糁汤,狭长的叶子碧绿柔嫩,在浓稠金黄的粥里上下翻滚,案板上放着腌萝卜丝或者蒸菜,看得人肚子更饿。母亲往碗里舀着蒲公英叶子,说,吃吧,心凉。她所说的心凉,专对应“心热”,那些上火牙疼、喉咙痛、身上各处的疙瘩红肿疼之类的病症。
父亲说,地里的药才是咱老百姓的药,花钱少就能治住病的医生,那才是好医生。后来做了医生的我,经常会说:去吧,找某某(草药),熬了喝几天再来看——西大路往西就有。在与中医黑顽强辩驳时,最有力的武器不是引经据典,而是:我用过。
蒲公英
在无数种草药里,我也偏爱蒲公英。小时候的喜欢,是因为那笑脸一样的花儿,在早春裸露的大地上,温暖、明净、喜悦。少年时,喜欢它那团雾一般随风飘散的种子,有点诗意有点忧伤,像我新生的那些情愫。后来我学医,这棵小草在我手下一次次验证着它“天然抗生素”神奇而强大的疗效。我和家人们那些喉咙痛、牙疼、中耳炎、炎性肿块,无数次被这把微苦的草棵子打败。

大儿子两岁时,忽一天食指肿胀,又硬又亮,一挨即爆的样子。饶是医生,我也吓得不轻,满脑子都是刀片划过肌肤脓血四流的画面。我去村边地堰上翻找,剜回来三棵蒲公英两棵紫花地丁,洗净,捣成糊,在儿子的食指上敷成一个绿壳。一夜不安。早上取下药包一看,除了皮肤微有绿色,一切如常。
早年坐门诊,遇见一个得了急性乳腺炎的年轻妈妈,体温近40度,左乳肿胀得像个小篮球,焮红发亮,痛不可触。住院,退热消炎,通乳按摩,热敷,抗生素直接三代头孢,收效甚微。如此下去,化了脓,只有手术切开引流。
情急便顾不得许多,我叫来家属:去剜些黄黄苗和紫花地丁,洗净拿来。好在不是冬天,草药并不难找。我捣烂草药给病人敷上时,心里其实忐忑:这算是西医擅长的急症,不知道中医这慢郎中会不会真造个奇效出来。如若还不行,这一刀怕是难免。“这两样药,熬浓一些,当茶喝”。
第二天一大早,家属欣喜若狂跑来叫我:消多了消多了!不红了也不疼了!
长吁一口气。这算是中医的又一次胜利吧……
清明柳
杨柳枝,芬芳节,可恨年年赠离别。
清明也折柳,却不为赠别。
清明那天的柳枝,照例也得日出之前采。门前的大柳树,河边的矮柳丛,那些唾手可得的枝条被随意砍回了家,照例是挂在檐下阴干。
清明柳和柴胡一样,是用来发汗退烧的。家里谁感冒发了烧,母亲从墙上扯几根干柳枝,撅成几截放锅里,添两碗清水,放了葱白、老姜、辣椒面、整棵的芫荽、盐,熬成一碗发黄的辣汤来。一掀锅盖,满屋子清苦的味道,有时还会奢侈滴上几滴香油。一碗这样的汤水下肚,盖严了被子躺着,很快就遍身微汗,热退自然病愈。

经年的劳作让母亲身体很好,高高低低五个孩子的吃穿和十几亩地的庄稼,让她片刻不闲。我从来没有见过她大白天在床上躺过,只有一次例外。
那天母亲从地里回来,没有了往日的健步如飞,疲惫恍惚,摇摇晃晃。母亲发烧了,额头滚烫。她强打精神做完饭,从墙上揪下一把清明柳,开始熬辣汤。家里没有姜,也没有芫荽和葱,锅里只有一大把干柳枝熬着。母亲坐在灶台前无力起身,让我去拿了两个干辣椒放进锅里,就赶我去吃饭了。
母亲喝了辣汤进屋捂汗。她的虚弱让我害怕,更担心这汤水会不会有用:没有了葱姜芫荽,就凭挂了大半年的干枝枝,还能治病吗?
不到半后晌,出透了汗的母亲,神清气爽擓着篮子下地了。
后来学了医,才知道阿司匹林正是源于柳树,这解热镇痛的圣药,原来始终伴随在我们左右。
端午艾
在农村,没有人不认识艾,没有人不用艾。
端午节的早晨,太阳没有升起之前,村子里每一家都会有人背一捆带露水的野艾回来。这几乎是一种仪式,专对于这个节日的仪式。在他们看来,这一天采割的艾才算是真正的药。北方农村的端午节不喝雄黄酒,粽子也可以没有,但艾草是绝不能缺席的,若有了闲暇,五色线和香囊才能登场。
割回来的艾草,一小扎一小扎挂在檐下阴干,驱病的用处大于辟邪。

那时的农村,生了孩子的人家,必会煮一锅艾水,放温了给新生的孩子洗浴,据说避风。以后的几天,还要用艾水给产妇熏洗,据说不得月子病。
夏天蚊虫多,老人们把一根艾绳燃起,一家人来便可安然入睡。
腰疼灸腰、腿疼熏腿、肚疼敷肚脐、驱寒泡脚,艾叶的诸多用途中,对我来说,止血最是印象深刻。
小时候我曾在老宅的青石台阶上磕破了头,鲜红的血滴答滴答打在地上,怎么也止不住。奶奶过来,让吓坏了的我拿小黑手捂住伤口, 回身去找一把艾叶燃了,火苗刚熄,一撮艾灰按我额上,片刻间血就止住了。六七天之后,揭去一大片血和艾灰结成的黑痂,非但没有感染,连个小疤也没留下。奶奶和妈都觉得这是“端午艾”的神力。当然,这神力不单对我,村里每个小伤不断的孩子都见证过。
我体寒,年年秋后便开始腰腹冷痛,去年越发严重,入冬大冷,不得已开始自治。晚上抓一大把艾叶,加了花椒熬水,先熏脚,水温勉强可以放脚进去,就开始泡脚,凉了再加热的,直至墨绿色艾水淹了脚踝。艾叶已煮得柔软若棉,在脚边一飘一荡,偶尔几根小梗在脚底硌得痒痒的,身上开始微微出汗。一周下来,通体温暖舒泰,觉得天仿佛也没有那么冷了。
“温经止血,除湿驱寒,平喘镇咳祛痰”,“除湿止痒,祛风疗疮”。这些年,在我们“艾草之乡”,成千上百亩的艾,一年三茬在肥沃的田地上自由生长,无数种改了模样的艾草,漂洋过海去了远方。艾,这曾经锄之不尽的野草,不止给乡亲身体肌肤的护佑,终于以财富回报了与它们世世代代纠缠相依的人们。
红薯叶
我的口味越来越像母亲,大鱼大肉远没有野菜让我着迷。从春到秋,田里树上总有我想吃的根叶花实,也总有机会拿它们给人科普。春天的猪毛菜和鬼针芽降脂清血管,后者还兼消炎。正月的茵陈护肝退黄清湿热、四月的槐花清热凉血、花椒芽温胃散寒、嫩柳芽治腹泻痢疾高血压。“八月小蒜,香死老汉”,小蒜骨朵学名叫薤白,辛辣通脉治冠心病。山薄荷腌了吃别具风味,又祛风热治喉咙痛。它们不再为了充饥,是因为美味和保健作用被端上餐桌,也许,还为了怀旧。
诸多的叶子菜里,我和母亲一样,喜欢吃红薯叶,它柔软光滑,没有异味,怎么吃都好吃。年幼时经常看母亲大篮小篮捋回来,晒干存着。冬天,糊涂面条里有它,红薯糁汤里有它,稠稠的粥饭被这些干叶子染成浅褐色,有一种特别的香味。红萝卜丝白萝卜条吃多了胃嘈,母亲就换个样子,把干红薯叶焯开凉拌,洒几滴香油,我们都能吃下去大半碗。等粮食菜蔬都不再短缺的时候,母亲还会大篮大篮扛回来,喂猪。
母亲不知道如今的红薯叶已经升级为“蔬菜皇后”了,她还是会掐了红薯秧的嫩尖或叶子,炒了,或者拌面蒸了,乐此不疲。去年母亲生病不怎么吃饭,问她想吃啥,说,有红薯叶的糊涂面条。弟弟一副怒其不争的无奈表情,我也苦笑:哪里有啊?其实,我也想念母亲做的糊涂面条了,下了玉米糁,煮了黄豆、粗萝卜条、红薯叶,冬天里那一碗浓稠喷香的糊涂面条,暖胃,也暖心。
我想替母亲辩解,赶紧去百度:提高免疫力、止血、降糖、解毒、通便利尿、催乳解毒、保护视力、延缓衰老……
看吧,它哪里只是一把野菜那样简单呢?
秋深了,四野风凉,大地上万千种植物正从苍翠走向枯黄,只待最后一场秋风将它们催眠,去冬天里做一场大梦。凡草或是良药,都会在来年春天醒来,妆点或者救治,无限轮回,就像这片大地上的万千凡人,生生不息, 生生不息……
作者简介:王苏兰,女,网名兰兮,河南洛阳人,宜阳县中医院医生。文字散见于《牡丹》《洛阳文学典藏2001--2021》《洛阳杂文年选》《中国民族报》《洛阳日报》《潮州日报》等报刊杂志及文学平台。
(编辑:杨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