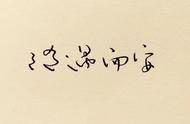许多年前在一次国际航班上,我坐在一位不会说英语的东欧老人旁边。他坐在靠过道的座位,当空姐经过时,他会拍拍我的肩膀提醒我,或者伸开手把我的垃圾递给空姐。我们当时正在安静地吃饭,我想是在近乎黑暗的环境下,我们是俯身在托盘上吃的,这时他伸出手拿走了我的面包卷。他没有看我一眼,就只是打开面包卷,咬了一口,然后把整个面包都吃了。
毫无歧义的是,面包卷是在我的盘子里的,而他自己的已经吃完了。他是不是以为我已经吃完饭了?但当时我手里还拿着一把叉子,意大利面还至少剩下一半。

我们很容易重复这样的想法: 他拿走我的面包是因为他是个男人,或者白人,或者因为我是亚洲人,一个女人;想到这与权利有关,与一种定式有关。但是这不对,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对的。那我还能说什么?没什么了,我承认。结论就是你无法了解他人的想法,是你从未能完全明白他人做法的理由。
当有人在谈话中说“我明白”时,我从来不觉得他们明白什么。事实上,直觉告诉我,那些对我说“我明白”的人最不明白。要是他们明白他们其实不明白,我们可能也不那么孤独了。如果你把单词 understand 中的字母 s 去掉,你可以重新排列这些字母来拼写出“冗余”这个词。只需用笔划一个小斜杠,就揭示了整个单词其实多无用。

问题是,人们喜欢表达自己对普通生活事件的理解。这也说得通:出生和死亡是普遍事件,疾病,进化和恶化的爱,亲子关系几乎如此。我们都对这些方面有一定的了解,希望别人知道我们也知道。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是生活的重点。
生下我儿子,对我来说艰难无比,更不用说后来的产后康复,以至于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关于两天待产的记忆仍持续在我的脑海中闪现,不期而至,短暂地抹*我对生存的渴望。这不仅仅是因为我被迫面对生产疼痛——麻醉师分三次将硬膜外麻醉置入我的脊椎,但并没有带来任何缓解——也不是因为如果没有现代医学的反复干预,我和我的儿子可能都会死去。这与我一小时又一小时地处在那微薄的、脉动的边缘,感觉自己即将,甚至可能注定死去有关。我从来没有和任何人谈论过这个问题,没和其他的母亲,也没和我最亲密的朋友谈起过。虽然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很容易受到言语伤害的人,但我害怕听到那两个简单的词。如果在医院里,我丈夫告诉我他理解,那我们的关系就会破裂。而相反,他哭了。
这就是人们失误的地方: 他们表达的是对一种特定的、私人的经历的理解,而这种经历你自己可能还无法充分描述——一种你本人可能还不懂的经历。我记得看到一位美术老师纠正我的一幅抽象画,用他的大白笔在一块细节上作画。

最近,在附近的操场上玩时,我的儿子用手铲起树皮,把它放到滑梯底部不断增长的树皮堆里,这项活动给了他一种成就感,反过来也给了我一种兴奋感。对他来说,觉得自己对这个世界有所作为是多么容易。
一个三四岁的女孩走近他,说了些什么,当他不理睬她时,她向我走来。她说话声音太轻,小孩子的发音也不够准确——他们想说的比能说的多多了——所以我说: “对不起? ”
她误解了我的困惑,一双眼睛又大又忧伤。“我不会说你们的语言,”她说。她继续看着我,她的目光非常直接,我喜欢这种方式。
我笑着说: “但是你懂的。”
我们很快就把事情澄清了。她想顺着滑梯下去,但她不能接受滑进一堆树皮里去。我把滑梯上的树皮擦掉,我儿子哭了,然后生活还是照样过。后来回忆起来,我惊叹于她思维过程的复杂性。我们的邻居主要是拉丁美洲人。早些时候我听到她对她姐姐说西班牙语,但是这个小女孩从一开始就试图用英语和我交流。当她认为我不明白时,她以为我会说第三种语言,一种她无法理解的语言。到什么年龄,我们才能理解别人头脑中整个世界的存在?我们在什么年龄掌握了障碍的概念?

在官方汉语中,常用的词语懂,明白,了解和理解都可以翻译成英语中的“ understand” ,尽管你使用的术语与音调、上下文、熟悉程度和抽象性有关。这些术语的分解可以说明问题。例如,“明白”由“明”,“明亮或清楚之意”,“白”,“白色之意”组成,使人产生一种清晰的感觉。
“懂”的书面汉字含有部首,或者书面结构,意思是“心”——通常出现在表达情感和思想的词语中。“理解”和“了解”都含有“解”这个字,意为“解开”,并进一步展开了“解”字的书写。如果你从右上角开始顺时针方向看,你可以辨认出象形文字 “刀”,“牛”和“角”;据说这个词起源于“切断牛角”——解剖或剖开。

在英语中,单词 understand 本身不易理解。它的不透明性也很有趣。(单词倒过来)站在下面?当我站在一座桥下,我没有特别的感觉或洞察力,除了模糊地感觉有什么巨大的东西正在我的头顶上若隐若现,阻挡了我对天空的视线。罗密欧站在朱丽叶的阳台下,西哈诺和克里斯蒂安站在罗克珊的阳台下,王子站在长发公主的窗户下。让我们假设他们至少想要了解那个在他们之上的人。但是,他们的位置——在下面,而不是面对面——难道不会让我们疑惑,在下面的人是否真的能懂得什么吗?
“隧道! ” 我儿子喊道。这个词被他发音成“ nunno” ,且必须是惊呼而不是说出来。在离我们家一个半街区的地方有一条地下通道。上面是火车轨道。散步时,我的儿子喜欢在这个混凝土穹顶的阴影下逗留。我试着催他赶路,鸽子在桥墩的顶端栖息,桥墩下的人行道上是一堆乱七八糟的羽毛和鸟粪。我偶然发现了被肢解的鸟类——浣熊或野猫*好事。但是我儿子,他喜欢这里。也许孩子们善于“下面呆着”。关于这个地方,他似乎知道一些我都不知道的事情。

词源学家阿纳托利 · 利伯曼断定,古英语的理解(understandan)是同义词“ stand in front of”和 undergetan 的混合,现代概念“ get someone”的根源仍然存在。如果我们放弃对特定介词“ under”的关注,我们就只剩下这个模糊的概念: I stand near you(我在你身边), 我和你很亲近。
但有时我会说,“我明白,”我的意思是,“请不要再和我说话了。” 通常说话的人会用上百种不同的方式一遍又一遍地说同一件事,而我会试着发出收到的信号——我明白了,你已经跟我说清楚了——这样攻击就会停止。但很多时候,它们不会停止。我的母亲告诉我她不快乐;医生不听,她行走困难,她的室内植物不能茁壮成长。细节不断变化,但恐惧始终存在,对话不断地循环和重播。每个人都在说,“听着,听我说。” 但我只是说,“我明白。” 这是一种摆脱的方式,增加彼此的距离,同时还停留在同一个地方。也许我不想理解,也许我想过在那条路的尽头有一个真相在等着我。或者,也许,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理解的*减弱了一点,被理解的需求却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紧迫。
,